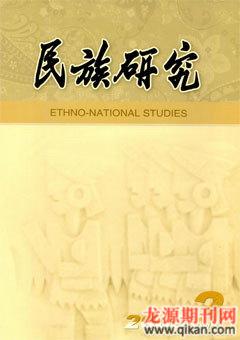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关键词:南京临时政府“五族共和”国家转型民族关系
作者彭武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五族共和”问题,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笔者认为,“五族共和”不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更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本文尝试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五族共和”的确立及相关民族关系基本情态的形成,作一探讨。
一、民族思想的整合与认同
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其中,是建立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以及怎样处理和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等问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肇端于甲午战后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良思想家,基本上在武昌起义前形成较一致的社会政治共识。其理论背景是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传人和影响,现实背景则是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严复在译介社会进化论的著作《天演论》及《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中较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合群”自强说,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民族或民族主义,但具有中国现代民族思想的启蒙意义。此后,康有为提出“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合为中华的主张,把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康氏在与革命派论战的著名文章《辨革命书》中,从历史、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对他的“大中国观”又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帝统宗室,不过如汉刘、唐李、宋赵、明朱,不过一家而已。”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并对国内民族关系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如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说》等文章中,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功能、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和途径等问题做了说明,并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现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等概念。虽然对于前者他没有做详细的解释,但对于后者他的解释是十分清楚的:“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不难看出,上述维新改良派的思考包含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方面。民族认同就是如何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中解放出来以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政治认同就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现从“朝廷国家”到“民权国家”的转型。其中之要义,则是力图寻找一条解决民族平等与国家政治统一之间的协调和平衡的渠道与路径,即如何克服帝国内部的族群矛盾、如何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组织起来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如何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认同之间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政治结构。维新派的这些探讨,不仅在思想理论层面上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张本,而且在当时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维新派温和的政治实践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他们关于民族主义与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因此中断。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这一认同与整合的脉络主要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立宪派两个思想阵营中延伸。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早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孙中山就响亮地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振兴中华”的口号,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由于西方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历史上传统国家与民族关系之扦格,少数民族之一满族是统治民族及由于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的不正常的国内民族关系现状,革命派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狭隘、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倾向。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一文中说,满族乃“异种,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是当时满汉异种论的典型代表,进而他主张满汉分治:“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邹容的《革命军》是当时影响巨大的革命宣传品,但其中却充满了种族复仇主义情绪。他在该书绪论中的头一句话就说“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而在第六章所列“革命独立之大义”二十五条中有六条相关内容,如第五条称:“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就连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也把满族称为“东北一游牧野番贱种”,主张“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革命派的这种狭隘、偏激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其合理内核在于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在经过与改良派的论战及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革命派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正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民族平等与民主革命的有机结合成为主流认识。章太炎在1908年6月撰写的《排满平议》中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事刃其腹哉?”显然较之他过去的民族复仇论有了较大的转变。比较彻底的是勇于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孙中山。1906年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对满族将士的布告中说:“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民国军之将士,一则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雠,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特一则奋激而起,一则隐忍未发,是我辈虽立于反对之地位,然情谊具在,心事又未尝不相合也!”针对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中“驱除鞑虏”的缺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又做了明确的解释:“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应当说,在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上革命派逐渐接近维新派的“大中国观”。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立宪派在关于民族主义和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承康梁之余绪并有所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他认为,“以今日中国国家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际之事实亦然”。根据五族社会发展程度而论,“汉族为首,满次之,蒙、回、藏又次之”,但同为中国国民,即“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杨度认为无论满族还是汉族皆应以国家主义为本,即国家民族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取向,进而在
国民统一之下实现民族平等、文化融合。而实现其所谓的国民社会的途径,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治制度,达到国民与民族这二者的相互统一。“其始也,姑以去其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痕迹、界限之可言。”可见,杨氏“合五族为一家”的认识在国内民族构成及其关系问题上较之维新派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尽管在许多具体问题仍然存在偏差甚至是谬误。除杨度外,还有立宪运动中关于“平满汉之界”的各种奏折和舆论。据统计,《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该类奏折达20余通,其中满族4人、蒙古族1人、汉族12人。这些奏折中不仅提出“撤旗”、立法等消除满汉界限的建议,而且就满汉等国内民族关系的同质性、一体性也做了较深入的阐述。同时,以一批满族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北京创办的《大同报》及《北京大同日报》,专门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宣传“五族大同”。
上述各派虽然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在关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大致是殊途同归,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是,前者主张各族合在君主政体下,后者主张合在共和政体下”。因而辛亥革命一爆发,“五族共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各界的政治共识。总体来看,上述认同与整合的载体是国家政治重建问题,而主题是如何调适国内民族关系问题,其主要的动力群体是汉族政治文化精英及满、蒙等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分子。
二、政治实践中的妥协与认同
除了上述思想文化领域的认同与整合外,“五族共和”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国方针还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认同与整合的产物。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联合,二是南北政治势力的议和妥协。
一方面,“五族共和”是南方革命阵营中革命派与立宪派联合的政治基础,并在筹建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得以确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相继宣布起义或“光复”。其中除了革命党人的发动和斗争外,立宪派也转向革命,“相继改制易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使清朝统治加速瓦解”。于是,在建立什么样的中央政府以及由什么人执掌的问题上,“五族共和”成为统一的号召和旗帜。在武汉光复的次日,起义的领导人便议定“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虽然湖北军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将五色旗作为国旗,但此议一出,实开“五族共和”之先声。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两地先后发出建议成立临时政府的通电,都力争控制中央政权。同时,各地在光复后也使用不同形式的国旗,“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在建立什么样的中央政府等问题上存在分歧。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由于首义之区湖北方面力争,各省代表联合会于24日决定迁往武昌开会,同时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联络。此时湖北形势吃紧,汉口、汉阳相继失守。11月30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代表中革命派与立宪派几乎各占一半。12月2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议: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一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江浙集团声势大振,决定在南京组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并立即电催汉口代表东下。12月4日,陈其美(上海都督)、宋教仁(欧阳振声代表)联合程德全(江苏都督)、汤寿潜(浙江都督)及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运动各省留沪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召开共和联合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程德全、汤寿潜、黄兴及多数与会代表认为,五色旗“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此议发出,群以为是”。虽然这一议决因当时大多数代表尚在武汉而不具有完全效力,但它标志着“五族共和”已经成为革命阵营的政治共识。12月25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29日,会议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至此,“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在南方革命阵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另一方面,“五族共和”也是南北政治势力相互较量、议和妥协的重要政治纽带。袁世凯重新出山后翻云覆雨,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玩弄政治权谋,意在掌控国柄。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会议从18日到31日共进行五次,表面上公开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实际上在私下讨论的是由谁来掌握政权。革命党人屡次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大总统。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以君宪向南方讨价还价,以“五族共和”逼清帝退位,正好可收一石二鸟之效。于是,公开的会议成了例行公事,真正的会谈与交易是在赵凤昌寓居的“惜阴堂”进行的。当时,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以及因刺杀载沣未遂而遭监禁后被袁世凯释放的汪精卫等经常聚集在“惜阴堂”密商,就连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也来决策于赵”。几经周折后,双方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义”的协议。所谓“国民会议”,是南方要求坚持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双方达成了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的默契。
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地点是上海还是北京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之际,孙中山回国并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袁世凯随即恼羞成怒,一方面授意唐绍仪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一方面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连续通电抵拒共和,对南方进行武力恫吓,一时局势陡变,南北之间似乎又要开战。孙中山开始态度坚决,力主北伐,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议和之可言也”。但是,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扼杀,内有临时政府内部的分歧、涣散和既成的议和事实,孙中山无力回天,被迫妥协。这样,在1912年1月上旬,南北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南方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在逼清帝退位后建立“共和”政体。随后,袁世凯加紧逼宫步伐。此时的清廷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虽然有少数满蒙亲贵的顽固叫嚣及“宗社党”的垂死挣扎,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优待条件而宣布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日:“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政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字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退位,宣告了在
中国绵延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南北统一告成。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到会17省代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职,他在就职宣言中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暇秽,谨守宪法。”11日,《临时约法》正式颁布,重申“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南北统一,民国告成。4月22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称:“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从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双方虽然在政权问题上反复争斗,但对于“五族共和”的原则,双方并无疑义,相反,“五族共和”成为南北均加以认同的立国原则,成为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砝码和基石。
三、“五族共和”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的历史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仅历时三个月,但是在考察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问题时,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阶段之一。“五族共和”的确立,一方面是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到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初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法理基础。
近代以前,中国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除特殊的地理环境、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及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外,就是以“中国”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为核心的王朝认同,即代表“中国”的大一统封建中央王朝始终是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的最高形式和目标。近代以后,由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向现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转变,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辛亥革命前的七十余年里,围绕这一主题,不同阶级、阶层都进行了探索思考与实践。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及“师夷长技”,仅仅是中国人调整传统政治文化视野、重建传统国家秩序的一个开端。太平天国运动固然可歌可泣,但最终因近代历史环境的大变动他们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传统历史循环而归于失败。持续近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试图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军事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结果王朝中兴的美梦亦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破灭。继之而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在立宪改良的制度安排与设计中“平满汉之界”、“大民族主义”等具有一定的建设性的贡献,即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君主立宪国家来挽救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是维新派的努力由于自身的诸多缺陷和守旧顽固势力的反攻倒算而很快流产。而后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与清廷的“预备立宪”新政,只不过是旧式农民阶级的呐喊抗争与统治阶级的无奈挣扎。与上述历史环节不同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揭橥的“五族共和”,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结构方面还是在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方面,都有之前所不具备的历史重要性。一方面,它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它也结束了以王朝为核心的传统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赋予了“中国”这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以现代意义,正如日本学者所论,它“把帝国(清王朝)的复合性民族结构或重新构成为‘中华民族这一文化一国民共同体,并且把她与‘中国这一政治单位安排得恰到好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指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机枢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这里揭橥的,正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及其民族关系建构的形式与内容:一是以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共和政体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二是多民族的现代统一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三是国家领土主权原则,即“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从民族政治关系类型看,它也规定了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各民族政治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各民族既有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又有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责任和义务。随后,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经审议通过后正式向全国公布。在这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中,“五族共和”即民主共和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组织形式与原则进一步得以确立。《临时约法》在总纲中首先声明:“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民族关系与领土主权方面,其规定更为明确:“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总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五族共和”的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是上述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双重认同与整合的结果。在清王朝的基础上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方式重建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汉族)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初步完成了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也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辛亥革命虽然不彻底,但中国从清王朝统一到民国五色旗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战和民族分裂,委实是不幸之中之万幸。它反映出在近代国家转型中如何调适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华民族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底蕴又具有理论置换与创新的智慧。
四、现实困境:问题与局限
但从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的历史进程来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仍存在诸多问题和局限,并且面临严重的现实困境。
其一,“五族共和”仅仅解决了取代清王朝的民国是多民族国家而非单一民族(汉族)国家的问题,而对于国内民族关系的结构以及少数民族成分的认识是模糊的。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族汉族外就是众多的少数民族。这种关系,在传统历史话语表述中就是“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封建大一统理论。与之比较,“五族共和”虽然具有以民族平等构建国内民族政治关系的历史突破,但是与实际现状和内在要求相比仍然显得十分粗糙。它所谓的“汉满蒙回藏”,更多的是指“十八行省”与满、蒙、回、藏五个地域即五个地理单元,并不是清楚地指称民族成分及其政治关系格局,所以用来指“民族”确乎并不切当。现在看来十分明显的缺陷就是以满、蒙、回、藏来代替少数民族,不仅与国内民族关系格局的现实相去甚远,而且“五族”的框限也忽略了其他少数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权益,因而“五族共和”或“五族平等”又包含国内各民族不平等的形式和内容。对此当时就有不同的声音,如云南军都督府提出“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为一体,维持共和……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与国家关系与“五族共和”
已经有出入了。后来,孙中山也批评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同时,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国方针,“五族共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理论表述,强调的重心是民族同化而不是民族平等。虽然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迅速地由“排满”革命转向“五族共和”,与他们政治上模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模式一样,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同样没有完全突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其二,由于理论上的粗糙与局限,虽然“五族共和”成为建构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在具体认识与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以主体民族汉族政治精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阵营虽然确立了“五族共和”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观念浓厚,常常将“中华民族”与汉族混为一谈,将“五族共和”与汉族国家政权等量齐观,表现在实践中就是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即以汉族同化满、蒙古、回、藏等少数民族。孙中山对于以五色旗为国旗存在疑义,他在复函参议院时说,“贵会咨来决议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南北议和中南方将政权“渡让”给袁世凯,当时南方认为袁世凯是汉人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实践中,“五族共和”虽然被写进了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和《临时约法》,各种文告和讲话也屡次不离“五族一家”、“五族平等”等词句,而见之于有效、具体的制度安排却寥寥无几。更为严重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甚至是在实行一种民族同化政策。孙中山就设想实行“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当时各社会团体也以积极推进民族同化为宗旨。同盟会在其新修订的会章的“总则”部分中,就赫然写明“实行种族同化”。立宪派人士和少数旧官僚成立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假定政纲”中规定:“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中华民国联合会宣布改组为统一党后其政纲也规定:“融和民族,齐一文化。”黄兴、刘揆一等组织发起的“中华民族大同会”声明:“今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矣,微特藩属之称,自是铲除,即种类之界,亦将渐归融化……组织斯会,藉岁时之团聚,谋意识之沟通……相挈相提,手足庶无偏枯之患,同袍同泽,痛痒更有相关之情。”可见,民族同化成为具体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其实质是以汉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从而实现所谓的“民族之统一”。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尤其是政治地位相对较高的满、蒙对于“五族共和”的认识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同盟会“驱除鞑虏”的口号,给满、蒙古等少数民族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特别是他们的上层分子更是对革命共和疑惧重重;又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其政治发展水平亦还未达到资产阶级阶段。因此,他们在“五族共和”问题上同样存在不同的看法。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面临灭顶之灾,原来与满洲贵族联系紧密的蒙古王公纷纷活动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益,对于革命后国家组织形式十分关切。南北议和开始后,蒙古王公联合会致电南方代表伍廷芳称:“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同时,他们还组织勤王队,并发表通电宣称:“如朝廷允认共和,即行宣告独立,与中国断绝联系,以为君主立宪之援助。”对此,伍廷芳回电解释说,“民军起义之目的,欲和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自私自利起见,乃欲与满、蒙、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并保证蒙古在民国政体下的一切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使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倚。”清帝宣布退位后,蒙古王公的态度虽然发生了转变但仍然是有条件的,“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人大共和国家。”作为统治民族满族总代表的清廷在退位诏书中将南京临时政府“五族共和”的汉、满、蒙、回、藏变成了满、汉、蒙、回、藏,显然不是简单的疏漏,而是对五族中各自政治地位的不同表达,即虽然已经逊位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少数民族并且是曾经主宰中国260余年的皇族。
其三,由于外部因素的干涉和利用,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给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造成了诸多后遗症。辛亥革命爆发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极大关注。他们一方面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实行经济封锁,支持袁世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政局混乱之际在边疆民族地区制造分裂阴谋活动。在蒙古地区,在沙俄的策动下,哲布尊丹巴集团于1911年12月1日在库伦宣布独立,宣称:“本蒙古原系独立之国,是以现在议定仍照旧制,自行立国,将一切事权不令他人干预,业已行文撤销满、汉文武大小各官之事权,并令即日回籍。”12月28日,外蒙古成立“大蒙古国”,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同时,内蒙古地区也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12年1月,呼伦贝尔额鲁特总管胜福组建军队,占领呼伦贝尔,宣布“独立”,称:“大众议定,起大清国义军,保守疆土,决不承认共和,亦不受汉官节制。”此外,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哲里木盟郡王乌泰等内蒙古王公上层也在日俄等国的策动下积极筹划所谓“独立”、“自治”活动。在西藏,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传到西藏后,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局势大乱。在英国的支持唆使下,达赖喇嘛于1912年初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几近断隔。在新疆,沙俄在南疆制造“策勒村事件”,并以护商、护侨为名分别增兵喀什、伊犁、阿尔泰等边境地区。
上述理论上的粗糙、具体认识与实践中的大汉族主义传统思想和民族同化政策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严重危机等三个方面,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局限。虽然“五族共和”开启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新阶段,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它又是非常简陋而脆弱的,如同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存在多方面问题而仅存短短三个月一样。特别是袁世凯夺取政权后打着民国的招牌实行个人封建专制独裁,“五族共和”也成为一块有名无实的空招牌,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责任编辑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