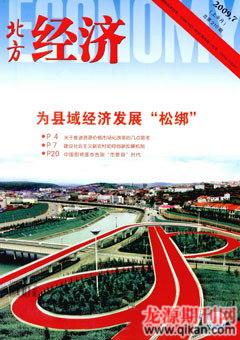解决“三农”问题的人口学思考
张 硕 王 曼
一、“三农”问题的本质
温铁军教授于1995年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在1996年发表的《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是产业的问题、农村是聚落的问题、农民是“人”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成因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在“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人口问题。
二、人口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人口与“三农”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是在我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站在人口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曾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以此来审视我国的“三农”问题,我们会发现,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并存现象。学者于学军指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或时期,是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地供养现存的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而过剩的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指制度本身要求发展生产力,需要减少过剩的人口,以便达到人口和经济的协调。
“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解决起来规模大:再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和复杂。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综述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在哪里?把社会学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解决的措施有破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身份的不平等、彻底进行县乡机构改革及国家财政政策对农村的倾斜等。
樊纲教授综合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以及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显然,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则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把2.15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亚洲的经济巨人。
(二)几点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严格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方针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
1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说到底,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如此下去,农村人口将继续增加,将会减慢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速度,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绝不能放松的。但中国的人口减少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在此之前只能是暂时缓解,而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就人口总量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学者李建新就坚决反对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年后中国人口降至3~5亿。其反对的理由:一是对于我国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及对生育率准确性的质疑:二是一般学者往往用“分母效应”分析人口数量问题。“分母效应”隐含着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往往被夸大了。李建新为此主张不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并强调以放宽和放开二胎来达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最佳结合。
2人口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
要解决前文提到的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实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增加土地。要么减少人口。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只有减少耕地上的农民数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要“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及“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等主张。这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学者于学军提出主要的途径应该是就地城镇化,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商业,它必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相适应。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时不能大量涌向物质生产部门。要坚持以第三产业为主。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下表为1996-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基本变化情况。很显然,这10年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稳步提高,已进人中期阶段(城市化率超过了30%)。这同时也是一个加速阶段,未来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同时也多次表示:城市化未必能解决“三农”问题。他指出,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无论是墨西哥、巴西还是印度。那里的所谓城市化基本上是靠大型贫民窟实现的。就算是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不能解决其“三农”问题。在日本,95%以上的人口都已经城市化了。但是日本农村不是在衰败吗?可见,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农村人口结构问题重要环节
在人口老龄化、农村趋向城市化的今天。处于社会保障网之外的农民,迫切需要一个社会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来保障其老有所养。土地是农民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是保障之本。没有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城市化就是空谈。
中国老年人口有近60%分布在农村。我国政府立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着手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土地保障和家庭赡养功能。《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发挥土地养老的保障作用,保护包括广大老年人在内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倡签订“家庭赡养协议”,规范赡养内容和标准,由村(居)民委员会或有关组织监督协议的履行,以保证老年人享受赡养扶助的权利。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开展了“家庭赡养协议”签订工作,到2005年底,已签订“家庭赡养协议”1300多万份。此外,中国还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保障制度,把农村特殊老年群体优先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白皮书还指出,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当年支付养老保险金21.3亿元人民币。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府缺位和农民缺钱交不起保费这两个主要问题的存在,使得处于试点中的不具备社会性的农村养老保险曾经出现了停顿中止的现象。为了减少一般财政税收的压力,关于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还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渠道进行特殊筹资:在全国范围开卖计划生育彩票以及推行小额柜台式机器自动付款博采(可参照美国的方式)。并将除福利彩票以外的所有其他现有彩票收入全部归人中央计划生育奖励基金。
四、结论
总的来说,上文提到的几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将人口控制、农村社会保障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措施。从在人口学的视角,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严格贯彻这项综合措施能够加速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加速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由此加速促进城乡平等的进程等等。
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学者开出的药方往往很简单,实际上照搬过来并不能用。在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农”问题的解决一定要纳入总体发展的框架中。特别是要与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的发展联系起来。合理的制度设置将使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