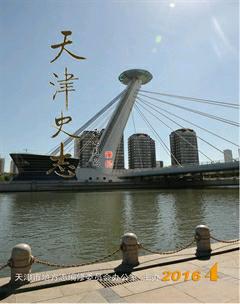天风海涛 爱国壮举
徐勇


摘 要:在对相关史志资料进行挖掘和分析以后,得出清代水师巡航南海的动议和尝试均自天津肇始的结论;1909年广东水师巡航南海的壮举中包含了各种天津元素;广东水师巡航南海行动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张人骏和李准,都以天津作为最后的人生归宿。
关键词:史志资料;天津大沽;水师巡航;南海主权
南海及其所属岛屿是由中国人最先发现的、主权归中国所有,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我国历代文献中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及至清代,更有派水师舰队到南海巡航,宣示中国主权的壮举。
在清代巡航南海的行动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天津始终扮演着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关键作用。本文试根据有关的史志资料,从三个层次对此进行评介。
上篇:策划与实施:清代巡航南海的动议和尝试均自天津肇始
据初步查阅,清道光年间的天津志书《津门保甲图说》[1] 中即提出:“古人筹海之方,谓必哨贼於远洋不常厥居,则彼之趋避无准,击贼於内洋而勿使近岸,则我之藩篱自固。”“……溯自二十年七月至今,天津陈镇委员弁乘坐哨船出洋远探……”这两段话又见于《直隶总督讷筹议章程奏稿》。另外,天津人王守恂(1865—1935)所著《天津政俗沿革记》[2] 卷十四“水师海军”节记有:“嘉庆二十二年,大学士筹议:天津添设水师,分左右两营……鸿章莅津设建水师之议,倡于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元,鸿章设水师于三岔河口,复于户部拨给各关洋税银,订购铁甲舰,此北洋海军之所由始也。光绪二年,购得龙骧、虎威,其后逐年续购炮舰镇北、镇南、镇东、镇西等,以资号召,并蚊船铁甲等件,并建造船坞于大沽海口。七年,又定购巡海快船兼碰船二只,一曰超勇,一曰扬威,由是北洋声威远届海上矣。”
从天津的这些史志资料中可以看出,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有在天津扩建水师和“哨贼於远洋”、“出洋远探”的动议,这也是中国人海权意识的最初萌芽。而到了清同治末、光绪初年,北洋水师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以天津大沽口为集散地和始发地的布局,“由是北洋声威远届海上矣”,为出远海巡航做好了准备。
有了策划和动议,还需要行动来实施。在天津地方志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四年(1878)六月二日,“李鸿章与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等,在大沽观看由南海巡哨来津的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四艘炮舰演习。随令留防大沽、北塘洋面,每月各巡两次,四舰于光绪六年三月离大沽,调赴南洋巡防。”[3] 这在清代水师巡航南海行动中是最早的,比后来李准率广东水师巡航南海早了三十余年!此次巡航在天津地方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堪称首创之举。
诚然,问题还是存在的。首先,由天津出发的北洋水师,“出洋远探”的半径有多大,天津距南海遥远,北洋水师续航能力能否抵达。其次,前引史料所说“由南海巡哨来津”中的“南海”与现在南海的空间概念是否完全一致。最后,北洋水师的巡航行动为什么在南海所属各岛屿中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这些确实都需要进一步挖掘资料、深入研究。这里笔者先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第一,直隶总督衙门虽然府址设在保定,实际办公地点却在天津海河的三岔河口。在北洋水师的创建方面,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清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一日,“李鸿章奏议:各省交存天津军饷制钱百余万串,不再提解户部……拟将上年天津关交京饷洋税十五万两截留,以备扩军。”[4]李鸿章等人在津利用其影响力解决了北洋水师购买多艘大型舰船所需的经费问题。
第二,清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二十二日,“福州造船厂造‘镇海轮由把总陆伦华驾驶,运赈米到津。李鸿章派陈钦、沈保靖前往查阅,拟请留用,与‘操江轮轮流在渤海湾巡哨。”[5] 清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二日,“赫德代购自英商阿摩士庄厂制造的炮舰二只,驶抵大沽,李鸿章亲赴阅看演试,授名‘龙骧、‘虎威号。”[6] 清光绪五年(1879)十月六日,“李鸿章等到大沽,对新购英制四艘炮舰进行验收,并以沈保靖拟定之‘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命名,派管带邓世昌暂行接管。”[7] 清光绪七年(1881)七月十七日,由赫德为南、北洋代购的英商阿摩士庄厂制炮舰八只,其中北洋二只驶抵大沽口,水师营務处道员许钤身、船炮游击刘步蟾……前往验收,命名‘镇中、‘镇边号。”[8] 清光绪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购自英国的快船二只,由丁汝昌驾驶抵大沽口拦江沙外。十月二日,李鸿章派海关道员周馥、道员马建忠、知府薛福成及周盛传等出海验收,驶往旅顺。”[9] 清光绪八年(1882)八月十六日,“李鸿章奏报:驻守北洋各口舰船二十二艘,其中驻天津海口有‘操江、‘镇海、‘镇东、‘镇南、‘镇西、‘镇北等六艘。”[10] 清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十一日,“李鸿章带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海关道周馥在大沽口查看验收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铁甲舰。”[11]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购自英、德的铁甲快船‘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由管带官邓世昌统率,自厦门驶抵大沽口,李鸿章出海察看。”[12] 清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十六日,“北洋海军建军三年第一次校阅,李鸿章率周馥、刘汝翼等视察,五月三日返抵大沽。”[13] 这些史志资料足以说明,北洋水师是当时清海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号称“亚洲第一”。大沽口是其主要支点,几乎所有舰船都先到天津领命、接受检阅,再驶向其他地方。
第三,上述史料也说明了,至少在清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即1872至1894年的二十余年间,以天津大沽口为起点的北洋水师舰队,已经具备了巡航南海的所有要素和条件。
第四,前面所引资料还可以证明,北洋舰队根据需要在天津与南方各港间经常有调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则更多地是驶往广东。原属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巡洋舰,就因军情所需被调到北洋水师。因此,天津虽然距离南海遥远,北洋水师完全有能力抵达。舰队可以先在广东等地停靠,再行巡航。佐证之一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北洋舰队就曾开赴日本等国访问。佐证之二是,清左侍郎郭嵩焘于光绪二年(1876)访问英国时,所乘舰船就曾途经西沙群岛。
第五,前文记述,清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二日,李鸿章亲赴大沽阅看赫德代购的两艘炮舰演试,授名“龙骧”、“虎威”号。此后这两艘舰不在大沽,去了哪里没有记载。而约一年半后的光绪四年(1878)六月二日,李鸿章等人又在大沽观看“由南海巡哨来津”的这两艘舰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另外两艘舰飞霆号和策电号,这两艘舰此前从未在北洋水师序列里出现过,显然来自南方,应当是同龙骧号、虎威号两艘舰一起完成了巡哨任务后来到大沽的。从一年半的时间来推断,上述四艘共同赴南海巡哨是合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舰于光绪六年三月离大沽,调赴南洋巡防”。
第六,北洋水师于清光绪初年巡航南海的行动,至今没有在所属岛屿中发现可以直接印证的痕迹。但是考察历史问题言有易、言无难,早期的巡航也未必刻意留下痕迹。因此,没有发现不能证明绝对没有,更不能否定巡航南海事实的存在。后来近三十年间,清军水师南海巡航间断,而日本等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伺机登上某些岛礁,把有些痕迹毁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后来在东沙岛上就有过类似的情况。
总之,以天津大沽作为主要支点的北洋水师巡航南海,史志资料是有明确记载的。虽然有些问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但是目前毕竟没有任何材料和证据可以否定它,更不能排除北洋水师巡航南海的可能性!这些尘封已久史料的被发掘,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全新的重建和认知,始于天津巡航远洋的动议和“巡哨”南海的行动,堪称壮举。而这个历史问题的被厘清,充分彰显了地方史志“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也为天津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荣耀。
中篇:人员与器材:广东水师巡航南海行动中的各种天津元素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的海防战略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外逐层设防。第一层是天津、旅顺、威海,由北洋水师镇守;第二层是长江、浙江一带,由南洋水师镇守;第三层是福建、台湾,由福建水师镇守;最外一层是广东,由广东水师镇守。当时清朝主要的力量都集中于北洋水师的建设,最不受重视的广东水师只能依靠地方自筹经费来发展,因而实力最弱。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八日,日军攻陷威海,北洋舰队在黄海大战败北后又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一度声势煊赫的水师仅存“康济”号一艘练习舰,已无任何远巡能力。这样,再次巡航南海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广东水师的身上。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群渔民发现东沙群岛的一些岛屿被日本人占据了。清政府马上电告负责管辖这一海域的两广总督张人骏,要他查明情况。据保存下来当时的电文,可知张人骏一面派人搜集东沙群岛的有关史料,一面请南洋大臣“酌派大轮往查”。而具体率舰去东沙巡查的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14] ,他了解到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配有刀枪的日本人登上东沙群岛的主岛东沙岛。他们一上岸就驱逐了中国渔民,将岛上天后庙、兄弟所、百余座坟冢全部拆毁焚烧,企图消灭有中国人在岛上活动过的痕迹,其头目西泽吉次不但带人窃取岛上积存的鸟粪,还用他自己的姓给东沙岛起了个日本名“西泽岛”。
李准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回省商之张安帅”,张人骏向日本驻广东领事濑川浅之进提出照会:“东沙岛系隶属广东之地,请谕令日商即行撤退。”[15] 但濑川的答复是该岛为无主荒岛。谈判陷入僵局。要想证明中国对东沙岛的主权,必须拿出可靠的根据。虽然张人骏在给外交部的电文中抱怨:“中国志书,只详记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但是最终解决问题还是靠地方志等资料。清王之春著《柔远记》、陈伦炯著《海国见闻录》等都对东沙岛有明确记载,并附有地图。再加上英国所绘《中国海总图》,证明东沙岛属于中国确实无疑。经过反复谈判,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收回了东沙岛。
也是在1909年,李准又奉张人骏之命,率伏波号、琛航号巡航南海。因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本文对此次巡航的过程从略。需要重点介绍的是这次行动中的天津元素。
(一)人员补充。海军是专业性极强的军种,清军的水师将领,要么出身于专门的学堂,要么留学欧洲归来,可谓术业有专攻,而李准显然并不是一个谙熟水师专业的军事人才。1905年夏天,时任清南北洋海军统领兼广东水师提督的叶祖珪,从南京沿江而下视察江防时染病死亡。此后不久,李准接任了广东水師提督,这颇有一些“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意味。不过,正是这位十足的外行水师提督,却带着两艘老旧的军舰,为飘摇之际的清政府赢得了又一次荣光。当时的情况是,虽然东沙巡探给李准增添了几分信心,他在日记中所写:“余极欲探其究竟”,反映出其急切的心情,但是实际上广东水师对远赴南海巡航的任务却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急需补充一批具有远航能力和经验的专业人员。李准把目光投向天津来寻求人才,可以说是理所应当的必然之举。
而天津这边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几条史志资料:清光绪二年(1876)九月十四日,“已调来津驾驶炮船之严复等二人,因福建船政局派出洋学生缺额,同意严复等二人仍回闽充数,出洋留学。”[16] 清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四日,“在东局设天津水师学堂,聘英官教练,设驾驶、管轮两班,学习英语、地舆图说、算学、驾驶、测量、化学、格致等课程。”[17] 清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天津武备学堂开设于法租界水师营务处……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科。”[18]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四日,“被日本败于营口来津遣散的清军三营,因饷粮未发,哗变。”[19] 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日本遣送被俘清军978人至大沽,天津总兵罗荣光、大沽协副将韩照琦用驳船运至新城,点名验收。”[20] 这些史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水师学堂等军事学校纷纷在天津建立,培养了一大批海军方面的人才。有的留在天津,有的效力北洋水师,也有的去往全国各地;二是甲午战争后,不少水师官兵或被俘遣返,或遭裁撤而生哗变,迫切希望有机会能得到继续招用。
此时全国的情形也发生了剧变。清政府不仅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及海军内外学堂全部停撤,其后将北洋水师的武职官员,自提督以下也概行裁撤,士兵一律遣散。加上经过了义和团事变,清军水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才,除战亡者外,幸存的大都散落在天津等地,不仅报国无门,生计也无着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作出的推论是,广东水师从天津等地招聘了原北洋水师的一批专业人才。换言之,李准1909年巡航南海的行动之所以顺利完成,是因为有这些来自天津等地、原属北洋水师、具备超强航海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才做支撑。据记载,李准率领巡航的官兵有170余人,其中多少来自原北洋水師尚不得而知。但李准的主要助手、被任命为“左翼分统”的林国祥就是原北洋水师的将领。
(二)设备器材购置。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顺利完成巡航南海这么大的行动,人的因素固然是第一位的,没有必要的设备条件和器材硬件也是不行的。而当时广东水师准备派出巡航的舰队,是由伏波、琛航两舰组成。这两艘木壳军舰原属于福建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江之役中,伏波号被击沉,琛航号负伤搁浅,后来捞起修复,转给了广东水师,设备落后,器材不全,仅能勉强使用而已,迫切需要补充大量的专业仪器和先进设备。
据李准本人明确记载[21] ,除一些常规设备在广州解决之外,重要的专业器材如海上定位仪、经纬仪、英制测距尺等均从天津购置。天津距广东不近,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据有关史料记述,清同治六年(1867)三月,“天津机器局在海光寺设立”[22] 。清同治七年(1868)二月中旬,“天津机器局新址在河东贾家沽勘定(后称东局)”[23] 。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二日,“清政府命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24] 。清光绪四年(1878)七月二日,“李鸿章奏报:天津机器局已能制造火药、铜帽、水雷、士乃得后门枪……”[25]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五日,“北洋设洋务局于天津”[26] 。由于天津相关机构设置较早,拥有在全国最多的军工生产基础部门,能加工和进口更多、更先进的器材,加之人员熟悉。因此,广东水师巡航南海前重点从天津补充设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三)李准、张人骏与天津的关系。李准舰队的巡航南海行动,勘查了岛屿十五座,并逐一命名。勒石立碑、升旗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李准回广州后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于1910年刊印。还举办了展览,在当时影响很大。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1911年,宣布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
据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二日,“(天津)广东会馆举行落成典礼。”[27] 说明当时广东上层官吏与天津交往密切。从前面所述巡航南海行动中人员和器材的补充以及后来张人骏、李准到天津做寓公的事实,都使我们清晰地看出:他们俩人都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和不解之缘。
下篇:偶然与必然:两位巡航南海关键人物在天津的最后归宿
历史的进程中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偶然中又往往蕴含着某种必然。值得我们关注并写上一笔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偶然还是必然,前述广东水师巡航南海行动中的两位关键人物:张人骏和李准,最后都殊途同归地在天津找到了他们人生的归宿。
先说张人骏。他生于1846年,字千里,直隶丰润县人。作为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对李准等人巡航南海给予了鼎力支持,他还出面与外国人针锋相对地谈判,向清政府多方致电周旋。李准巡航成功归来后,张人骏“惊喜欲狂”、说“从此我之海图又增入此西沙十四岛也”。他还向清廷奏报,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此后不久(1909年),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的南海巡航计划也随之搁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先是从南京逃到青岛闲居,后又举家搬至天津,1927年病逝,享年83岁。
再说李准。他生于1871年,字直绳,四川邻水县人。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他,除有率舰队巡航南海的壮举外,其个人经历也是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在那个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代,李准开始是顽固地站在清政府一边的。他先后率部镇压了1902年的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等,可以说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也深为革命党所恨,屡遭刺杀、两次受重伤。
据说李准的变化是在1911年。一方面是因为,当他审问在黄花岗起义中受伤被俘的林觉民时,被林的革命气概所感动,亲手解开镣铐、为其捧茶;另一方面是因为,后任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对李准颇多猜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李准命令部下挂起白旗起义,迎接胡汉民前往广州就任都督。他还派员说服在惠州城与陈炯明军激战的清军陆路提督秦炳直开城投降。当年底,胡汉民辞去广东都督时,在文告里对李准在广东光复中的作用予以了高度评价[28] 。1912年10月,李准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任高等军事顾问。1916年,他毅然弃袁、离开官场,次年到天津隐居。
在津期间,李准的活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书法,尤擅篆隶,曾为《大公报》题过报名。二是交友,天津名流杜宝桢曾给李准写了一副龙门对:“行路有何难?我曾从天柱、九嶷、三涂、太室、紫阁、终南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师真不易,所愿与高堂、二戴、安国、子长、相如、正则同依东鲁圣人家。”三是京剧,曾为金少梅编写了《画中缘》等剧本。四是著述,李准日记的全本和他所写《巡海记事》等文献、图照均已在战乱中佚散,令人遗憾。但《大公报》和《国闻周报》1933年曾选刊过李准的日记,题名《李准巡海记》,还有前文谈及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等,均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五是关心国事,1933年7月,法国以公告形式宣布占领太平岛、中业岛、南子岛等九个小岛,并擅自“定名”,这就是南海历史上有名的“九小岛事件”,当时李准曾亲赴天津国闻周报社讲述自己巡航南海的经历,并提供翔实资料,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成为中国对南海诸岛屿行使管辖权的直接证据。
李准1936年12月22日去世,享年65岁。为了纪念他在巡航南海中的重要贡献,后人在他的出生地四川邻水县修建了李准公墓。
以上我们根据史志资料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考证和评介。在本文结束之前,还必须面对两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清代水师巡航南海的行动中,天津是否发挥了首创的、独特的作用?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第二问题:在史志资料中能否找到明确记载,为上述结论提供可靠的证据?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这正是:
水师巡航南海,扬我军威国威,
宣示主权壮举,天津与有荣焉。
注释:
[1]此书两函十二册,不著作者。第一函第一册写有“道光丙午年新镌”,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
[2]该书1933年定稿,直到作者去世之后,才由其继室黄夫人“为偿其志,以节衣缩食之资……俾该书得以问世。”
[3]~[13][16]~[20][22]~[27]《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14][15][21]参见《大公报》连载《李准日记》的部分内容、《国闻周报》1933年8月21日第十卷第33期所刊《李准巡海记》等文献资料。
[28]《胡汉民宣布李准反正实情始末书》指出:“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
(作者单位: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规划研究处)
【作者附记:本文是受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委托,为参加“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论坛报送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关树锋主任的大力支持,南开大学吴振清教授提供了一条线索,某些内容与陈兰义、张岩、沙洵同志进行过讨论,特此说明,并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