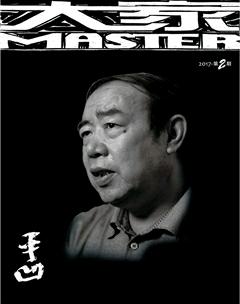大象,骷髅与罐子
我还记得自己获得的第一个小说类奖项。初升高的暑假,在高中的百度贴吧闲逛,看到征稿启事,写出四五千字的“小说”投了过去。高中开学后,他们把获奖名单贴到公告栏上,我拿到了小说组第一名。他们搞错了我的名字,把“修新羽”写成“修新宇”,所以同学都不太相信获奖的居然是我,而是某位名字恰好和我相似的学长。
我还记得自己后来加入了校刊,经过两年努力成为主编,拿到了那串能打开资料柜的钥匙,终于有机会看到每届征文比赛的评委打分和评语。评委说,感觉我在尝试创作自己还无法驾驭的东西。“还无法驾驭,但假以时日或许能成功。”整个会议室里只有我一個人,站在窗户旁边,就着傍晚时分昏暗的天光仔细阅读着那张薄薄的纸,茫然多过激动。
那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基本都是在课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拓展。也就意味着,基本上都是四大名著,列夫·托尔斯泰,契科夫,鲁迅,对先锋派和后现代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小说”对我而言是太过厚重遥远的东西,只配印在课本上,让所有年轻人强制阅读一万遍。对十三岁的我来说,往自己的作品里也塞入那些“厚重遥远”,未免太缺乏自知,太过贪婪。然而野心摆在那里,只要方向是对的,日复一日,终究还是能离目标近些。
从最早的那篇作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
起初年纪小,想的多半是分数,应试教育,少女情怀,写的东西都发表在《萌芽》上,基本是同龄人在看。后来在清华读了哲学系本科,又修了新闻学双学位,想得越来越杂,写得也越来越杂,科幻、战争、校园,诗歌、剧本、散文,什么题材什么体裁都想去试试,可以说是兴趣广泛,也可以说是心思散乱。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着写作的才华。在我看来,那些最优秀的小说家多少都有点儿病态,至少是有着过于强烈的窥探欲和袒露欲。村上春树在那篇著名的获奖感言中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他相信小说家应当永远站在弱者那边,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未免也太偏执了。我觉得小说家两边都不站。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们一旦深陷在细枝末节中而缺乏冷静思索,就会很容易忘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而小说家就应当承担着“审视者”的角色,他会提醒狂热的鸡蛋以毁灭的命运,也会提醒高墙以鸡蛋的狂热,他的审视和他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家站在自己那边,他是鸡蛋与高墙的敌人,也是鸡蛋与高墙的盟友。
英文里有两个俗语,“房间里的大象”和“柜子里的骷髅”。前者说的是人们对众目睽睽之下的某些事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后者说的是受人尊敬的人或家庭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可怕秘密。小说家所描述的,就是这头“大象”和这具“骷髅”:他要替所有人承认,替所有人忏悔,最终,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替所有人争取到救赎。
而从更为私人的角度出发,小说亦是一个储存东西的罐子。某个情绪,某句话,某个人,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想把他们记录下来,又不能让他们看起来太突兀,所以就编制出了不同的小说,讲了许多句子,花费了很长时间,只希望他们能出现在最恰如其分的位置。
我尝试过用更为精巧的结构和语言来创作。我尝试过用失意的、抽烟酗酒的中年男人的口吻讲故事。不过是在罐子上描绘花纹,或者制造点儿陶土罐子,玻璃罐子。它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封存起了我的一部分生命。
《不仅是雪》里波士顿的暴雪,我遇到过。《逃跑星辰》里孩子之间的排挤与竞争,我参与过。我只是习惯于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琐碎生活……如果有人愿意读完我的每篇作品再来注视我的眼睛,就能够完完全全了解我的一生。
而我不愿仅有一生。
高二时半夜窝在被子里,读了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多年来清楚记得这句:“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海德格尔宣称,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诗意在这里是一种超出原本生活之上的审美境界,是信仰,也是渴望。
而我们期待的,正是像所有伟大文学家所做成的那样,用自己的方式命名万物,让终将消亡的所有记忆都变得更有意义。
我想这就是我阅读小说和创作小说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