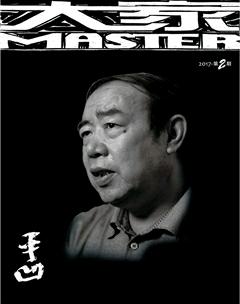批评家不是看人脸色写作的
谢有顺+魏微+张莉

好批评要实现与文学的真正对话
谢有顺:下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在这样一个小型场地里,我们温馨地聚集在一起谈文学,谈一个批评家对作家的理解,是很有意思的活动。张莉教授是我打心里喜欢、敬重的批评家之一,她的文章写得好,影响大,有自己的观点。很多人都知道批评著作已经是非常小众的读物了,但很多作家都在我面前提张莉教授的《持微火者》。并不是说张莉表扬了他的缘故。因为有些作家,表扬不能让他高兴,批评也不能让他愤怒。曾经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和我说,某个人批评我,我感觉他像在批评别人,某个人表扬我也像在表扬别人。说得不准确,没有理解作家的作品,没有实现与作品真正的对话,你说好说坏作家都无所谓。但是,张莉教授的文字让很多人钦佩。这不是溢美之词。她的批评实现了与作家灵魂的交流,让作家觉得有一种遇见了知己的感觉,这是对批评家最高的褒奖。当然,批评家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被作家认可,但是能否实现和作家的对话还是很重要。《持微火者》是一本让作家觉得有知己般感受的书,也是一本能让读者对批评文体重燃热情的书。这本书现在很受关注,销量很好。但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作者是如何理解作家作品的。
张莉:谢有顺老师虽是同龄人,但其实是前辈,我上学的时候就读他的文字,而在我最初写评论的时候,他偶然看到我写的东西后就写信鼓励我,还把我的评论推荐给很多同行。这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想想看,你以前阅读和尊敬的批评家,在你最初发表文字时就赞扬你,并且找许多机会让你的文章和更多人见面,这很难得的,我非常珍惜。魏微老师是很好的小说家,我很早就读她的小说。2009年我们认识,见面不多,但每年都会通几次电话,讨论文学问题,关于小说的,以及文学评论的,非常直接和坦荡,内心里很亲近。坦率说,我们是彼此见证,一起成长的。
《持微火者》这本书,像谢老师说的,是有一个契机。我读博士的时候做的是现代文学,博士之后做当代文学的时候,我在想应该用什么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应该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那时候是2007年,我一边读一边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等我整理成文章想拿去发表时,发现很困难,因为不是很严格的学术论文,评的也不是最新作品。所以这些文字一直在抽屉里。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名作欣赏》的时任主编续小强先生说他们2013年要开一个专栏,系统地向《名作欣赏》的青年读者介绍中国当代作家,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于是,2013年的时候我开了一个专栏“张看”,这样就有了前12篇的系统发表,包括莫言、贾平凹、余华、铁凝、王安忆等这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专栏发表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他们都喜欢这种文体。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徐晨亮先生希望我能出版这些文字,但是我们也都觉得,当代文学的面貌不能只是这些成名作家。——当代文学现场既包括成名作家,也包括正在成长的作家。因而,批评家一方面要关注已经成名的作家,另一方面也要发掘没有成名、处于边缘的写作者。批评家评价的作家后来进入了文学史成为作家,这是工作的意义,但还有可能你选择的作家随着时间流逝没有了,那么,很可能证明你这个批评家的眼光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批评的风险,也是批评的挑战。我开始关注另一些作家,要跟时间博弈。我做的批评工作是否好,就再过几十年让时间来检验吧。因此,我用了三四年的时间,陆陆续续把其他十二位作家面孔勾勒完整。我希望这25张面孔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向。因此,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成名作家,第二部分我自己认为有潜力的作家。
之所以用“持微火者”做书名,缘于我对写作的理解。在我眼里,每一位作家手里都有个神奇的火把,它吸引读者一起闯进晦暗之地。最初,读者往往被那些最耀眼的火把吸引,但慢慢地,我们会发现它的刺目。我更喜欢微火,这是我的个人趣味使然。微火的姿态是恰切的,它的光线也更适宜。读者有机会观察被微光反射的作家面容,注意到他的脸上有隐隐不安划过。另外,名字还有另一个意思,大家知道,很多人認为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做当代文学批评的时候不免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有困扰。有句话给了我很大信心,是鲁迅先生在1919年写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这跟“微火”的意思很相近——虽然我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是希望自己的一点工作寻找到一些同路人,这是我对书名缘起的介绍。
魏微:很高兴今天作为嘉宾与大家分享我读《持微火者》的感受。张莉老师是近十年来当代文学一个非常活跃的批评家,她的文章我很喜欢,首先是好读,一般我读学院派的文章读不下去;当然,我也是谢有顺老师热烈的读者。他们虽然是做批评的,但是他们的文章可以当散文来读,张莉在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她追求生动亲切的文字。因此,她的写作是有点靠近随笔的。我是写小说的人,读他们的文字,一个总的感觉是很贴,与文学、文本都很贴近,就是我们惯常讲的说人话,有常情,而不是那种很概念化的、大而化之的文字。我和张莉一年里总有几次通话,聊创作,聊批评。她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八股腔其实是有不满的,因此《持微火者》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对当今流行的“学院派”批评的一个纠正。我是不久前才知道,张莉早年写过小说,也发表过,直到现在,说到文学的时候,她都怀有赤子之心,她是我很喜欢又觉得很亲切的一个批评家。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是个很懂的人,懂人、懂生活、懂世情。而这些,无论是对于写小说还是做批评都是很重要的。一代批评家有一代批评家的责任
谢有顺:作为同行,我觉得张莉的努力很难得,对那些经典的作家或者体量大的作家,要在五千字左右篇幅,以个人感悟的方式说出对他们精准的感受,并且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是很有难度的。好比现在大学里面要做关于鲁迅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是很难的,因为鲁迅的作品都被人充分研究过了,像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人,他们的研究文章无数,相关研究论著也有数十本之多。这种情况下,张莉依然有自己的角度,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新见,非常难得。说实话,一篇短的文章要有概括性,要精准地把一个作家的整体特征,包括作品中表现出来很特质的东西说清楚,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另外,要将更年轻的,还在上升通道中的年轻作家写好也难度很大。要为一个新的作家塑型,或者把潜藏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以恰当的定位,这是有风险有难度的,这方面我觉得张莉也做得很好。她能够以一个同时代人的角度,甚至抱着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态度来理解这些作家。我个人觉得这更见才华,也更有意义。我的老师陈思和教授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愿意选择和一代作家一起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批评家。要求批评家评论、关注所有作家是有难度的,但是选择和一代作家一起成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以及彼此的援助,是很重要的文学生态。
坦率来讲,今天很多批评不受尊重的原因是批评家什么都敢评,什么都能评,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那时的批评家,比如一些年轻批评家,只选择年轻的先锋作家来研究,传统的作家作品他肯定是不评的。他有选择。但现在的批评家不是这样,不太选择,只要是熟人,出版社找到了他,他就写批评,这是文学批评的另外一种危机。现在电视上的嘉宾很多是无所不知的人,无论讨论什么话题都是那个专家,什么都可以讨论,什么问题都敢发表意见,这种无所不知其实是很可笑的。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有限是非常好的品质。所以我欣赏张莉对同代人的关注,我鼓励她多写同代人,多评年轻的作家和正在成长中的作家。
张莉:关于前面十三位作家,难度在于写作之前要翻阅大量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虑自己怎么写。五千字内怎么写莫言和贾平凹这样级别的作家,这的确是挑战。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时候,我和陈思和先生有个对谈,他说,他注意到我写的50后的作家时使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他们的节点作品、从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入手,他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我说是的,就是这样。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是承前启后的作品,我就谈它,由此连接作家的前面和后面的创作,莫言的我选择了《生死疲劳》。我不可能在短的篇幅内囊括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那么,我就选择一个视角谈我的看法,找到属于我的路径。
刚才谢老师说“塑形”这个词语,我很喜欢。面对新锐作家的困难是,没有人谈论过他,没有人给他评论的时候,你要“塑形”。这要求批评家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敏感性,好在我有一些文学创作经验。但是,我写的时候,心里也是有压力的。我怕自己把握不准确。我现在做批评家时间长了,很担心自己的尺度有问题。比如,当我给作家一个评价,——这个作家到底好在哪儿,特点是什么,我更多要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批评家的虚荣心。作为批评家,我要时刻与我的虚荣心进行搏斗。比如,所有人都夸奖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个人会站出来说这个作品不好,这很容易博得掌声和喝彩,这些人被称为勇敢的人,我敬畏这样的同行。反过来,当别人都说不好的时候,你说它好,这也是一种勇敢。问题是,你的评价是出自对这个作品的真实判断,还是为了显示和别人的不同?如果真的是出自本心的判断,那么非常值得尊敬;如果只是为了与众不同,为了刷存在感,那么,你对得住这部作品吗?所以,我写新作家、新作品的评价时,常常要问自己,这个作品是否配得上这个赞扬,或者你对这个作品的批评是否言过其实?我常常要这样问自己。
今天的批评家和前辈相比,面临的障碍和困难越来越多了。这个障碍首先是如何给作品一个准确的定位,比如,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把这本书放在文学史框架里面怎么判断。另外,随着传媒的发达,国外作品很容易传到国内,几乎是同步。那么,一位当代小说家写了部很好的作品,你作为批评家禁不住赞叹,——那有没可能是他受了国外电影或者小说影响?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国外小说和电影,你很容易就把他夸得天花乱坠的。我觉得,今天对批评家的知识储备要求越来越高了,不仅要关注当代文学,还要尽可能把阅读范围扩大,包括影视艺术的观看经验,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之内才能给作家准确定位。这很难,坦率说,这是我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文学批评说到底是一个披沙拣金的工作,不断淘汰沙子,最后才能捡金子,我们一般是这样理解的。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以为捡到的是金子,但有可能50年后依然是沙子……但是,50年、100年后很可能你撿到全是沙子你就不做这个工作吗?也不是。我有个看法,一代批评家有一代批评家的责任。每一代批评家都有自己理解的角度,我写的只是我作为同时代人的理解。未来,再年轻的一代怎么评价莫言和贾平凹,那是他们的事情。人类文学的进程,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一个一个台阶组成的,不是说一开始的人就是登上顶峰的人,不是的。每个人都是台阶之一,我的目标就是争取成为台阶之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魏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批评,这话我喜欢。我和有顺、张莉算是同龄人,今天一块聊天,很美好,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自己人的意思,就是刚才有顺讲的,是看着彼此在成长,在变化,可能这些变化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因为懂得,所以有体谅,有包容。自己人坐在一起,常常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因为成长背景是一样的,在这个背景下长成的人、形成的文字,无论多么千差万别,内里还是能找到一个总的解释的。可能我们之间也会有批评,甚至这种批评比对隔代人的批评来得更苛刻、更挑剔,可能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就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希望身边人能做到,批评到最后,其实身边人也做不到。到了这时候,大家就会坐下来找原因,聊根源,我觉得这是好的。我记得张莉对同代作家就多有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满于我们这代人普遍地回避社会生活,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致,当然更谈不上责任心。我们多是日常视角、个人视角,说得好听一点,文字是向内走,看上去很“内向”,自然就少了点恢宏气象。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可能要牵扯到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青少年时期所感受到的时代审美、所接受到的精神风向标等。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是,张莉是一边批评,一边体谅,她批评得越严厉,她体谅得也就越温柔,因为她是我们的同代人。
张莉:在上海和陈思和老师谈到50后作家的时候,气氛很融洽,因为有很多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作家,但一旦说到70后、80后作家就比较严肃了。他说社会问题那么多,为什么50后作家看到了,而70后作家没有看到。这是不是70后作家的问题?我说文学环境发生了变化,大家对好的文学标准不一样,50后作家认为你不关注社会问题就不是一个好作家,而70后作家可能不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陈思和老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之后我一直想。我们经常说题材不分高下,不论写贵人还是穷人,好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对的。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关注当下社会重大问题或者精神疑难的问题更应该受到关注。《红高粱》《白鹿原》《活着》,之所以被我们念念不忘,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形式,也和作品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关。我们讨论国外作家,如果他关注的是种族主义、纳粹、殖民主义等等问题,也更受我们的关注。这是事实。我和魏微也讨论过,新一代作家的写作确实是有问题的。当然,现在有一些作家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社会问题了,他们每个人都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70后作家也不是都不关注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很可能有一本重要著作正在写作之中,一代一代作家在成长,我们要给他们时间。
当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概念,是不断生长着的。作为批评家,一方面要给同时代人提意见,但也要对他们抱有一个热烈的期待,要愿意和同时代人一起关注问题,并试图解决它。别林斯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当一个街道失火的时候,一些人应该迎着火跑,而不是背着火跑”。作家都得面对自己的时代,不一定是赞歌或者批评,但是要对所在时代心存悲哀,心存警惕,心有思考,每个时代都要有这样的写作者,写作者中是要有这样的人在的,我用这句话与我的同时代人共勉。
“文章千古事”
谢有顺:所评论的对象如何,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评论本身的生命力,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蒙田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你选择和一代作家一起成长,如果他成了重要的作家,你可能就是这个作家的早期阐释者;如果这个作家消失了,你的批评也可能随之消失。这基本是批评的宿命。但是,即使如此,我也并不悲观,因我觉得批评本身和文章本身也有它独立的价值。
刚才我为什么强调张莉的写作角度和她的文体意识,包括她写作的探索,其实都是对当代批评范式的出逃和偏离。她在她的文章里面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文章风格和文体意识。当代批评家很多,学者也很多,但有文体意识、有自己感悟的批评家并不是很多,“持微火者”这个题目包含了她对文学和世界的个人感受。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不是这样写的,题目也不是这样起的。比如她写贾平凹的题目是“难以转译的中国性”,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贾平凹小说中的中国性是很难言说的,她把握到了这个东西。如果她的题目用“浅谈贾平凹的小说特色”,语言上给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这表明批评语言本身有独立的价值,文体本身有独立价值。
我读张莉《持微火者》,会想起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批评家李健吾。李健吾的批评文字并不多。他评论的作家或作品,有的可能我们没有读过,有的作家甚至都没听说过,但李健吾的批评文章依然可读,读了有启发,有意思,好看。这就表明,批评有时候也不完全附着于作家身上,它有它独立的价值。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人经常说的“文章千古事”。我跟学生说过,文章写得好,文章本身有文辞之美,文体有创新,同样可以千古。为什么现在太少的人有文章意识,因为他没有想到文章本身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比如,我们都熟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事实上,苏东坡的“赤壁”,并不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原址,苏东坡在那里抒怀感慨,他把赤壁这个地方都搞错了,但并不影响苏东坡的词千古流传。他的情怀,他的诗心,你依然可以体会到,这就是“文章千古事”。
所以,批评家不要太焦虑你所评的这个作家是否重要,如果都在想谁重要,那最初时又是谁使他重要的?当年鲁迅刚写小说时,谁会说他重要?鲁迅当时什么事情做,朋友说你写一点小说吧,他就写了一篇《狂人日记》,谁知道那么重要?如果没有人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作品,鲁迅可能要写更多年才为人所知。所以批评家需要一种胆识,新作品刚出现的时候,一种艺术刚萌芽的时候,他就敢下判断,这既需要有自己见地,也要有这种胆识。某种角度说,这比做纯资料性的学术研究更难。很多人认为文学批评没有学问,但是,写好文学批评其难度不亚于做鲁迅研究。找100本鲁迅研究的著作,读它半年,你怎么样也可以写出一篇研究文章来;但是你读一本魏微的新作,你可能很久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如果此前没有人研究她的作品,没其他人的观点做参考,很多人第一时间是没法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曾有人问格非,你觉得写小说难还是做研究来,他说写小说难,做研究有资料参考,但是写小说只能面对墙壁,完全靠想象和虚构,他觉得写小说更难。我理解他的说法。
刚才,我鼓励张莉关注更多的成长作家,其实是把难题给她。做莫言研究、贾平凹研究难度没那么大,因为很多人写过,大致不会差。但新锐作家的批评一般人是做不好的,要有很好的艺术直觉,要有文章和文体意识,这是张莉有别于其他批评家的特点。目前年轻一代的女性批评家里面她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个,准确、清晰、有力、宽广,很不容易,这是我对张莉另一方面的感受。
魏微:我想问张莉老师一个问题,你学生时代曾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小说,你觉得是什么让你成为批评家而不是作家,你的“文青”经历对你从事文学批评有着怎样的影响?假设时间可以重来,你会选择当作家还是批评家?
张莉:还是会做批评家。我18岁就开始发表小说,当时用的是笔名。2000年的时候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慢慢开始了解什么是好小说和好作家,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我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小说家是有天赋的,而我天赋不够。所以我选择放弃。但我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中获得乐趣。后来进入北师大跟随王富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做的是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论文。我做了非常细致的资料梳理工作。但2007年博士毕业时,每一位答辩老师都对我论文中的文本分析很欣赏。有个老师说,你既然有写作经验和分析作品的能力,你为什么不做当代文学批评?他说,当代文学批评虽然受人诟病,但也的确值得做。因为文学史研究有赖于现场批评,这是最基础的工作。直到现在,我都感谢老师的建议。
批评家很喜欢告诉作家应该怎么写,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但是,有创作经验的人会意识到,每一个题材或者每个写作者都有其局限性,文學批评家首先要站在写作者立场上考虑。批评家可以轻易地质问一位作家为什么不写宏大的史诗题材,但是,如果这个作家就擅长写日常生活呢?那关于他的批评就应该变成,放在写日常生活的谱系里,你写得怎么样。要看作家的能力范围,得要求作家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人尽其才。伍尔夫说,一个好的读者,他要趴在写作者的肩膀上一同看世界,而不是站在对面看,很有道理。好的批评家要就“梨子”谈“梨子”,不能吃着“梨子”挑剔它为什么没有“芒果”的味道。
我想,我的创作经验拓展了我的理解力。比如,一位著名作家的新作品出来,很多人都会说写得太差,对你太失望了,干脆你别写了。我觉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认为,写作者终生都在为最好的那一部而努力,这个代表作是40岁出来或者50岁出来没有人不知道,只能不断地写下去。所以,最优秀的写作者就是要不断地写作。失败一次哪有那么可怕?写下一部就好了。但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不能粗制滥造。
谢老师刚才的话非常感动我。我的确非常重视文体。写的作家不存在了,批评就不存在了,一般都是这样认为。但是,世界上最好的批评家一定是文体家,好的批评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它不依附作家和作品。李健吾那个时代的人是深知这一点的,而现在,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被文学体制造就,很少有人有文章意识。谢老师自己也很有文体意识,他的文章、讲演、作家论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当然,还有一些批评家也致力于这样的工作,比如孙郁先生、李敬泽先生,我很尊敬他们,视他们为榜样。现场文学批评不仅要关注异质力量、边缘的写作者和尚未发现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要写成文章,让自己的文字既在现场,又要有脱离当下语境的气质。这是我的努力方向,但是,坦白说,我做得还不够,我对自己并不满意。
“不得罪人的批评家,不是好批评家”
读者提问:《持微火者》里面评论了贾平凹,我中学的时候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他的早期散文感觉很美,但是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岁以后那些散文感觉唠叨,而且都是废话的感觉。可贾平凹本人认为他后期的散文成就更高,认为早期的散文比较造作,你怎么看贾平凹前后散文风格的变化。
张莉:首先,我不同意你说的贾平凹后期散文废话、啰嗦的评价,我的看法与你相反。我认为他后期的散文比早期的好。在某一个层面说他早期的散文好,我能理解,因为那种美是舒服的、能够被大众接受的美。但是,一代大师级作家就要有冲破大众审美的能力,有冒犯读者审美的力量。我最钦佩贾平凹的地方是,他四十岁的时候在旁人眼里就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了,名满全国。他完全可以这样写下去。但是,他却突然把自己的审美体系打散了,他在四十岁的时候把以前所有的美学建构、把他对世界的理解,全部打散,推倒重建。《废都》的出现,表明他要做另外的事情,建构另外的美学世界。他做到了,做得非常好。从而,他成为更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个更优秀的作家。这个小说家最厉害的是把前面建立的美学全部推倒,重新建立了一种属于他的美学系统。这个美学具有冒犯性,但是,他也借此扩充了自己,重新建立了自己,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提问:张老师你好,我前阵子在香港看到曹文轩老师说当代文学的批评越来越大,不讨论文学而讨论别的,你怎么看待当代文学的现象?
张莉:我同意营文轩老师的看法。90年代以来,学科建制越来越严格,大学教授为了生存要写学术论文,要么为某个理论做背书,要么陷入庞大的文学资料里面做收集,文学变成了一种学科,而不是艺术。某种程度上,90年代以来文学的地位也是下降的,它似乎变成了社会学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文学和社会学具有同样价值,具有同样地位。事实上,很多社会学不能涵盖的东西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才能看到。近年来,很多同行注意到这其中的问题,包括谢有顺老师这次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会议,“重识文学批评和作家论的意义”,也是在致力于从文学内部讨论问题,使文学成为文学。这本《持微火者》其实是回到文学内部讨论文学的尝试,我希望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提问:你提到关于社会学的批评,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有陷入里面的倾向,我在《新京报》看到你发表的《北鸢》书评,惊讶地发现文学批评原来可以这样做。您是怎么进入小说文本的?怎么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葛亮和他的小说,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用文学的路子找回最本真的东西。
张莉:葛亮是一位有发展潜力的70后作家,也是《持微火者》的二十五张面孔之一,这本书里有我对他的整体理解。因为是我持续关注的作家,所以《北鸢》出版后,我要在我的脉络里去理解他。具体要怎么在文学内部理解呢?比如很多人觉得《北鸢》的意义写民国生活,民国的个体生活,有作家对历史的理解。当然,这是对的,我也写到了。但更重要的是,《北鸢》使一种被我们久违的语言重回我们的文学世界。葛亮很早就试图用民国语言书写,但是对语言的掌握方面或许还有不成熟的方面。而这一次,他用了七年的时间,慢慢打磨,逐渐找到了属于他的腔调和方向。我非常欣赏他在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读《北鸢》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语言系统里有慷慨激昂抑扬顿挫,也有内敛雅正平和冲淡,正像我在书评里所说的,《北鸢》是从古诗古画意境中走出来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异质力量,特别珍贵。
提问:我觉得你的朋友肯定很多,各种朋友把他写的书放在你这儿,你会怎样选择这些书评论?畅销书和纯文学的书,因为你写的都是有实力的作家,还有畅销书作家你也会读吗?
张莉:那么多的书放在面前,没有什么谁是朋友或者谁不是朋友。批评家不是看人脸色写作的,我写过一篇文字,叫《要有所评有所不评》,谈过这个问题。批评家面对的只有作品本身。对我来说,摆在眼前的书分为两类,好的,或没那么好的;或者说,我感兴趣的,或我不感兴趣的。如果是我感兴趣的作品类型,同时我又心有感触,有写作的欲望,那么,不管是不是朋友我都会写;反过来,如果不是我感兴趣的,即便是好朋友我也写不了。当然,我几乎不写讨厌的作品,因为已经够讨厌的了,写评论还要把作品看一遍,再告诉别人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多么痛苦啊。对我来说,写评论是快乐的,作品本身要对我有意义,因为文学批评是我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教养的途径,我希望从我喜欢的作品里面获得内心成长的力量,也喜欢把这样的力量和读者分享。所以,如果我对作品没有感触,我就不写,一个字也不写。——我不喜欢,怎么写?
关于读畅销书的问题,谢老师前面说到一个人的有限性,我很赞同,一个批评家不可能对所有的门类感兴趣,如果有人让我谈谈网络文学,我会说我不懂。大部分畅销书我也不看的。但是,我读了《蜗居》《琅琊榜》《杜拉拉升职记》,因为它们参与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这个我会看。我限定了自己关注的作家和作品类型。人的精力有限,我只能做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魏微:我来补充一点。很多年前,张莉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要跟作家保持距离,尽量少和作家交朋友。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少受人情之累,尽量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可是我作为作家,当时听了还是蛮别扭的,作家怎么了,作家就不是人?而且也不是所有作家都爱巴着批评家,作家也有独立性的好不好?但是撇开我的作家身份,张莉这话我是很爱听的,也是让人尊重的。这么些年来,我想张莉不可避免地还是交了一些作家朋友,但是她也确实做到了少受人情之累,尽量保持批评的独立和公正。
谢有顺:现在很多人不理解批评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张莉算得上是勤奋的批评家了,读了很多书,但是她再勤奋,阅读也是有限的。按我自己的速度,一周读一本书,一年也只能读52本,不可能全部是小说,肯定还有理论书,翻译书,再勤奋的人一年也只能读几十本作品,所以,很多作家根本理解不了,时间对一个批评家意味着什么。他说你给我写一個评论,我说写不了;然后他说你写短一点,我说也写不了。他不明白,我写几百字也要把这个作品读完。写得好的,我读起来有快乐;写得不好的,读得人憔悴。为了写这几百字,付出太多。这种困境,一般人理解不了。批评家固然面临智慧、胆识的问题,但今天批评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出版3000部长篇,送到我案头的估计200部,张莉应该更多。如果没有强大的遴选能力和拒绝能力,这个批评家没法做。所以,批评家做到后面,一定是会得罪人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得罪人的批评家,不是好批评家。我用这话与张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