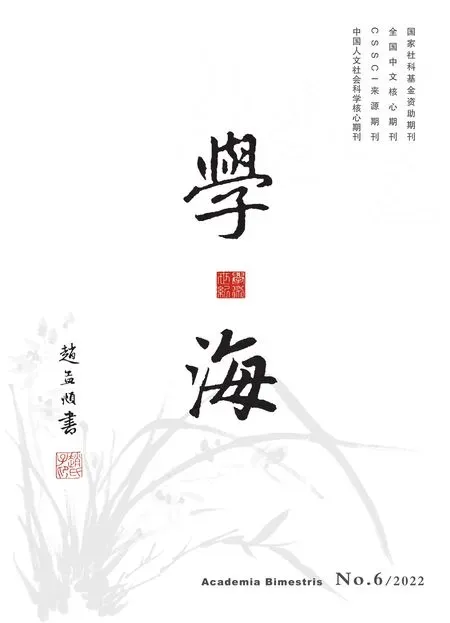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
焦长权
内容提要 差序格局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某些圈层更加硬和实,另一些圈层则更加软和虚,体现在丧服制度中就是期服、大功服和缌麻服这几个“节级”的特殊性。同时,差序格局中的各圈层也不完全处于同一平面,某些圈层“悬浮”于己身所在圈层之上,某些圈层则下沉到这一平面之下。差序格局具有“尊尊”维度,是一种立体性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经典概括。近年来,周飞舟、吴飞教授等研究指出,差序格局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丧服制度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他们以丧服制度为核心,对差序格局及其背后的社会伦理展开了系列阐释,有力推动了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深化理解,并为学界认识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特征开辟了新路径。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继续从丧服制度切入,探讨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并拓展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解。
关系社会与差序格局
潘光旦先生认为,在中国讲社会学,最应该联想到的两个字是“群”与“伦”。中国以前虽然没有“社会”这个名词,但并不是没有社会这宗事实,更不是缺乏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一个“群”字和一个“伦”字指的就是这一宗事实。因此,“社会学”更恰切的翻译可能是“群理学”(群学)或“伦理学”(伦学)。社会学者所研究的对象,抽象地说是人群,而在中国的语境下,则不如用“伦”字表达得更加亲切。②
潘先生指出,“伦”有二义:类别与关系。二义之间还有因果关系,类别是因,关系是果,没有了类别,关系便无从发生。同时,类别是事物之间的一种静态关系,其根据为同异之辩;关系则代表着一种动态,表示互相影响。社会个体之间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社会关系得以发生的关键就在于辨别人我之间的差别,也就是群己之间的差别和界限。按潘先生的话说就是:“每个人不止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有自意识的个体,是一个个人,是一个人格。”因此,同样是人,却各有各的不同的格式,或相面先生所称的格局。而“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群己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之所以不同,主要是格局的差异。这些群体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构成社会。“伦”字类别和关系的两种含义,大致同时包含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内涵,因此,研习社会学必自“明伦”开始。③
“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伦关系的重要区分。五伦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不仅概述了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五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指出了每种关系背后的伦理准则。潘先生通过对传统经籍的细致检录发现:“五伦”说法的产生有好几个源头,但到了清代,“五伦”的名目得以普遍化,从此“言关系必称伦,数人伦必称五”。④显然,潘先生的努力,是将舶来于西洋的社会学“远绍”到中国传统先贤之智慧的一种尝试,近年来受到了学界的重新重视。⑤
受潘先生“说伦”之启发,费孝通先生将中西社会的不同“格局”进行了一番推演。费先生指出,西洋社会的结构类似于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在社会中,这些单位是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以及个人与团体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这可以称为“团体格局”。中国社会则不同,“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因此,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⑥
费先生不仅阐明了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结构,而且特别阐述了维系着这种格局的道德观念。他认为,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在差序格局中,道德则维系着“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⑦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互相配合的,共同构成了乡土社会的基本底色。
潘、费两位先生共同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的根本性不同。西方社会在个人和社会的两端均为实体,在个人一端是享有权利义务的平等“个体”,在社会一端则是有超于个人而又界限分明的“实在”团体。中国社会则不同,既没有权利义务加身的独立个体,也没有界限分明的“实在”团体。因此,中国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是一种“关系本位”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几种社会关系被称为“五伦”。
梁漱溟先生也持有近似的看法:“西洋人学得了团体组织之本。第一,于此个人隶属团体,团体直辖个人;第二,于此公认团体中各个人都是同等的;此其重要,可说非常重要,中国所缺乏的,就是这个。”⑧中国人则“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家人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是其最基本的天然关系,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展开,而渐有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比如师徒、东伙、君臣等等。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茫无边界。⑨梁先生将这一由关系和伦理网络不断联锁编织起来的社会称为“伦理本位”。
这一联结社会的关系和伦理网络,虽然异常繁复,但也并非杂乱无章、混沌一团。潘先生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推广”和“扩充”的关系,即从自我扩充和推广至于众人,即从修身始,经齐家治国,而达于平治天下。⑩费先生对差序格局的阐述,更加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网络由“己”为中心,逐渐推广和扩展的动态过程。潘、费两位先生所强调的核心,都是“推己及人”的过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
后来的学者对差序格局概念进行了诸多思考,但仍然有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一方面,费先生对差序格局的阐述非常形象和形式化,但未能系统论析这一圈层外推过程中是否也有其结构性特征,即某些圈层是否明显更为重要和硬实,另外一些圈层则更为虚化;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差序格局不仅包括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结构,而且包括一套以尊卑为基础的等级结构。周飞舟、吴飞教授等从丧服制度切入,进一步将“尊尊”维度纳入差序格局概念进行阐述,有力推进了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深化理解,也为本土社会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继续从丧服制度切入,进一步对上述两方面展开论析,以拓展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解。
差序格局与“亲亲”
费先生晚年指出,他用“差序格局”概念想表达的实质内容是中国“亲属关系的结构形态”。因此,这种结构形态与同样主要用来表达和规范传统亲属关系结构的丧服制度就有了很强的相似性。从形式上看,丧服制度较差序格局的表述要复杂很多(见图1)。

图1 本宗丧服图
《礼记·大传》曰:“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郑玄注曰:“术犹道也。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名,世母叔母之属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长幼,成人及殇也;从服,若夫为妻之父母,妻为夫之党服”。所谓“服术”,就是构成丧服体系的基本原则,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六大原则是丧服制度的核心,具体到每个个体,他的服制都是这些核心原则叠加演变的结果。
我们先从“亲亲”原则开始,分析本宗五服(男子)的本服体系。这个体系以己身为中心,向上依次为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制服为齐衰期、大功、小功和缌麻;向下依次为子、孙、曾孙、玄孙,制服为期服、大功、小功和缌麻,其他五服内亲属依次类推。
当然,己身最终为这些人所服的成服与本服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引入其他制服原则后,对本服进行“修正”的结果。比如,引入“尊尊”原则后,由于父亲是至尊,故加隆为斩衰三年;祖父、曾祖父也依次加隆。对子女的服制,成服也有变化。比如,因长子正体于上,又将传重于己,故需引入“尊尊”原则,为长子服斩衰三年,为众子则服齐衰不杖期。女子未出嫁时服制与众子相同,若出嫁后则需引入“出入”原则,下降一等为大功,但若其出嫁而无主,则不忍降之,为之仍服齐衰不杖期。为孙制服,嫡孙则期,庶孙大功。为曾孙制服,本服是小功,但因曾孙为曾祖服齐衰三月,故曾祖反之为曾孙制服不应超过三月,故降一等为缌麻。玄孙与曾孙同。
《丧服小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郑玄注曰:“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孔颖达疏曰:此一经广明五服之轻重,随人之亲疏,著服之节。“亲亲以三”者,以上亲父,下亲子,并己为三,故云“亲亲以三”。“为五”者,又以父上亲祖,以子下亲孙,向者三,今加祖及孙,故言五也。“以五为九”者,己上祖下孙则是五也,又以曾祖故亲高祖,曾孙故亲玄孙,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两孙,以四笼五,故为九也。然己上亲父,下亲子,合应云“以一为三”,而云“以三为五”者,父子一体,无可分之义,故相亲之说不须分矣。而分祖孙,非己一体,故有可分之义,而亲名著也。又以祖亲曾祖,以孙亲曾孙,应云“以五为七”,今言“九”者,曾祖、曾孙,为情已远,非己一体所亲,故略其相亲之旨也。“亲亲”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亲其所亲,从作为至亲的父母开始,随着亲疏程度的迭减,丧服也由重到轻,直到无服。《丧服小记》(以下简称《小记》)上面这段话,则是对“亲亲”原则更深入的阐述,主要是指出了背后的结构性特征,即亲亲“迭杀”并不是一个均质展开的过程,而是存在“一体之亲”、“大功亲”和“缌麻亲”三个大的“节级”,下文详细论析。
(一)至亲以期断
诚如孔颖达疏中指出的:己身上亲父,下亲子,合起来应该说“以一为三”。但《小记》中却没有说,直接提出“以三为五”,主要原因在于父子一体,无可分之义。这里就提出了“亲亲”原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节级”,我们可以称为“至亲以期断”。
《礼记·三年问》曰:“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至亲”者,“一体之亲”也。“父子首足,夫妻牉合,昆弟四体。皆骨肉不可分异,是为至亲。其生也恩爱绝常,其死也哀痛至极。圣人以送死当有已,复生当有节,一期则天地之中莫不更始也,因象之,而并断以齐衰期,是为服本”。
所谓至亲,是指父子、夫妻和昆弟,这相当于现在核心家庭的成员范围,也是差序格局的“核心层”。这些骨肉相亲、不分彼此的“一体之亲”,“其生也恩爱绝常,其死也哀痛至极”,因此他们之间互相制服的本服都是最重的齐衰期,并以之为众服之本。在此基础上,引入“尊尊”等制服原则,最终形成了这些成员之间的成服。
至亲又被称为“一体之亲”。在世叔父母一章中,传曰: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兄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贾公彦作疏进一步解释说:凡是说“体”,则好比人之四体,所以传文以父子、夫妻、兄弟比作人之四体。“父子一体”,是说二者骨血相亲,人身首足为上下,父子亦是尊卑之上下,故父子比于首足。所谓“夫妇牉合”,是“半合”之意,夫妇半合,而后子胤生焉,因此“半合”亦为“一体”。四体指二手二足,在身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就像手足四体本在一身、不可分别一样,昆弟也是父身之“四体”,不可分离。
因此,“一体之亲”的核心在于“一体”,即父子、夫妻、昆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分别。“一体”在制服过程中就表现为:一方面,“一体之亲”的齐衰期是众服之本,由此推演出整个丧服体系;另一方面,父子、夫妻这两个一体关系又是最基本的制服单位。在对夫妻、父子以外的亲属制服时,己身是不能单独制服的,必须视父亲或丈夫的制服而定,他人在为自己制服时也要依靠对自己父亲或丈夫的服制决定对自己的制服。因此,“一体”关系是丧服体系最基本的轴心,丧服体系是“一体本位”而不是“个体本位”。
(二)以三为五
从“一体之亲”往外推,丧服制度中的一个“大节级”出现,即“以三为五”这一圈层:由祖、父、己身、子、孙五人为基础构成的圈层。从服制上看,即本宗五服中的本服“大功”范围,“以三为五”的讨论,就表现为对“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服制重大区别的辨析。
《礼记·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孔疏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者,五服之内,大功以上服粗者为亲,小功以下服精者为疏,故周礼小史掌定系世、辨昭穆也”。《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以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郑玄注曰:“称情以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孔疏曰:“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者”,亲谓大功以上,疏谓小功以下,贵谓天子诸侯绝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贱谓士庶人服族。其节分明,使不可损益也。《礼记·服问》曰:“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陈澔曰:“罪重者附于上刑,罪轻者附于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于亲,小功以下附于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丧服小记》《曲礼》《三年问》《服问》中的这些阐述,共同提出了一个重大判断,即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是丧服体系中辨别亲疏的一个大界别。下面具体从丧服形制、服丧过程、具体服例等方面对此予以辨析。
先看大功以上、小功以下在丧服形制、服丧过程方面的一些关键差别(见表1)。丧服形制一般包括衰裳、绖、杖、冠、带、屦等诸项,加之服期、变除、易服之节,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只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区别予以说明。比如,丧冠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别“吉凶”,大功以上哀重,丧冠右缝,从阴从凶,小功以下哀轻,丧冠左缝,从阳从吉。绖带是分别环绕系于头部、腰部的两条麻绳,“以绖表孝子忠实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意”,因此绖是“衰绖之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绖之缨则为环绕头部系牢后剩余部分垂下的穗子,但只有大功以上才绖有缨,小功以下则绖无缨,主要在于“绖有缨者,为其重也”。绖带形制的另一个要害在于是否有“本”,即麻是否有“根”,只有大功以上重服才绖带有本,小功以下轻服则断本。另外,“带”是否绞垂也是辨别轻重的重要标志。《礼记·杂记》曰:“大功以上散带,小功缌轻,初而绞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丧至小敛之后,皆服未成服之麻,大功以上哀重,不忍即成之,故散带之垂者,至成服乃绞之,小功以下哀轻,初而绞之。
此外,在服丧过程中的易服、变除、追服等环节,也处处体现着大功以上、小功以下的关键区别(见表1)。易服,指身先有前丧重,今更遭后丧轻服,欲变易前丧。“唯大功有变三年既练之服,小功以下,则于上皆无易焉”,“小功缌不得变大功以上”,“小功无变也”。丧服易服之节最为表现五服之间的轻重区别,以“不以轻累重”为原则,小功以下无变。服丧变除、追服之节,也是区分轻重服的重要标志。丧服之变除,是指根据服丧过程中的不同节点,逐步由轻服替代重服,并最终除服的过程,即所谓“受服”。但“受服”同样止于大功,小功以下则无受。追服是指闻丧晚,服丧日月已过,对大功以上丧服进行追服,小功以下也不追。

表1 大功以上、小功以下丧服形制区别(举例)
下面我们再举一服例深入辨析。在殇小功章中,有“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之长殇”一条。传曰:“问者曰:中殇何以不见也?大功之殇中从上,小功之殇中从下。”郑玄注曰:“问者,缘从父昆弟之下殇在缌麻也。大功、小功皆谓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殇中从上,则齐衰之殇亦中从上也。此主谓丈夫之为殇者服也。凡不见者,以此求之也。”
这是一条涉及殇服的讨论,需先简要说明一下殇服体系。殇服是为未成年者去世后所制丧服,分为三等:长殇、中殇和下殇。具体而言,年十九岁至十六岁为长殇,十五岁至十二岁为中殇,十一岁至八岁为下殇,八岁以下则为无服之殇。殇虽有三等,但制服却只有二等,长殇较成人本服降一等,下殇降两等,中殇则根据情况从于长殇或下殇。可见,殇服本身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又在于中殇的不同处理。
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本服在大功,长殇降一等为殇小功。传文指出:有人问为何经文中没有提出中殇?因下殇已经在缌麻章中提出,前后对比一直没有规定中殇,传文解释说是因为“大功之殇中从上,小功之殇中从下”,因此中殇未单独规定。既然大功之殇中从上,则齐衰之殇亦中从上,因此也不必赘言。郑玄作注进一步指出此处指男子为殇者服,主要是为了说明与缌麻章“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妻”一条中的传文中提出的“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上中从下”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郑注要说明的是这两处看似矛盾,实则不矛盾,因为此处是丈夫为殇者服,缌麻章则指妇人为夫之族类服,前者是正服恩深,因此大功之殇中从上,后者义服恩浅,因此大功之殇中从下。
结合其他殇服条目的讨论,我们发现,对中殇的不同对待,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若男子为殇者服,男子与殇者之间本服为大功及以上时,则遵循“大功之殇中从上”的原则,即中殇按照长殇制服,较本服降一等,小功之殇则“中从下”,即降两等为无服。若是妇人为夫之族类从服,因本已属义服恩浅,因此“大功之殇中从下”,需降两等制服,此时大功长殇制服缌麻,大功中殇以下的殇服就全部降为无服了。
因此,正服大功是殇服体系的一个关键之处。大功以上亲且重,因此首先必须确保大功殇服有服,为此殇虽分三等,但殇服仅两等,如此就能确保大功下殇仍然有服(较大功降两等为缌麻),若制服为三等,则大功下殇需降三等,如此就无服了。同时,中殇的处理,也是以正服大功为关键节点:大功之殇中从上,小功之殇中从下。盛世佐对此做了精妙的评论:从上者,比本服降一等也,从下者,比本服降二等也;大功之殇中从上,皆降为小功,惟下殇缌麻也;小功之殇中从下,皆降为无服,惟长殇缌麻也。亲者“引而进之”,疏者“推而远之”,于中殇之从上从下,而大功小功之隆杀判矣。大功、小功殇服的区别对待,正是因为大功以上服重,小功以下服轻,前者“引而进之”,后者“推而远之”。
事实上,还有不少服例都体现了大功以上、小功以下的亲疏之别,在此不再赘述。上述分析已经清楚表明,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是丧服中的一个大界别,大功以上亲而重,小功以下疏且轻。如此我们就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张锡恭提出的祖之上、孙之下的“大节级”之说。在关于“曾祖父母”一条中关于曾、高二祖如何制服的讨论中,张锡恭指出,“所谓‘以五为九’者,由祖而亲祖之父祖,由孙而亲孙之子孙,故祖之上、孙之下,有大节级焉,祖之父祖、孙之子孙,无大等杀焉。为祖父母齐衰期,而曾祖父母齐衰三月,为孙大功,而曾孙缌麻,以其历‘以五为九’之节级也,则祖之父祖,同是由祖而亲之,孙之子孙,同是由孙而亲之,何不可同服乎?明乎‘以五为九’之义,则曾祖与高祖同服了然矣”。祖之上、孙之下的“大节级”,正是大功以上、小功以下的大界别。
(三)以五为九
《丧服小记》云:“‘以五为九’者,由己与父、祖、子、孙而成五,再外推到曾、高祖,曾、玄孙以为九”。孔颖达疏曰:“所谓‘亲毕矣’者,主要指从‘亲亲’所出的丧服,于此为断,以‘结亲亲之义’,始自父母,终于族人,故云‘亲毕’矣”。从服制上,“以五为九”包括小功、缌麻之服,与大功以上相对,属于丧服中的轻服。
《礼记·大传》亦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孔疏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者,四世,谓上至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后,为族兄弟,相报缌麻,是服尽于此,故缌麻服穷,是‘四世’也。为亲兄弟期,一从兄弟大功,再从兄弟小功,三从兄弟缌麻,共承高祖为四世,而缌服尽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者,谓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无正服,减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者,谓其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亲属竭’矣”。
在对“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加一等”一章的讨论中,有人困惑于正服五服之外的人如何加服的问题。张锡恭则引《文王世子》加以阐发,《文王世子》曰:“族之相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罚之”。郑玄注云:“吊谓六世以往,免谓五世”。张锡恭说:“‘吊’谓吊服,‘免’谓袒免。然则小功以下有缌麻焉,有袒免焉,有吊服焉。加一等者,六世以往为之袒免,五世为之缌麻,正服缌麻者为之小功,正服小功者为之大功也”。
因此,从“亲亲”原则来讲,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虽有袒免,六世以后虽有吊服,但都不属于正服范围,较缌麻明显要轻。所以,五服内外(缌麻内外)又是丧服体系的一个大界别。举个反例,五伦中“朋友”一伦虽至为重要,但在丧服体系中,仅为朋友“吊服加麻”,若皆在他邦则加至袒免。
因此,五服之中,“至亲”以“期服”为断,大功以上“亲”,小功以下疏,缌麻之外则“亲毕矣”。从服制讲,诸期为至重之服,大功以上重服,小功以下轻服,缌麻以外则(正)服穷矣,仅以袒免、吊服作为补充。
由上文可见,从形式上看,本宗五服本服体系完全类似于费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波纹式”结构,以己为中心,向外“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本宗五服成服体系虽然引入了一些其他制服原则,较标准化的同心圆结构略有不同,但仍然表现出极强的圈层“外推”特征。但是,这种“外推”并不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一些圈层相对更加硬和实,最典型的表现为“一体之亲”“大功亲”“缌麻亲”这三个丧服体系中的重要“节级”。
“一体之亲”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社会行动单位,是差序格局的核心层,也是推己及人的起点。在这个范围内,中国人是没有“我”的,这恰如梁漱溟先生形象地指出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处,处处尚情而无我”。“大功之亲”有同财之义,大功以上、小功以下又是中国亲属关系的一个大界别,一般被称为亲疏之别,大功以上亲,小功以下疏。在《礼记·祭统》中,这一“亲疏之别”被称为“十伦”之一,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这在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中仍然时有表现。“缌麻之亲”则一般被称为五服以内,五服以外为族人,因此五服内外也是“亲亲”关系的一个大界别。在差序格局的层层外推过程中,这些更为重要的圈层和节级,成为引导人们社会行动的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力量,自身对与这些圈层更亲近的个体“引而近之”,比如丧服体系中对昆弟之子引同己子,反之则“推而远之”。这一或“引”或“推”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了差序格局不同圈层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同时也表明了差序格局在具体行动过程中的动态特征。
以“尊尊”统“亲亲”
上文从“亲亲”之道出发,对丧服体系中的“至亲以期断”、“以三为五”和“以五为九”三个重要圈层进行了辨析,揭示了其结构性特征。但是,这种分析仍然是抽象和平面的,离丧服制度的实际过程有很大距离。
上文主要依赖本宗五服本、成服图来展开,即通常所说的菱形宗枝图(见图1)。但是,这个图只是抽象概括了以己身为中心的五服服例,在现实中让人感到不好操作。早在汉朝,汉宣帝就抱怨“古宗枝图列九族,世俗难晓”。汉宣帝困惑的实质在于,宗枝图中每一个服服对象在现实中都有众多人与之对应,他们是分别从不同枝派传递下来的,为每一个具体对象制服,都得梳理他的枝派世系,所以非常复杂麻烦。在汉宣帝的支持下,王章制定了更加现实丰满的“鸡笼图”。“鸡笼图”的好处是,它把本宗五服内部各枝派的延伸情况清楚描绘出来,让人一目了然(见图2)。比如,己身不再位于图表的中心,己身所在的枝派被放在最右边,其他分枝世系分别自左向右排列。其中,假设自高祖以下,每一男性子嗣均有两个儿子,结果,从己身看,族昆弟就有八人,己身均为之服缌麻,而在原来的宗枝图中,只简单以“族昆弟”一词抽象称呼概括。

图2 鸡笼图(据龚端礼《五服图解》)
“鸡笼图”尝试将抽象的宗枝图予以具体化,把宗枝图中每一个抽象对象所包含的众多具体对象标识出来。但是,“鸡笼图”仍然有些缺陷:第一,它在表示己身与其他枝系的关系时不够形象,把本来位于中心的己身抽离了出来;第二,它的制图过程比较复杂,若是每人都有很多子嗣,子嗣数目也不相同时,作图就非常困难。受“鸡笼图”启发,笔者尝试进一步将“鸡笼图”进行一些变化,以达到将“宗枝图”的抽象简洁和“鸡笼图”的形象丰满相结合的目的。
本宗菱形“宗枝图”的构成非常复杂,最基本部分是菱形图的右上三角形部分,其他三部分是以这部分为基础引入其他原则演变出来的。我们可以将图中的每个人简化为一个点,己身为三角形的直角点。从己身开始,三角形底边上有四个点分别是昆弟、从父昆弟、从祖昆弟和族昆弟,垂直边上的四个点分别是父、祖、曾祖和高祖,斜边上自上往下三个点分别是族曾祖父、族祖父和族父。其他三角形内部各交叉点的人员和制服都很容易得知。为便于分析,我们只画出本宗五服本服图(见图3)。

图3 本宗五服本服图(部分)
这个三角形是对菱形“宗枝图”的简化,为了引入“鸡笼图”的优点,即把每一个对象更具体地展现出来,就必须让这个三角形“立体化”,即让这个三角形“旋转”起来,因之得到一个圆锥图。圆锥图底面以己身为中心,依次向外有四个圈层:昆弟圈、从父昆弟圈、从祖昆弟圈和族昆弟圈,制服依次是期、大功、小功和缌麻(见图4)。其他由原来三角形中的点形成的圈层也清晰可见,每一个圈层制服相同。每一个圈层上的点,实质就是“鸡笼图”中各枝派的具体人员。

图4 本宗五服(本服)锥形图
实质上,这个锥形图由四个锥形图组成,它们的顶点分别是父、祖、曾祖和高祖,底面半径分别是昆弟(期)、从父昆弟(大功)、从祖父昆弟(小功)和族昆弟(缌麻)。若把每个圆锥体表面展开,即得到一个扇形图。比如,最外围的圆锥体展开得到一个以高祖为顶点的扇形图,扇形图中有四道“腰线”,分别由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和族昆弟组成,己身为他们均服缌麻。若将扇形中各具体人物点之间的关系线连接起来,即可得到一幅以高祖为顶点,各枝派延伸下来的亲属关系图(见图5),图中包括了除己身曾祖这一枝派外的所有五服内的亲属,也就是上文“鸡笼图”最左边部分。其他各圆锥体表面展开之后的情况与之类似,不赘。

图5 本宗五服(本服)缌麻亲属图
结果,从高祖开始的五服亲属关系被拆分成了四个扇形亲属图和一根连接中轴。四个扇形图分别是己身的期亲、大功亲、小功亲和缌麻亲,连接中轴是“高祖—曾祖—祖—父—己身”这条轴线,即圆锥体的中轴线,由它把四个扇形串连起来,并立体化为一个圆锥体。借用“鸡笼图”的比喻,这是四个大小不同、底面中空的“鸡笼图”被叠放到了一起,各顶点被一条线拴了起来。
锥形图不仅可以表达每一个抽象对象可能在现实中所对应的无数具体对象,避免了“鸡笼图”面对人员众多时的麻烦。同时,圆锥图还形成了一条以“己身—高祖”为轴线的中轴,同宗各枝派的个体与己身的关系也清晰可见。从制服上看,己身对位于四个圆锥体表面上的每人制服相同,己身为同高祖者服缌麻,同曾祖者服小功,同祖者服大功,同父则期,己身对圆锥体顶点个体的制服决定了全部锥体表面人员的制服。
可见,虽然本宗五服本服体系可以说是完全基于“亲亲”之道制定的,但是,“亲亲”并不是完全的自然性血缘关系,而是一种“社会性”血缘关系。即丧服中的“旁杀”并不是从己身直接横向迭减,而是以旁系亲属与自己的父、祖、曾祖、高祖的关系来迭减,这是从“父为子纲”为基础的宗法性关系延伸出来的。在《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一条的讨论中,孔颖达疏曰:“此一经论服之降杀之义,亲亲谓父母也,尊尊谓祖及曾祖、高祖也,长长谓兄及旁亲也”。显然,旁亲之服是按照“长长”之意制定出来的,“兄”指五宗中的“宗子”,因此,“长长”也是族人为宗子制服的理据。吴飞教授的分析也发现,“上杀是基准,下杀只是上杀的报服(因为加隆等原因,会更复杂),旁杀则来自上杀,因为旁杀在根本上是不同枝派的旁杀”;“真正的旁杀并不是某一横行的递减,而是各枝派之间的递减”;“旁杀是由亲到疏的关系,这个关系来自正尊一系的自仁率亲,却受制于自义率祖”。此即丧服中的“以尊尊统亲亲”。父、祖、曾祖、高祖只是因尊加服,故从本服加为斩衰三年、齐衰期、齐衰三月;世叔父因与父亲为一体,故加为齐衰期。
在丧服成服体系中,“亲亲”与“尊尊”的关系更为复杂。从本服上看,“上杀”是一种“亲亲”之道的体现,“旁杀”是以“上杀”为基础的“尊尊”之道。因此,更确切的说法是,在给旁尊亲属制服过程中,“以尊尊统亲亲”。因此,“尊尊”不仅无法脱离“亲亲”独立存在,而且可以说部分来源于“亲亲”。这不仅体现在直系亲属的“上杀”是旁系“旁杀”的基础,而且也体现在为旁尊亲属制服的具体过程中。比如,在“族曾祖父母”一条讨论中,郑玄注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亲也”。按照“以尊尊统亲亲”的原则,为“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之制服本于对“族曾祖父”的制服。而郑玄给出的为“族曾祖父”制服的依据恰恰因为他是“曾祖”的“昆弟之亲”,即因他与曾祖为一体之亲,己身为曾祖本服小功,为其昆弟降一等,为缌麻。又如,给旁尊“世叔父”制服加一等,父既为至尊,亦是至亲,世叔父为父之一体之亲故加一等。显然,其秉持的理据是为己之至亲的一体之亲加一等,为昆弟之子加一等的理据也是如此。两条结合起来可见,“亲亲”乃本宗直系亲属的制服之本,旁系亲属的制服,在直系“亲亲”之本的基础上,遵循“以尊尊统亲亲”的原则,即以直系内的“尊尊”统摄旁系的“亲亲”制服。因此,“除却一体之亲的父母昆弟之外,其他所有亲属的本服是根据以尊尊而非以亲亲为主的宗法原则制定出来的”。
《礼记·大传》对此进行了更精微的阐发。《礼记·大传》曰:“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郑玄注曰:“用恩则父母重而祖轻,用义则祖重而父母轻。恩重者为之三年,义重者为之齐衰”。孔颖达疏曰:“此一经论祖祢仁义之事。亲,谓父母。子孙若用恩爱依循于亲,节级而上,至于祖远者,恩爱渐轻,故云‘名曰轻’也。‘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者,义主断割,用义循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其义渐轻,祖则义重,故云‘名曰重’也。‘一轻一重,其义然也’者,言恩之与义,于祖与父母,互有轻重,若义则祖重而父母轻,若恩则父母重而祖轻。一轻一重,义宜也”。显然,孔疏将“亲”做了更具体的解释,直接谓之父母,由此“亲亲”同时包含了两义:一是由父母之恩引发的对父母的恩爱,二是由此“外推”形成的对其他亲属的恩爱。父母既为至亲,对母亲和己身而言,父亲又均是至尊,因此,父亲是集“至尊”与“至亲”于一身。《礼记·大传》又曰:“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郑玄注曰:“言先有恩”,是故“亲亲”为本。因此,张锡恭在“释正尊降服篇”中才说,“至敬根至爱而生,故其至尊以至亲而出”;郑珍也说,“既亲亲,当尊尊”。“敬由爱生,义由恩出”,“尊尊”的初始性来源正是“亲亲”。
但是,“自下而上”的“自仁率亲”需要受到“自上而下”的“自义率祖”的节制。故为曾祖父制服齐衰三月,其传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郑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在“祖父母”一条的讨论中,其传曰,“何以期也,至尊也”。贾公彦认为,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孙之至尊,故直云至尊也。张锡恭也认为:贾疏释至尊善矣,而词太简,当云是父之至尊,非孙之至尊,故不云“祖至尊”。然父之至尊,孙亦从父而尊之,故直云“至尊也”。但是,对比祖父母、曾祖父母两条的讨论可见,传文在曾祖父母条中直指曾祖父母为至尊,此处至尊显然不能再解释为祖父母之至尊,孙从父、祖父尊之,其要明确表达的意思就是曾祖父母是“己之至尊”。由此推之,则祖父母条中之“至尊”当为己之至尊,孔疏、锡恭均微误。对这一点的辨析,能够更加清晰地说明“亲亲”与“尊尊”的区别。“亲亲”之道,具有“愈推愈远”、逐步递减的特征。而“尊尊”之统则不同,张锡恭在总结群儒关于远祖是否有服的讨论中说得最为明白,“盖亲亲之属虽竭,而尊尊之统无穷,夫亲亲毕于以五为九,则下杀至元孙而止矣。其为远祖服者,尊尊之义也。尊尊之义可上推,而不可下逮,故上服可及无名之祖,而下服不得过元孙”。正是因为“尊尊”之统无穷,故需由“尊祖”而“敬宗”。
宗者,尊也,亦谓亲之党也。“宗”字大致有两重含义:一谓宗子,即大小宗中之尊者,尊者谓之宗,尊之谓宗之。大宗以率小宗,小宗以率群弟,即指宗子。二谓亲之党,大宗、小宗、内宗、外宗、父宗、夫宗均指这种用法。《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以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郑玄注曰:“称情以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群,谓亲之党也”。孔疏曰:“三年之丧差降,各表其亲党”。因此,亲之党既可谓之宗(妻之党可谓之父宗,夫之党可谓之夫宗),亦可谓之群。宗既兼“尊”与“亲之党”(群)之二义,不同宗之间的关系即不同“尊”之间的关系,这在丧服制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夫宗高于父宗,大宗重于小宗,内宗重于外宗。一旦超出本宗五服之外,各宗之间的轻重完全取决于“尊”与“义”,“门内之治恩演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丧服制度中所讨论的“尊”主要有两种:父祖之尊和爵位之尊,前者在本宗五服(小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后者则应用于君臣政治领域的制服,大宗是二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地带。
因此,不仅本宗五服内的旁系亲属关系制服遵循着“以尊尊统亲亲”的原则,从整个丧服体系来看,不同宗之间的关系更是严格的“以义断恩”。
结论与讨论: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
本文的分析表明,差序格局的概念内涵有可能得到进一步丰富。
首先,在差序格局的“推己及人”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差序格局中的不同圈层重要性不一,有些圈层更加硬和实,有些圈层相对比较软和虚。“一体之亲”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社会行动单位,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差序格局不是“个体本位”而是“一体本位”。从“一体之亲”向外推,还有“大功之亲”、五服之属等重要行动单位。这些圈层之间互相配合,勾勒了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也塑造了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差序格局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使得不同圈层和行动单位之间的边界具有一定模糊性,某些行动圈层更为重要,因此己身会对与这些圈层更亲密的个体“引而近之”,反之则“推而远之”。这种或“引”或“推”的行为,也是对行动单位的动态塑造过程。
其次,差序格局中各圈层也不是完全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它们中的某些圈层“悬浮”于以己身为中心的平面之上,有些圈层则“下沉”到这一平面之下,此即尊卑等级之别。费先生非常敏锐地指出:个人主义是团体格局的重要基础,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是相等的;在差序格局中,作为中心的“己”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探讨“自我主义”中的个体是否像团体格局中那样“各分子的地位相等”;或者说,差序格局中心的“己”,与其他个体是在一个平面上吗?在锥形丧服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序格局中的不同圈层并不完全处于同一平面上,这就是丧服中的“尊尊”一维表达的内容。
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确实像费先生所说的“捆柴”,团体中的个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团体的整合中心由团体“公意”指定的个体作为“代理者”。而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则不同,社群中个体的社会地位是不“相等”的,具有明显的尊卑等级之别。这在丧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尊尊统亲亲”,“亲亲”圈层的外推不完全是一个平面中的平行外推,而是会受到“尊尊”的节制,即不仅是一种“外推”,也有一种隐伏的“下推”。社群的整合中心也不是群体“公意”指定的代理,而经常是集“亲亲”与“尊尊”于一身的社会性个体。从锥形丧服图来看,其整合中心是由“己身—父—祖—曾祖—高祖”构成的一条轴线,它集至尊与至亲于一体。事实上,费先生在有关著述中也已经表达了相似的思想。比如,针对《生育制度》一书的主题,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补充说:
当我特别被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吸引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发觉有必要把他的概念转成垂直的。他的概念像是平面的人际关系;而中国的整合观念是垂直的,是代际关系。在我们的传统观点里,个人只是构成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当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节。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正当职责。那是代际的整合。在那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社会整体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
他将这一垂直性的代际整合称之为“社会继替”的过程。当从历史社会绵续来看,这就是一个“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的过程,为了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社会以强制规范来要求个人结婚生子和抚育后代,以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从现实社会整合来看,这就让平面性的人际关系拥有了垂直的维度,现实生活中的父、祖因集“亲亲”和“尊尊”于一身,成了亲属社群的整合中心,形成了一种垂直性的社会整合。同时,这一整合轴心不仅指向了过去,而且指向了未来,因此具有了动态特征。显然,引入“尊尊”维度之后,平面化的差序格局变得立体起来,在丧服制度中表现为以“己身—父祖”为轴线,旁系亲属序次性地向中心“堆积”靠拢,以直系“尊尊”统摄旁系“亲亲”的锥形结构。中国人的日常社会行动,虽不如锥形丧服图所显示的那样规整和严密,但却具有其涵盖的基本特征,即同时考虑自身与行动所指向对象的“亲亲”和“尊尊”关系,秉此采取社会行动,并赋予其价值意义。
①安文研:《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原理——从服服制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2019年第2期;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年第4期;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吴飞:《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②潘光旦:《说“伦”字》,《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
③潘光旦:《“伦”有二义》,《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6—265页。
④潘光旦:《说“五伦”的由来》,《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6—291页。
⑤周飞舟:《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4期;翟学伟:《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社会》2016年第5期;秦鹏飞:《儒家思想中的“关系”逻辑——“伦”字界说及其内在理路》,《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⑧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2—73页。
⑩潘光旦:《过渡中的家庭制度》,参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9页。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