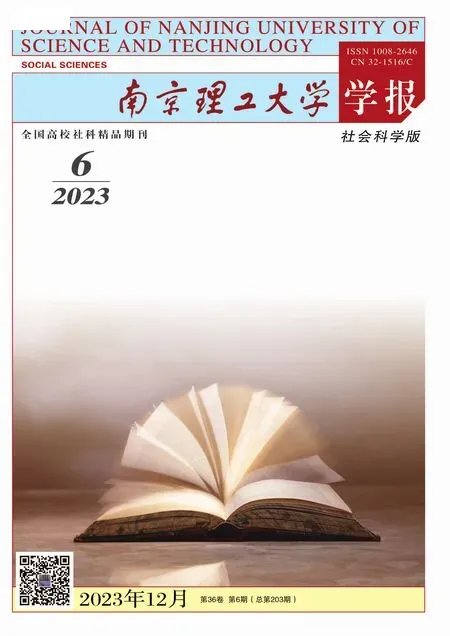俄罗斯文学中的汉语借词
叶连娜·伊孔尼科娃,石雨晴
(1.萨哈林国立大学 语文、历史和东方学学院,俄罗斯 萨哈林 643000;2.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语言常常会“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和概念。这种被“借来”的词汇叫做“借词”。由于许多借词在语音、语义、语法等方面发生变化,所以汉语中的借词并非都能被母语者轻松辨识,同样地,俄罗斯人也常常需要推测某个俄语词汇是否与他国历史或文化相关联。本文主要探讨汉语词汇是如何逐渐融入俄罗斯文学的语境,成为文学作品乃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代俄语包括大量源自汉语的词汇,例如“人参”“琵琶”“糖葫芦”“粉条子”“八角”“旗袍”“台风”等。据张红玲在《略析俄语中的汉语外来词特点以及分类》一文统计,俄语中的汉语借词及其派生词已逾百例。这些汉语借词不仅成功融入了俄语口语和新闻文体,还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珍珠”和“茶”在最早通过突厥语传入俄语的汉语词汇之列。“珍珠”一词早在12世纪的古罗斯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中就已出现两次。在一个情节中,它与眼泪和不幸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个情节中,它被看作是精神纯洁的象征。当然,这个词在俄罗斯经典文学中非常活跃,出现在亚历山大·普希金、尼古拉·高尔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等众多作家的作品中。此外,“珍珠”还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的标题中,例如尼古拉·列斯科夫的短篇小说《珍珠项链》(1885年)、尼古拉·古米廖夫的诗集《珍珠》(1910年)。而在瓦列里·勃留索夫的诗歌《项链》(1910年)中,有如下句子:
大珍珠,小珍珠
日复一日穿成串
黄珍珠,红珍珠
中间有根白银线
在俄罗斯文学中,“珍珠”的意象非常广泛。一方面,珍珠是一种装饰品或宝物,另一方面,它们被用来比喻牙齿、雨滴、雪花和眼泪,还用来形容词语和声音,鲜明的记忆和一些珍贵的事物。比如,“书中之言如珍珠”是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它强调了书面文字的重要和珍贵。在现代俄罗斯文学中,关于“珍珠”及其衍生词的意象仍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茶”一词在俄语中首次出现于17世纪,几乎在19世纪所有俄国文学经典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这个词在尼古拉·高尔基、米哈伊尔·萨尔特科夫-谢德林、伊凡·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安东·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中频繁出现。这些作品中经常描绘家庭成员或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享用茶的场景。在品茶的过程中,通常会使用茶炊和茶壶等器皿,也会摆放糖(通常是碎糖或块糖)、果酱和蜂蜜,以及各式饼干、馅饼和甜点。喝茶的同时也在进食。因此,在过去“茶”不仅与“喝”这个动词连用,还与表示进食的动词连用。例如,在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编年史》(1856)中就出现了“吃茶”的表述。在俄国文学中,人们喝茶时使用玻璃杯、茶杯,有时还会用小茶碟,正如安东·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农民》(1897)中所描述的那样。
词汇“茶”已经深深地融入俄语,并衍生出许多同根词。带有文学性质的词有“茶壶”(用于冲泡茶的器皿)、“茶会”(饮茶的过程)、“茶艺师”(专业的茶艺师)、“一片茶叶”(一片泡开的茶叶)等。口语中的词汇有“喝茶消遣”(在泡茶过程中共度时光)和“茶水费”(字面上是指“有关茶”的费用,即额外的服务费)等。此外,俄语中还引入了“白毫茶”一词。尽管它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得不太频繁,但在安东·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1895)的注释里援引了报纸《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则报道,提到一些狱吏将白毫茶当做烟抽。
当然,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关于茶的艺术描写不胜枚举。例如,在尤金·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愤怒》(1955年)中,提到品茶已成为了解和观察他人的借口或契机。在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中,与“茶”相关的韵脚也颇具趣味。比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鲍里斯·斯卢茨基都用“茶”(чай)和“偶然”(невзначай)来押韵,萨沙·乔尔内则使用“茶”(чай)和“救助”(выручай)作为韵脚。此外,在谢尔盖·叶赛宁的诗歌中出现了“茶”(чаю)和“回应”(отвечаю)以及“肩膀”(плечами)和“茶”(чаем)等韵脚。米哈伊尔·库兹明则在作品中使用“上海”(Шанхай)和“茶”(чай)入韵。20世纪下半叶,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新的押韵方式,例如,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使用“茶”(чаю)和“祝愿”(желаю)、约瑟夫·布罗茨基使用“茶”(чая)和“感受”(ощущая)进行押韵。也许,最引人瞩目的是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于1927年创作的诗歌《你来念念这首诗,上巴黎、中国去一次》,他以巧妙的方式将“茶”和“中国”这两个词押韵,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诗意形象。而在数十个俄罗斯谚语和口头禅中也能找到“茶”的身影,例如“多喝茶汤,寿命悠长”或“饮茶不寂寞,七杯一口喝”等。
除了“珍珠”和“茶”这两个词,还有其他中文词语进入俄语文学。然而,这些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使用并不频繁。这是因为这些词汇的意义相对狭窄,通常只在与中国接壤的某些地区广泛使用。例如,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台风”“人参”或“房子”等词汇从汉语口语走进了经典远东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马克西莫夫(1851—1896)和弗拉基米尔·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的作品中使用率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台风”一词在1890—1907年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词典》中有所记载。然而,这个词在融入俄语之前曾在伊凡·冈察洛夫(1812—1891)的作品《帕拉达战舰》(1857)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中出现。实际上,伊万·冈察洛夫在参与由尤夫拉西·普特亚京指挥的环球旅行期间,在自己的随笔中提到了这个中文词汇,用以描述强风的特点。随着《帕拉达战舰》的出版,“台风”一词也开始在科学语言中广泛使用。例如,安东·契诃夫在前往萨哈林岛之前,曾将一本附带台风路径图的《关于中国和日本海上的台风路径》(1881)列入了他的书单。
在弗拉基米尔·阿尔谢尼耶夫的小说和回忆录中,不仅频繁出现了“台风”一词,还出现了“房子”,用来指代远东某些民族独有的居住建筑。与此同时,这些词在音韵和语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俄语中,“房子”一词以字母“а”结尾,被归类为阴性名词。这个词在弗拉基米尔·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比如,在《乌苏里地区之行》(1921)中,出现很多次。
在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几个使用中文词汇的例子。自1902年起,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与父亲一同在关东半岛旅顺港短暂居住(不到一年),并曾去过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或许正是在这段短暂的时光里,他接触到了一些中文词汇,这些词汇后来出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例如,在他的诗歌《微风轻叹,瓷器轻唱》(1905)和《夜间漫步速写》(1906)中出现了“房子”一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诗人使用“房子”一词时,单词的重音不仅可以在我们所熟悉的第一个音节上,也可能会采用与我们的习惯不同的方式,将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这样做是为了押韵。
1933年,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创作了一部名为《人参》的中篇小说。“人参”是一个从中文翻译而来的词汇,意味着生命之根。在这位俄国作家的故事中,人参这一形象成为了故事中的主导,它代表着生命本身,代表了生命的奥秘和追求生命意义的人。除此之外,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作品中还使用“房子”“台风”等中文借词。这些词汇成为了环绕着小说主人公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词语是文化的因子,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作家的视野,也为作品增添了异国风味。并非只有东北亚的作家使用具有异国情调的借词。例如,符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剧作《铁甲列车14-69》(1927)中,除了“人参”和“高粱”等熟悉的词汇外,还包括其他俄语读者几乎不知道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伊万诺夫的剧本(以及同名小说)中,故事发生在1919年,地点位于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道路上。这一故事背景决定了中文词汇的融入,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中国主人公沈彬吾。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中国故事》(1923)中也出现了一个带有连字符的中文名字,即森津波。此外,在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1893—1930)的诗《莫斯科的中国》(1926)中,出现了张作霖、吴佩孚的名字。
大部分进入俄语及俄语文学作品的汉语借词与文化和生活领域有关。这些借词通常是泛指性的,包括饰品、宝石、饮品、自然现象、谷物、职业,甚至绰号。当然,在文学作品中,也可能包括一些与历史和政治相关的专有名词,如地名和人名。
借词是文化接触的产物。深入研究俄语中的汉语借词,并梳理它们融入俄语文学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广泛多元的文化空间。这些借词就像中俄人民一样,相互交流。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退场,而有些则深深融入新的语境,这一过程产生了特殊的语言学和跨文化学材料。从一种语言融入到另一种语言的词汇越多,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就越深刻。国家之间的联系越密切,词汇的流动也就变得越频繁。这种文化和语言的交融,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和语言本身,也丰富了人们对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认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