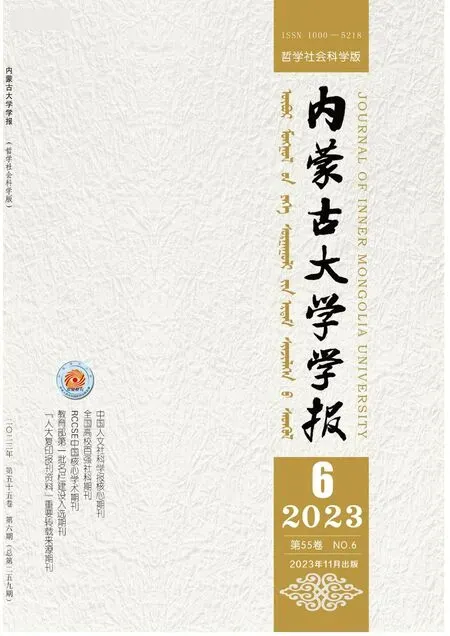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演变及动因分析
许有胜, 马宏程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49;2.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国土面积约为273 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家。 全国约有140 个民族,主体民族是哈萨克族,境内语言有120 余种。 目前哈萨克语和俄语同为该国官方语言,是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
语言政策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语言政策的调整,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 研究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对我们了解其他新兴独立的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演变
关于“哈萨克”的来源说法不一,学界较为认同的是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5 世纪初期。 在此之前,哈萨克斯坦境内一直以独立的游牧部落和突厥部落形式存在,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直到15 世纪,“哈萨克”才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1456 年创立哈萨克汗国,形成哈萨克语,采用的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19 世纪开始至今,哈萨克斯坦不同阶段制定的语言政策均体现了政府对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国家利益的考量。
(一)强制推行俄语阶段(1847—1916 年)
1847 年,俄国完成对哈萨克地区的征服,哈萨克汗国灭亡,俄国取代哈萨克汗国进行统治。此后直到十月革命之前,沙俄政府为了在精神上削弱哈萨克人民的民族意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直在哈萨克斯坦推行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 在这期间,沙俄政府打破哈萨克斯坦原有的教育体系,对民众尤其是哈萨克上层开展新的俄式教育:兴办俄语学校,强制推行俄语,实行“义务国语制”,强迫包括哈萨克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学习、使用俄语,同时禁止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及语言教学,[1](3)甚至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其他民族使用本族语的法令。 此外,还在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习俗、民族语言中大量渗透俄语。
这一阶段的语言政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制推行俄语,使得部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文化印迹和精神特质丧失,但同时也把俄罗斯文化引进哈萨克斯坦,增进了哈俄文化交流,并在客观上弥补了哈萨克斯坦原来不太完备的教育体系。 二是,大力推行俄语教育,使得哈萨克语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但该政策只对上层的精英群体影响较大。当时哈萨克斯坦文盲率较高,据统计,1897 年识字率仅为8.1%,[2]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他们对语言的接受能力也相对较低,且沙俄政府关注哈萨克精英阶层,早期创办的部分学校只对贵族开放,所以该阶段俄语推行政策对普通民众影响微弱。
(二)民族语言本土化阶段(1917—1933 年)
1917 年11 月,哈萨克斯坦人民在十月革命期间,宣布脱离苏维埃俄国的管辖,成立了阿拉什自治共和国。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于1917 年11 月15 日颁布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承认各民族间平等共存,少数民族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 苏联成立后,列宁主张各民族应该一视同仁,各民族的语言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并将这一思想写进法律加以保护。 如俄共(布)十大上《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当前任务的决议》,将帮助各族人民发展使用民族语言的相关文化活动及语言教育作为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俄语仅保留为族际共通语地位。 决议还要求建立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学体系。[1](4)此后的俄共(布)十二大、俄共(布)中央四次会议都延续了这一政策,并在俄共(布)中央四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语言本土化政策。 得益于这一时期语言平等政策,哈萨克斯坦开始重视本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哈萨克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批哈萨克文报刊出现,1929 年完成了拉丁字母作为官方文字的改革。 这一阶段,以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国民教育体系得以建立,1926 年哈萨克斯坦民众识字率提高到25.2%。[2]
(三) 哈萨克语被限制发展阶段(1934—1988 年)
斯大林统治初期仍旧推行“语言平等”的政策,但在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斯大林改变了列宁时期的语言政策,在1934 年联共(布)十七大时终止推行民族语言本土化运动,要求全部学生都必须学习俄语,后又将哈萨克文由使用不到10年的拉丁字母改为西里尔字母,与俄语保持一致。1938 年苏联发布了《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要求俄语作为必修科目引入哈萨克语中小学,所有学校必须从小学一年级起开始学习。 20 世纪50 年代初,城市里的哈萨克语中小学陆续关闭,同时禁止在俄语中小学学习哈萨克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民族关系呈现出自由化的趋势,对本民族语言也更加关注。 民族语言在教育领域的功能曾得到短暂的恢复,但很快路线发生变化,1958—1959 年进行的教育改革扩大了俄语的应用范围[1](7),俄语学习又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意义。 赫鲁晓夫曾宣称:“我们掌握俄语的速度越快,建成共产主义就会越快。”[1](7)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提出了“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民族语+俄语”双语制成为当时主要语言政策之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基本延续了斯大林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限制包括哈萨克语在内的民族语言、实际提升俄语社会地位的语言政策。
戈尔巴乔夫时期,哈萨克语被限制的状况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有所改变。 1986 年12 月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阿拉木图事件”,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哈萨克青年进行示威要求拥有国家主权。示威虽然促使通过了《关于改进共和国哈语学习的决议》(第98 号令)和《关于改进共和国俄语学习的决议》(第99 号令),但并没有实际执行。[3]
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苏联政府明确规定,俄语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语”①,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俄语都是实际的唯一指定用语。 这一政策限制了哈萨克语的发展,造成了哈萨克语的极度萎缩。 从20 世纪30 年代后期开始,哈萨克斯坦初步建立起来的民族语言教育体系开始衰退,数量大为减少,俄语学校数量激增。 1958年,有75%的哈萨克族小孩去哈萨克语学校学习,而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只剩下34.4%。[4](35)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全国人口中能流利使用哈萨克语的人不超过30%,而能熟练使用俄语的占73.6%,有1/3 左右的哈萨克族不会或基本不会使用母语。[5](133)由此可见,20 世纪30 年代以后,哈萨克语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四)哈萨克语作为国家主体语言地位确立阶段(1989—2005 年)
苏联政府对哈萨克民族语言的政策在20 世纪80 中期开始遭到强烈反弹,加之初获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民族意识的推波助澜,最终形成一股强烈要求将哈萨克语作为国语的浪潮。
哈萨克语作为国家主体语言地位的确立之路从一开始就比较曲折,1989 年颁布的《语言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哈萨克语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语,俄语是族际交际语。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通过《哈萨克国家独立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等法律继承了这一方针。 在国家法律层面,俄语的社会地位下降,俄语教学在哈萨克斯坦受到压缩,俄语学习时间削减,俄罗斯人高校入学比例不断下降。 但由于俄语在哈萨克斯坦根深蒂固,其在文化、经济领域仍发挥着较大的社会功能。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哈萨克斯坦对俄语的态度开始缓和,但对哈萨克语作为国语地位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为了促使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得到切实的落实,在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下,哈萨克斯坦又相继出台了很多法律条文,积极从立法的角度保障哈萨克语的地位。 1996 年11 月出台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政策构想》,1997 年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 这两份文件均强调了哈萨克语作为国家语言的掌握、使用上的优先及国家语言在教育机构中的地位。[6]2001 年2 月哈萨克斯坦又发布了《2010 年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发展国家纲要》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各项语言发展计划,明确要求在公共领域推广使用哈萨克语,全面促进各层次的哈萨克语教学。
然而因为历史的原因,哈萨克语的推广遇到很多困难,其教育、教学体系不健全,俄语在工作场所的实际使用情况远高于哈萨克语。[3]
(五)多语言政策阶段(2006 年至今)
为促进哈萨克斯坦积极融入全球一体化,作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措施,2006 年10月,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议实施“三语政策”,即大力发展哈萨克语、支持俄语、学习英语,既强调了哈萨克语作为国语的主体地位,又保持了俄语在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也为英语等其他语言提供了发展空间。 这为哈萨克斯坦的语言多元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哈萨克斯坦2011 年实施的《2011—2020 年期间语言的作用与发展国家纲要》宣称,其主要目标是详细制定一套和谐的语言政策以推广国家语言和本国居民的所有其他语言,并要求哈萨克斯坦成年人在2011—2013 年、2014—2017 年和2017—2020 年三个时间段掌握国语、俄语、英语的人口数量达到一定标准。 2020 年初,哈萨克斯坦又批准了《2020—2025 年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实施计划》②,在推动哈萨克语拉丁字母化的同时,也强化了英语教学与应用,要求逐年提高“三语人员”的人口比例。
在推进多语言政策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也积极展开了汉语教学。 其国内高校与我国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创建了孔子学院,开设了汉语专业或者相关课程。 2013 年9 月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倡议与“光明之路”③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对接,为汉语在哈萨克斯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无论是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还是哈萨克斯坦学习汉语的民众,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目前哈萨克斯坦已创办5 所孔子学院,在华留学生已达1.4 万人。④现阶段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不断得到稳固发展,俄语仍保持族际交际语地位,英语是第一外语,汉语为第二外语。哈萨克斯坦在深化发展国家语言地位的同时,也尊重其他民族语言的平等发展。 哈萨克斯坦国内呈现语言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语言政策演变的动因分析
语言政策的制定直接体现着国家利益。 “语言政策没有独立性,其目标始终对应着国家利益的需要。”[7]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独立前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由于没有独立的主权作为立法保障,语言政策的制定权被控制在沙俄及苏联政府手上,主要服从沙俄殖民统治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需要。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也经历了多次变迁,在失衡中寻求新的利益平衡,通过不断的调节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一)独立前的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演变动因
18 世纪的沙俄政府认为俄罗斯民族高于其他一切民族,鼓吹民族优越论,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沙俄统治者认为,“国家的权力限定国家利益;国家要谋求自身利益就要谋求权力,就要支配别人,也就是说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够实现”[8]。 他们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血腥统治,排斥包括哈萨克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以实现沙皇一个宗教(东正教)和一个民族(俄罗斯民族)的专制统治。 基于这样的思想,沙俄统治者在哈萨克斯坦强制推行俄语,公文处理和社会活动大面积使用俄语,哈萨克语只在私人场合使用。[4](32)
十月革命后,苏俄高举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 为体现制度的优越性,苏联领导人提出“各民族语言平等”,宣布苏维埃俄罗斯境内没有官方语言,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选择说“母语”,每个人都有用民族语言接受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2]这种语言本土化政策的优势很快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得到了彰显。 哈萨克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缓解了沙俄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对立问题,从而使得新生的国家政权得到包括哈萨克人民在内的各民族的积极支持。 这种支持在抵御国外势力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执政前期延续了列宁时期的语言政策,但在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则转为推行“一国建成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苏联人民急切的实践任务……这样就没有了民族差异,尤其是语言差异。 这些都被视为阶级差异最终消失的过程。”[2]同时,“联邦制”的国家形式名存实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在各加盟共和国大力推行俄语,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使用。 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已被斯大林当作一种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政治上一体化管理及控制社会的手段。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延续了这一理念。
(二)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演变动因
哈萨克斯坦在建国之初,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增强哈萨克族的主体民族意识,提升民族地位,构建民族认同,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 而语言政策动机的认同的强烈表现形式是民族主义,这是语言运动的主要动机。[9](38)独立前后哈萨克斯坦实行以民族语言作为国语的政策,试图以此实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 1990 年颁布的《国家主权宣言》中明确规定,哈萨克族是缔造国家的民族,是国家民族文化的核心。 当时的语言政策在提高民族意识、复兴哈萨克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中亚各国具有普遍性。 中亚各国都在独立之初通过颁布新的语言法或宪法,来大力发展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 由于它们把使用主体民族语言视为新独立国家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因此纷纷兴起了“语言民族化”运动,将主体民族语言规定为国语。[10]
20 世纪 90 年代初,哈萨克斯坦将哈萨克语规定为国语的同时,努力降低俄语的语言地位,压缩了俄语在教育和公共领域的使用空间,以提升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 但由于苏联时期俄语的强势地位,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社会中已根深蒂固,在经济领域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是哈萨克语无法比拟的,抑制俄语也对经济发展及与世界接轨方面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因此在1995 年第2 部宪法、1997 年语言法和1999 年《1999—2010 年各语言功能与发展政府纲要》中,又放缓了对俄语的抑制,确定了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地位。 这种调整平衡并妥善处理了哈萨克语与俄语的关系,保证了两种语言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了对国家政治利益的权衡,更表明了对国家经济和文化利益的考量。
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自我发展,语言规划也是如此,开放才能带来最大利益化。 为了更好地稳定社会团结、发展本国经济、顺应语言现代化国际化的趋势,2006 年哈萨克斯坦开始推行多语言政策。 哈萨克斯坦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融入世界,过渡到了新型化、多元化语言发展的时代,实现了国语、俄语、英语及其他语言的同步发展。
总体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能够根据国内的政治经济需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本国的语言政策,使这些政策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
三、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演变带来的启示
(一)主权是国家和民族语言地位确立的根本保证
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规划,首先需要国家主权的独立作保障。 被殖民或主权受限的国家,无法拥有独立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权利,那么,该国语言政策的制定一定会受制于宗主国或联邦政权,从而深深打上宗主国或联邦政权意志的烙印,本民族的语言权利自然严重受损。 无论是在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所推行的俄罗斯沙文主义都强力推行俄语,抑制哈萨克民族语言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没有民族自决权,语言政策只能由沙俄或苏联政府统一制定规划。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才走上了语言政策自我规划的道路。
与任何其他政策一样,语言政策也需要通过一些具体途径和专门程序来推行。 哈萨克斯坦推行语言政策的主要途径有法律文件、总统签署命令、政府签发指令、教育部等部门的决议及州长等政府官员的命令。 哈萨克斯坦的主权独立为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提高民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对语言政策指令性文件的分析可知,哈萨克斯坦政府为哈萨克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二)语言政策的制定要全盘规划、多角度考虑
制定语言政策必须通观全局、契合社会现实,要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约因素,不能靠一厢情愿的主观判定。 哈萨克斯坦建国之初,政府为了提升民族意识,一味强化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对俄语进行断崖式打压,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在教育方面,关闭了大量俄语学校,导致很多年轻人俄语阅读能力下降,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 在经济方面,由于俄语的语言成熟度和国际地位较高,压缩俄语空间对哈萨克斯坦的劳务输出和国际交流造成了较大障碍,最终影响并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政治方面,大量以俄罗斯人为主的斯拉夫族人群受到严峻挑战,不懂哈萨克语的人被排挤出关键部门,就业和生存环境恶化,导致这些俄语居民迁出中亚国家而移民俄罗斯,造成民族关系十分紧张。[11]
吸取前期教训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后,及时调整语言政策,适当提高了俄语地位,平衡了哈萨克语和俄语的权利空间,其负面影响才得以逐渐消除。
纵观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历时发展变化,独立前的语言教育主要体现了沙俄政府和苏联政府意志;独立后的语言政策更多是为了保护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演变是新兴独立国家语言政策的一个缩影。 很多非主权国家独立后语言政策演变的大致路径都是“宗主国语言(殖民语言)占统治地位——民族语言地位上升成为国语——适应时代发展为多语言政策”。 这一基本路径的形成背后,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动力和推手。
注释:
①1938 年颁布的文件《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州的学校必须学习俄语》及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都明确规定俄语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语”。
②丝路新观察官微,“哈批准2025 语言发展计划:向拉丁字母过渡、强化英语地位”,2020-01-15,https:/ /k.sina.com.cn/article_6556793383_186d0ba2701900mqy0.html? from=edu。
③2014 年,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光明之路”计划,致力于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④哈萨克斯坦在华留学生已达1.4 万人 学汉语蔚然成风,2019-01-15,https:/ /www. yidaiyilu. gov. cn/xwzx/roll/773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