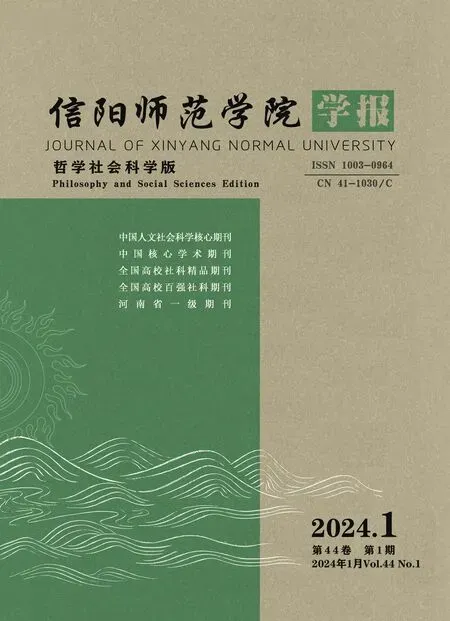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研究
夏金梅,吴紫莹,彭荣胜
(信阳师范大学 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学者们基本肯定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1-2]。2017年,“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后,直接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现阶段从全国层面直接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较少,理论探讨居多[3]。现有关于城镇和乡村发展的实证文献多数从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土地、人口、环境、空间等维度选择指标[4-5],近年来也有部分文献基于新发展理念五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6]。从最初的理论构建指标体系,到运用指标体系实证判断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情况[7],再到进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8]、分析影响因素[9]及经济增长效应[10]等,该领域研究有所深化拓展,研究范围实现了从单一省份到跨区域比较的拓展[11-12]。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网络层次分析法、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总体来看,现有实证文献侧重城乡融合程度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指标选择侧重城乡一体化反映。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测度则需要分别筛选反映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目前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的研究多数为省域或区域分析,全国维度进行测度和比较的研究成果不多,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我国四大板块城乡发展的区域差异比较显著,尤其是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实施对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尤其重要。了解我国四大板块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以及空间演进,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说明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整体战略,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分别由无数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这些不同构成的运行状况对城乡社会整体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选择,在宏观—微观、数量—质量的设计导向下,遵循系统性、针对性、动态性、可比性、可得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尽可能全面、直观真实地反映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特点和状况,选择权威的公开数据,客观反映各指标之间的实际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传统城镇化而言的城镇化模式,重在“以人为核心”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2013年中央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和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以来,有关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这里依据2014年李克强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内涵的20字表述,即“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结合研究需要,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3-14],将新型城镇化细化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5个维度。其中,将“四化同步”内含于“经济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产业融合,实现四化同步,夯实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城镇化”在“传承文化”之外,还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开展公共设施配套供给,提升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终目标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生态城镇化”主要任务是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美丽生态、清洁生产、美好生活的城镇化绿色发展,倡导节约资源、环境友好、低碳环保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解决城市环境生态、生产和生活污染和治理问题。“空间城镇化”原始动力是人口的空间集聚、产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呈现出城市人口和土地空间关系的演变,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达性,空间城镇化的目标在于改善城市原有空间格局,进而解决城乡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人口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就业、定居、落户问题,提高进城人口生活质量,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旨在凸显新时代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生态的现代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空间优化以及“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选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为二级指标,并在这5个维度基础上选定16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及权重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具体目标要求,即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从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民增收、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方面保障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意味着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产业要更有生机和活力,顺应我国农业主要矛盾从总量不足向结构失衡的变化,应致力于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生态宜居”强调农业绿色发展,农村环境高效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乡村,要关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领域的污染治理问题,依托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坚持乡村发展的生态底线;“乡风文明”关注乡村主流价值形成,通过教育普及提升农村整体文明程度、通过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端正乡风、在保持乡土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特色与城市现代文化的融合,通过移风易俗促进农民理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政治基础,关系着乡村治理的主体性,要求改革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有机结合,融合自治、德治和法治,形成一套合作治理的乡村治理体系[15];“生活富裕”的目标是让全体农民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的双重富足,涉及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提升、社会保障力度加大等多方面的内涵。目前关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多以这20字目标要求为依据,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来构建,本文参照已有相关研究成果[16-17],以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内涵为5个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定16个三级指标,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二)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1.确定指标客观权重
进行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各个指标权重。鉴于主观赋权法容易受到个体主观因素制约,为了得到较为客观的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
2.计算子系统发展指数
运用熵值法得到各指标的综合权重后,利用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与权重相乘。
3.计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
(1)
式中,C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U1、U2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依据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计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D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和β分别为两个子系统的权重,且α+β=1。设定α=β=0.5。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18],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值划分为以下5种程度及具体协调类型,如表2所示。

表2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4.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部分年份和指标数据缺失严重,从指标获取的完整性、可得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准确性角度出发,选取2010—2019年全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对30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各五个维度涵盖的32个指标,共计9 000多个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计算,得到各指标客观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依据各指标权重,分别对各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乡村振兴发展指数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全国和各区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相关数据来自2011—202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计算得出,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平均值法填充。
三、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一)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根据表1各指标权重,计算所统计的30个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进而得到2010-2019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的各区域均值和全国均值,根据2010-2019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变化(见图1),对全国和各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进行对比和分析。

图1 全国各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变化(2010-2019年)
从2010-2019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来看,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整体呈增长趋势。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质量要求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统筹安排,顶层设计落实到新型城镇化实践,带来全国和各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的持续增长,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逐渐拉开差距。自2014年以来,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逐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速度放缓,显示出后劲不足的态势。2019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0.410)进入0.4-0.5区间。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0.510)突破0.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0.43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0.35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中部地区进一步拉开差距;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0.320)跃入0.3-0.4区间,尽管增长速度较快,但仍然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2010-2019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增长趋势,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值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
(二)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根据表1各指标权重,计算所统计的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得到2010-2019年乡村振兴发展指数的各区域均值和全国均值,根据2010-2019年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变化(见图2),对全国和各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进行对比和分析。

图2 全国各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变化(2010-2019年)
从2010-2019年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来看,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指数整体呈增长态势。2010-2019年,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平稳增长;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波动较小,中部地区逐渐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西部地区也逐渐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波动较大,增长缓慢。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全国及四大板块乡村振兴持续发展。至2019年,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0.357)进入0.3-0.4区间。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0.410),尽管增长缓慢,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0.388)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0.3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中部地区进一步拉开差距;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0.299),尽管增长速度较快,但仍然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而言,2010-2019年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增长趋势,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
(三)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
通过计算得到2010-2019年本文所统计的30个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如表3所示,依据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变化,分析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表3 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2010—2019年)
从表3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值可以看出,2010-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整体向高一级状态提升,由于耦合协调度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大小及其波动程度影响,2010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程度的是东部地区的北京(0.662)、上海(0.623)、江苏(0.614);失调的是西部地区的贵州(0.314)、云南(0.369)、甘肃(0.344)、青海(0.356)、宁夏(0.386);濒临失调的有内蒙古(0.481)、吉林(0.489)、安徽(0.495)、湖北(0.487)、广西(0.425)、海南(0.491)、重庆(0.475)、四川(0.478)、陕西(0.488);其余省份均处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初级协调状态。2010-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普遍得到提升,至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均摆脱失调状态,其中东部地区北京(0.740)、上海(0.726)、江苏(0.708)、广东(0.700)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度上升为高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贵州(0.466)、甘肃(0.491)、青海(0.487)进入濒临失调,云南(0.517)、宁夏(0.532)、海南(0.598)、广西(0.537)、陕西(0.588)、辽宁(0.586)、吉林(0.563)进入初级协调状态;其余省份均处于中级协调状态。整体来看,2010-2019年,耦合协调度最高的省(市)分布于东部,协调度最低的省(市、自治区)分布于西部地区,协调度波动较大的是位于东北地区的省份,协调度差异较小的是中部地区的省份。
四、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演进
(一)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演进
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研究期内2010年和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进行处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空间演进情况如下。
2010年,统计范围内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是东部地区的北京,高于0.4的还有广东和天津,其次是江苏、上海、浙江、中部地区江西和东北地区辽宁;新型城镇化水平处于 0.2-0.3之间的省(市、自治区)最多,低于0.2的区域集中在西部,贵州、甘肃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低于0.1,地区间差异较大。
2019年,整体上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状分布格局。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还是北京,其与广东发展指数均高于0.6;0.5以上高值区增加了福建、上海、浙江;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分布于0.4-0.5之间的省份明显增加,由南北两端发力,逐渐向中部地区演进。天津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变化不大,一直处于0.4-0.5之间;与其情况类似的还有东北地区的辽宁,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也渐缓,一直处于0.3-0.4之间。发展指数最低的依然在西部地区,201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低于0.1的甘肃,至2019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提升明显,进入0.2-0.3区间。整体而言,2010-2019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从东到西呈现梯度递减的趋势,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自治区),如四川、重庆、安徽、湖南等省份凭借后发潜力保持较快增长态势,逐渐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二)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演进
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研究期内2010年和2019年的乡村振兴的测算结果进行处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空间演进情况如下。
2010年,统计范围内,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指数分布于0.1-0.5之间,乡村振兴发展指数高于0.4的只有东部地区的上海;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分布于0.3-0.4之间,分布于这一区间的还有中部地区河南、湖南、山西,东北地区的辽宁;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分布于0.2-0.3;低值区集中在西部偏远地区的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201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指数均得到较大提升,分布于0.2-0.6之间。高于0.4的区间增加了北京、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突破0.5,仍然是乡村振兴指数最高的地区。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振兴指数集中分布于0.3-0.4之间。2010-2019年,中西部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指数增速明显,省际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分布上西部地区不断向中部递进,趋向均衡发展。整体而言,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2018-2019年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提升较快,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空间演进趋势基本一致,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
(三)全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进
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研究期内2010年和2019年统计范围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进行处理,整体上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演进情况如下。
2010年,东部地区的北京耦合协调度最高,与上海、江苏同处于中级协调;其他大部分省份处于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状态;失调地区为西部地区的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宁夏。
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逐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东部和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市)耦合协调度达到0.6以上,处于中级协调状态,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失调地区贵州、甘肃、青海过渡成为濒临失调,云南、宁夏则升入初级协调。濒临失调区域的海南、广西、陕西、辽宁、吉林则升级为初级协调。高级协调集中在东部地区,如2010年属于中级协调的北京、上海、江苏,还有初级协调的广东,至2019年一起升入高级协调区域,耦合协调度最高的还是北京;中级协调区域明显向中部集中,增加了中部地区6个省份,同时进入这一区域的还有东部地区的天津、河北、福建,西部的内蒙古、重庆、四川、新疆和东北地区的辽宁,各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五、结论与建议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下,我国各省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逐渐改善,各省(市、自治区)城乡差距缩小,反过来又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提升。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全国除港澳台及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论为:第一,2010-2019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演进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趋势,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高值区域均分布于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低值区域均分布于西部地区,整体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演进轨迹呈现出由东北、西南两端发力,逐渐向中部地区演进的态势。第二,2010-2019年,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但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其乡村振兴发展指数仍然较高。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中部地区和西部内蒙古、重庆、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指数增速明显,空间分布上不断向中部递进。第三,至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大部分省市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的阶段,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逐渐增加。
总体而言,2010-2019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反映在空间分布上,则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各区域原有显著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不论是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还是从两者耦合协调度来看,各区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综上,促进区域发展要根据区域情况分类施策: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通南北,一方面承接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快速发展的辐射,另一方面对西部、东北地区又有一定程度的带动效应;西部、东北地区部分省、市、自治区,如内蒙古、重庆、四川、新疆、黑龙江等,对接中部地区,呈现出赶超势头,这部分省、市、自治区已成为各自区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对东部地区来说,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更关注乡村建设和发展,以防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差距较小,具有良好的协同发展基础,需促进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高级协调;对西部地区来说,要防止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省(市、自治区)陷入因城镇化增速放缓而拖慢乡村振兴节奏的低水平耦合陷阱;东北地区由于区位、基础设施、资源等客观条件所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潜力不足,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需要政府助力,在农业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农村三产融合,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