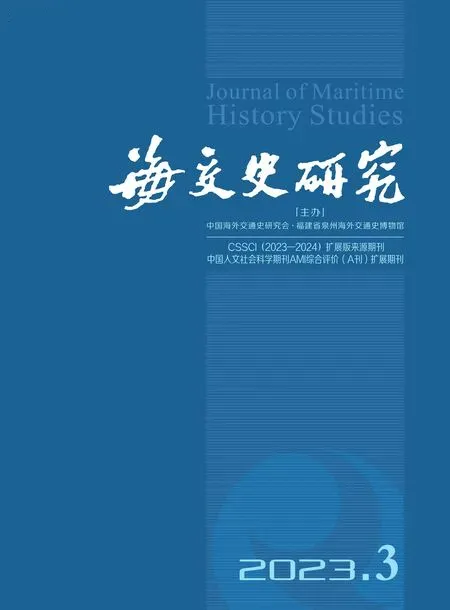从世界意义到地方经验:近来英法关系研究中的“海峡视角”
徐桑奕
国内学界对于英法关系这对近代世界史上的重要国际关系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多数是将视角集中在重要事件、时段,考察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互动;而对于英法关系在民间或地方层面上的具体运作,则仍有若干拓展空间。近年来,相关著述也开始涌现。例如,剑桥大学学者雷诺·莫里厄(Renaud Morieux)的《海峡:18世纪的英国、法国和海洋边界的构建》(1)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England,F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Bor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一书,乃是这一方面研究的典型之作;另外,像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鲍尔(Daniel Baugh)的《全球性的七年战争》(2)Daniel Baugh,The Global Seven Years War,1754-1763,London:Routledge,2011.,虽以“全球”为名,但也是在关注英法在不同地域中的不同形式的竞争。在此,笔者将以类似书目为依托,尝试对18世纪英法关系中的“微观”“地方”视角进行部分解读,提供些许视角,并求教于方家。
一
海峡地区,可谓是英法两国互动的起点和最前沿。丹尼尔·鲍尔在著述中曾对七年战争时期英法在海峡中的交锋作了叙述。1758年,英国逐渐有了一些富余的陆军和舰艇,因此政府便酝酿对法国沿岸进行攻击。当年的春夏之交,英国舰队到达圣·马洛(St Malo)、康卡勒(Cancale)等地,并以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对相关地区展开了突袭。鲍尔提到,英国十分重视对一些要塞的围困和占领。例如瑟堡(Cherbourg),就是当时法国的一个重要的渔业和私掠船只的集散港口。(3)Daniel Baugh,The Global Seven Years War,pp.306-309.
与许多学者所关注的“宏大叙事”相比,渔业等方面在学术研究中所得到的关注度有待提高,而学者雷诺·莫里厄则着重关注了这一主题,他的《海峡》一书是一部全面反映18世纪英法在海峡地区竞争的著作。从结构上看,全书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边界的发明”(Theborderinvented),主要论述了英法居民在英吉利海峡活动的历史,以及双方的对立与敌意对海洋边界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强制的边界”(Theborderimposed),考察了英法对海洋领土和资源的争夺,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军事和法理问题。第三章“越过边界”(Transgressingtheborder),论述了两国海洋人口对海峡的利用,以及他们各种形式的互动和交往。莫里厄认为,一方面,由于18世纪英法关系的敌对,英吉利海峡首先成为了两国分异和隔离的一种隐喻,作为边界的海峡是在不断的纠纷与争议中,被人为建构的。(4)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p.341-342.另一方面,正如海水的流动性一样,海峡本质上也是“流动的边界”(liquid borders)(5)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18.,而并非地图上所标示的那样明确和森严。在这当中,人口、物质和文化也是具有流动性的,虽然18世纪的英法长期处在交锋状态,但若聚焦于较为微观的地方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不可否认的是,两国的渔民、私掠者等群体会因为各种海洋资源而产生龃龉,但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是多样的。渔业是英法争锋的其中一个场域,特别是在英吉利海峡这一资源丰富的海域,双方的争夺时刻都在进行。《海峡》一书将渔业竞争置于18世纪英法海洋争夺的大背景下予以观察,本文也将重点关注莫里厄所述的海峡渔业问题。
渔业一直是英国国内经济领域的重要门类之一,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素来受到社会的密切关注。英国渔业发展拥有上佳的自然条件,西南部的德文郡(Devon)和康沃尔郡(Cornwall)位于布里斯托尔海峡和西部远海深水区的交汇处,为其渔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上天的恩赐”,东海岸的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等地也素有渔业重镇的声名。时至18世纪,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增加,渔业发展也面临着严峻考验。由于两国分处英吉利海峡两岸,故在该处渔业方面的诉求相近,加之长时间的兵戎相向,纠纷的产生在所难免。从现有成果看,学界对英国渔业的关注重点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相关法案、渔业管理机构与策略的演变;第二是渔业发展历史概况、不同渔区的个案分析;第三是渔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可见,对18世纪英国渔业的研究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在各场重大战争的学术光环下对它的有限关注则显得较为黯淡。
莫里厄在书中对两国渔民在渔区、渔权等问题上的纷争进行了细致考察,并尝试从地方和国家的角度出发,重视挖掘其中值得关注的举措,探究双方应对过程中的“微观经验”,尤其是地方治理和实践发挥的作用。散布在海峡中的岛屿是双方争夺的“桥头堡”,狭长的水道不利于大型战舰的运动和藏匿,所以虽然法国素有直取英伦之心,但大规模海战却一般发生于“外缘”海域。因此,对18世纪英法渔业争端的考察,既是对此时两国关系的一种补充性理解,也让读者在宏大叙事之下得以放大历史的细节,并且明白,即便处在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下,战争依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从现实意义来看,这或对当今世界渔业问题的应对与解决有所启示。
二
对近代海洋国家来说,海疆象征着海上势力范围,是海洋政策存在和实施的基础。因此,不论是渔业安全抑或贸易安全,都要以英吉利海峡的安全为基础,确保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一直是英国在安全领域的重中之重(6)徐桑奕:《19世纪前英国海疆意识的嬗变及其历史逻辑考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54页。。有关英国对海峡享有的历史性权力,早在16世纪就已对此有所界定。当时,英国官方对海岸范围和归属作出了若干初步规定,宣告了王室对海岸的主权和管控,其中申明:“前滩……及所有岛屿(notonlytheforeshore……butevrypieceofland),无论水位高低(highandlowwatermarks)……涨潮或退潮(fluxandre-flux)……都是王室的领土。”(7)S.A.Moore,The History of the Foreshore and the Law Relating Thereto,London:Stevens and Haynes,1888,p.171.领海中蕴藏的丰富资源也受到了重视。1609年,詹姆斯一世发表公告,宣布从当年8月1日起,“任何外国人或凡不属本国公民者,不许在本国任何海岸或海域从事捕鱼活动”,除非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主要是针对荷兰在海峡的鲱鱼捕捞行动(8)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69页。。荷兰政府对英国试图否认荷兰捕鱼权的做法反应强烈,谴责英国这一公告侵犯了荷兰在英国沿海捕鱼的条约性权利。荷兰政府不承认英国宣称的其对广阔海域的渔业管辖权,但承认英国在从其海岸向外一定距离的海域内对渔业具有特殊权利,亦即,争端双方就沿海国对沿岸渔业享有特殊的权利这一点并无异议,但在距岸海域的宽度范围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9)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第69页。。故从总体上看,英国在其周边海域的权力诉求十分强硬,并有众多舰船在海峡周边巡逻护卫。
即便宣称对一切海洋资源都拥有不容置喙的权力,囿于有限的资源,政府也无法事必躬亲,此时,形成于各个地方的习惯和风俗就发挥了其作用。例如,墨角藻(10)拉丁学名为Fucus vesiculosus,当时布列塔尼人称goemon,诺曼底人称vraicq。参见Jacquin,C.,Le goemonier,Paris:Berger-Levrault,1980,p.11.(wrack)是一种生长在海边岩石上的海草类植物,可用作肥料或饲料,也用作肥皂等物品的制作,数百年来一直被英法及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的居民所拾取使用,而政府并不能对此多加干涉。对此有学者指出,条例、律令的实行仍要与当地的惯例和实践相结合(11)J.M.Neeson,“Gathering the Humid Harvest of the Deep”,in La Societe Guernesiaise:Report and Transactions 2009,Guemsey:La Societe Guernesiaise,2010,pp.521-538.;莫里厄亦认为,要将其中的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影响同时纳入考量(12)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187.。虽然像是一种后见之明,但也足见当时的政权意志并不能通达于国家所有地方。因而,地方特色即显性地开始自我表达。以根西岛(Guernsey)为例,在法条律令之外,对水域的开发利用都基于当地惯例的引导,因而较为有序。尽管在拾取海草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摩擦和争议,但在集体主义和互惠互助原则的规制下,岛民均能得到相应的收获,即便贫穷的人也可以或多或少有所入账(13)J.M.Neeson,“Gathering the Humid Harvest of the Deep”,pp.521-538.。这表明,在根西岛等地方,水域仍属当地居民所共有,由此产生的冲突反而较少。
在海疆和渔业资源的管控方面,法国也不遑多让。它于1681年颁布的《海事敕令》(OrdinanceofMarine)是对此前各类海事法令的集成和总结,也为其此后一个世纪的海洋政策奠定了基调(14)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185.。该海事条例分“船员与船舶”“港湾海岸停泊处所的管理”“海上捕捞”等章节,较为详细与系统。在其中有关海洋范围划分的表述中,“海岸”(seashore)的范围有所扩大,近似于现今所说的“前滨”(foreshore),在此范围内不得建造各类永久建筑或进行渔业活动(15)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185.。
莫里厄注意到,对海峡支配权的争夺,是英法数百年纷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渔业问题的根源也发轫于此。海峡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离开来,让英国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免于陆军的直接冲击,对英国保存有生力量、集中资源发展海事的总体战略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当时英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封锁(blockade)海峡以及布雷斯特(Brest)等法国港口(16)N.A.M.Rodger,“Naval Strateg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in Geoffrey Till ed.,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Thinking,London:Routledge,2006,pp.23-24.。另一个显著实例是海峡群岛。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它一直是英法之间龃龉的关键杠杆之一。它北距英国南部海岸约80海里,南临法国海岸,最近处不到12海里。正因如此,法国一直如鲠在喉,在历史上曾多次试图以武力夺取群岛。直到18世纪中后期,法国仍希望利用英国身陷北美战争的机会进行夺岛行动。1781年1月,法军尝试在泽西岛(Jersey)的圣·赫利尔(St.Helier)登陆,若能成功,法国就有可能继续增兵,泽西岛也会大概率因之沦陷。然而泽西岛民兵最终打退了法军,并将俘虏押解到朴茨茅斯受审(17)于文杰、詹墨奴:《英属海峡群岛的主权危机及其应对方式》,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第94页。,乔治三世特授其“皇家”称号,以嘉忠勇,也是为了昭彰海峡之“英国性”。此举更进一步提升了岛民对英国本已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连当时的法国军官都对他们的英勇和忠诚歆羡不已(18)于文杰、詹墨奴:《英属海峡群岛的主权危机及其应对方式》,第94页。。同时,这还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英国海洋政策的某些优越之处,官方和民间或以各种方式和渠道笼络和团结群岛居民,以至如它这样的“飞地”都愿意为之而战,也让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也无法轻举妄动。虽然在北美和大西洋上举步维艰,但在此时海峡仍基本处在英国权力的节制之下。
另一方面,18世纪英国的迅速崛起是诱发英法渔业纠纷的直接原因。“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以全新的姿态挑战欧洲头号强国路易十四法国的霸权,连续投入两场遏制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战争,即“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Spanish Succession),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当1740年前后欧洲大陆局势再度出现动荡之时,英国返回欧洲再次抵制复兴的法国称霸大陆的野心(19)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184页。。通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Austrian Succession)和“七年战争”,英国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稳定,还再度摧毁了法、西等国的海上力量,成为“欧洲之外的海上和陆上的主人”(20)[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册),薛力敏、琳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32页。。此外,作为两大国之间狭小的缓冲地带,海峡修长构造与地貌导致的渔区重叠交错,也是渔业争执的一个原因。
有历史学家总结道:“历史上,尽管双方都有一些在渔业方面和平共处的意愿,但官方的协定却从未达成……17世纪末,随着英国好战性的锋芒毕露,这类机制最终不复存在了。”(21)A.R.Mitchell,“The European Fishery in Early Modern History”,in E.E.Rich and C.H.Wilson 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82.18世纪的各场战争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渔业问题的发生和博弈模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法渔业间的联系较多,高层对话也随之增加;然而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各类协定遂无疾而终。18世纪中期开始,历经“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再到“北美战争”,英法始终处在针锋相对的状态,两国开始频繁抓捕和扣押对方渔民和渔船,国内利益群体的分歧也渐渐显露。然而,从整个18世纪来看,无论两国的邦交如何崩坏,海峡两岸港口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一直较为紧密,这是英法渔业争端的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
所以,英法之间并没有因争夺渔业资源而爆发规模巨大的决战,而是因局势和利益诉求的变迁展开不同层面的博弈。它们在其中所遵循的原则和坚持的底线,都与以往历史中形成的观念和惯例相关。因此,对渔业纠纷中各方行动及其背后逻辑的关注,比单纯研究纠纷本身更具意义。
三
在当时看来,历史上的古老权力申明都是较为苍白无力的(22)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186.。海上力量规模和行动力的限制使得英法都无法对海峡进行绝对控制,西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也令它们有着顾此失彼的顾虑。除却政权内部的原因外,政府的排他性政策也损害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乡绅、农民、渔民等群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自然不愿支持这些政策,反而热心于促成民间的共识。
(一)英法在地方层面的交涉互动与有限谅解
在英国社会的普遍思维中,渔业时常用来类比农业,船主用来类比农民,水手则类比农民的双手(23)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186.,足见渔业之不可或缺性。在和平时期,英国渔民对法国渔船在英海岸的捕捞活动尚且不满,遑论战争时期私掠船对渔船的清剿。统计显示,18世纪所有渔业纠纷事件的80%都发生在英国海岸附近,毕竟英国沿岸的鱼类资源要比法国丰富太多,以致于加莱、敦刻尔克等地的渔船都蜂拥而至。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渔船不受本国法令的约束,英法渔船遂在对方海域大肆捕捞,有时甚至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性捕捞方式。例如,18世纪20、30年代,法国使用疏浚设备,在某些海域开掘海床以便捕捞,严重破坏了水体环境;18世纪末,英国渔船也有样学样,在法国康卡勒海岸附近使用疏浚手段捕捞牡蛎,法方也只能给予谴责。
除却双方渔民之间难以避免的龃龉,地方层面的沟通与对话是更为引人注目的。事实上,虽然英法处于长期紧张的关系之中,但两国渔民之间却非自始至终剑拔弩张,在暗地使绊的同时,英法国内的一些港口和渔业团体都在尝试进行沟通与协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港口城镇之间的一些口头磋商结果还成为某些渔业协定的蓝本。1704年,法国沿海地区盛传英方正谋求渔业方面的和解,法国港市迪耶普(Dieppe)当局随即派遣海员,前往苏塞克斯(Sussex)等地谒见英国地方官员,打探信息是否属实。1708年,继与荷兰之间达成渔业捕捞方面的谅解后,法国又和英国签订了一份有关渔业活动范围的协定,其中表述道:“……在获得了英国方面的允诺后,法国船只可以在从敦刻尔克到巴约讷(Bayonne)的海域中自由渔猎;同时,法国的所有舰船船长、其他各类船只的船主,都不得突袭或劫掠在从奥克尼郡(Orkney)到英格兰南部--包括泽西和根西在内--的范围内进行渔业活动的英方船只。”(24)Archives du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Paris,CPA226,fos.67-67v.这一协定的订立离不开地方官员以及渔业相关人士的推动,历史学家指出,类似的停战或合作协议往往也最先出自于民间非正式共识或民意的传播(25)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15.,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相关从业者和地方官员也较为热衷于推进双边对话,可谓是对两国外交关系的一种补充。1710年,法国港市布洛涅(Boulogne)的商人和海员又奔赴英国开展进一步商讨,由是,英法民间的渔业协商也渐成一种惯例。直到1739年,一名法国渔民的渔网在多佛(Dover)海域失窃,他随后向就近的英国港口申诉,认为是英国人偷走了他的渔网,并要求英方妥善处理。此时,他所援引的依据仍是1708年的英法渔业协定(26)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19.。
18世纪中期,地方因素已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但迪耶普、布洛涅等城市和英国的直接交涉仍是渔业问题处理的重要途径。40、50年代,包括英国、法国、荷兰在内的一些国家之间有关渔业谅解和渔区划分等事宜的协商相继进行(27)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21.。而在北美战争之后,港口间的谈判更走向了系统化。莫里厄注意到,此时,即便还处于交战状态,双方的商谈人员也能受邀进入彼此国家,参与非正式的谈判(28)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22.。1778年11月,法国的一名私掠船主还释放了一位被其俘获的英渔船船长,此举登时获赞,一名法国的海事官员对此评论称:“……无论何时,贸易总是有用的;就算开战,贸易的稳定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29)Copy of Sartine to Mrs Lhermite and Michelon,owners of La Therese,24 November,1778,in Archives departementales du Nord,Lille,C4609,item 3.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协议和谅解大多数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且一般在战争结束后举行。同时,它们在表述和执行上仍然存在诸多欠缺,双方针对彼此渔船的敌对活动也没有完全停止。例如,这些协议都对渔民(fisherman)的保护做了规定,但对何谓“渔民”,以及渔船的规制和体量等问题并未清晰界定。同时,对攻击行为也缺少明令禁止和相应的惩戒手段,由此导致一些海盗和私掠者伪装成渔船并实施海上劫掠活动,海峡群岛的私掠船还借机向法国的诺曼底等地展开了走私贸易(30)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p.216-217.。这表明,渔业纠纷是国家安全和殖民地利益等尖锐问题的一个表征,英法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者的奔走虽然能部分缓释紧张局面,但根植于双方思想和政策中的敌对意识依然占据主流,特别是从“詹金斯之耳”(War of Jenkin’s Ear)开始,英国和法国、西班牙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并爆发,官方层面开始将此诉诸于武力,渔业领域的矛盾遂也随之激化。
(二)政权介入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战事的进行,“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介入使得对抗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这种态势也毫无意外地蔓延到渔业问题上。1760年,有法国人观察并记述到:“这些‘渔业条约’(fishery treaties)从上世纪末开始就逐渐消失了……英国人一边安全地捕鱼,一边习惯性地抓捕我国的渔民……这让我国不得不废止这些条约。”(31)R.Valin,Nonveau Commontaire sur L’ordonnance de la Marine,du mois d’aout 1681,Vol.2,Paris:Jerome Legier,1760,p.640.英法的海上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大规模的征兵和军费投入使得财政捉襟见肘,“私掠”制度由此重装上阵。从性质上看,这一时期的私掠船具有较为明显的“海盗”属性,特别是游弋在加勒比地区的私掠船;而在海峡附近,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本土的安全,拱卫港口。私掠船主要活动于海岸附近,伺机对敌国船只进行劫掠和打击;同时,海峡群岛的渔民和海员也发挥其地理优势,大力开展相关活动。海峡地区的水道较为狭窄,又常年受洋流、信风等影响,适宜体量较小的私掠船发挥其特点。当时有英国法条规定,私掠船可在“任何海域、港湾、港口和河流”(32)K.Von Martens,Essai Concernant les Armateurs,les Prises et sur tout les Reprises,Gttingen:J.C.Dieterich,1795,pp.64-65.中攻击敌人,意欲利用私掠船充塞官方舰船所无法企及的水域空间。其时,法国、西班牙等国也不遑多让,大量支持和授权私掠船活动,各国都在海峡展开军事和经济上的试探和制衡。40年代,一些商船船主还联名请愿,要求政府派军舰护航(33)J.B.Hattendorf,R.J.B.Knight,A.W.H.Pearsall,N.A.M.Rodger,and Geoffrey Till eds.,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London:Navy Records Society,1993,p.366.。1747年的一封官方书信中提到:“两或三艘来自布洛涅、迪耶普或者敦刻尔克的私掠船正潜伏在我们的海岸附近……这让我们多达60艘渔船不敢贸然出港……现在我们只需要一艘20门炮船或者军用单桅帆船就足够……”(34)J.B.Hattendorf and others eds.,British Naval Documents 1204-1960,p.379.可见渔船已成为当时私掠船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据统计,渔民成为双方战争俘虏的一大主要来源(35)A.Cabantous,Dix-mille marins face a l’Ocean,Paris:Publisud,1991,pp.161-206.。然而即便如此,渔民和私掠者之间的关系也并未十分敌对,因为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秘密合作,如走私活动和物资补给供应等(36)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p.217-218.。
在民间互动的同时,英国试图在法理上对此作出某些界定,其中一个举措是完善了其“捕获法”的表述和适用范围。作为一种国际惯例,捕获法早已实践了数个世纪,但英国法律界仍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晰表述。作为战争期间执行特殊管辖权的机构,英国海事法院创造出了欧洲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捕获法(37)肖崇俊:《英国海事法院的历史探析(1360-1873)》,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30-31页。;虽然并非为渔业领域特意设计,但在渔业争端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虽然所有捕获活动都是在君主指令下进行的,但是对于捕获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则是由海事法院做出的。因此,这些问题大多都需要在海事法院中得到解决。18世纪后期,在英国海事法院建立起判例汇编制度之后,关于捕获案件的判例就逐渐成为一部对其后判决具有约束力的捕获法。战争期间,国家经常颁布法令,禁止部分商品的交易。但是这些所谓的违禁品之中并非所有物品都如军火一样一目了然。例如,食品是否应当作为违禁品就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对此,英国法律界提出以食品目的港的性质作为判断标准,即如果这批食品的目的港是民用性质的,那么这批食品不能够被认为是违禁品,即使这个港口偶尔会有军舰停靠也不例外;如果目的港是军用性质的,那么这批食品就是违禁品,而无论它最终的用途如何(38)肖崇俊:《英国海事法院的历史探析(1360-1873)》,第31页。。18世纪中后期英法之间的海上冲突不断,于此,英方舰船就能够对法国渔船、商船等进行较为有效的排查,并对法国沿海各港口进行巡航监控,遏制其军需供应和渔业运行。
从1815年起,英国在海峡的渔业开始有所衰退。英国将此归咎于法国,认为是由于法国拖网船在海峡的作业,妨碍了英国的流网作业,从而造成英国渔业的不景气,并造成两国在渔业上的争端(39)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第69页。。1837年,英法遂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和谈判。经过两年的拉锯,两国于1839年签订了《确定和控制大不列巅和法国沿岸的牡蛎渔业和其他渔业专属权利范围公约》(ConventionforDefiningandRegulatingtheLimitsoftheExclusiveRightoftheOysterandOtherFisheryontheCoastsofGreatBritainandofFrance)。这一文件约定,以3海里为国家渔业管辖范围,但格兰维尼湾的牡蛎捕捞除外;3海里线以外的渔业资源属于两国共有。同时,该公约还对渔船标识、渔船的注册作了规定(40)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第69页;W.T.Burke,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s of Fisheries:UNCLOS 1982 and Beyo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至此,至少从形式上看,两国之间长期的渔业纠纷暂时告一段落。
可见,18世纪的英法渔业纠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联系和必然性。一方面,分处海峡两岸的英法在历史上都曾宣称对其周边海域的权力管控,领海控制权的排他性注定了双方之间日后的海事龃龉;另一方面,17世纪末英国的崛起不容许一个强大海洋邻国的存在,而法国也必然不愿坐视英国的扩张而无动于衷。因此,渔业纠纷是两国在18世纪权力争夺的一个方面和侧影。
结语
在宏观的叙事当中,英法之间的海洋竞争贯穿了整个18世纪的欧洲历史。对于这一问题,历史学家在其记述中,着重展现了两国将军事争端的边界推向世界各地,北美、加勒比、南亚等地都成为英法鏖战与拉锯的战场这一历史事实。由此,英法竞争的“世界意义”开始被不断渲染,而其中的“本土意义”则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相应的学术重视。有鉴于此,莫里厄的《海峡》一作,无疑是对后一问题研究的有力补充。在笔者看来,在海洋史的研究中,需关注海洋的“流动性”,作为水体的海洋,赋予了海洋人口、海洋社会、海洋交往等事物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在特定地区和时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对“边疆”的理解上,莫里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边疆”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它也是与另一国家相沟通与互动的“中心”,其中既可能有着激烈的冲突,亦能看到协商或斡旋的迹象。因此,“边疆”是考察国家对外关系和政策的重要场域。(41)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p.21-22.第二,莫里厄指出,当代史学研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的视角和语境中展开讨论,并将各个帝国作为界线分明的单位(units)进行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边疆”的空间属性。事实上,边疆或海疆都是面积广大的地区,不同民族杂居、交错于此,其历史实则是“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y),(42)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3.而并非像地图上划分地那样泾渭分明。第三,海域空间和跨国交往的历史值得进一步深挖。在莫里厄看来,一些生活在两国交界处的边疆子民,其身上的共同特性,甚至比他们各自的同胞还要更多。(43)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5.由此,他指出,以地方或地方性作为研究对象和视角,探究区域(regional)、国家(national)、国际(international)等因素的耦合作用,不失为一种见微知著的研究方略。(44)Renaud Morieux,The Channel,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