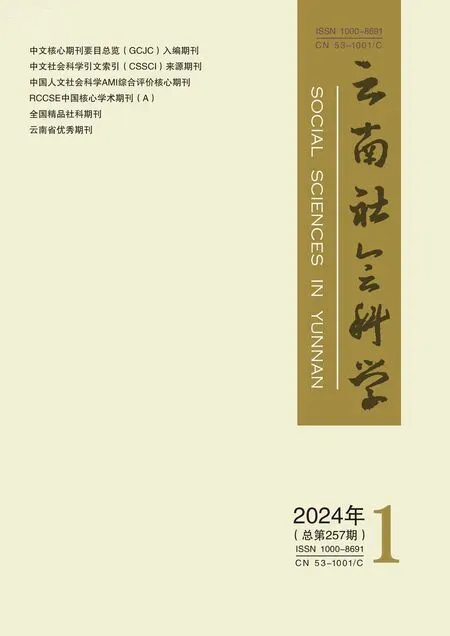清末筹议放垦蒙地及在察哈尔地区的放垦实践
吕文利 马周睿
一、引言
晚清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出现新境遇与新实践,以察哈尔为代表的蒙古地区的管理实践发生了巨大改变,岑春煊、贻谷等地方官员因地制宜,采取了务实的垦务政策,使得北部边疆开发呈现新态势,为边疆的进一步开发,积累了难得的历史经验。
清代前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主要是对人口、地域和资源的封禁。①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等:《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260—261 页;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 年第2 期。封禁政策体现清廷对蒙古地区的治理特点,它通过国家强制力限制蒙古各旗、蒙汉自由往来以贯彻“分而治之”的理念。19 世纪80 年代以来,这种防边政策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驻边各省将军、督抚、都统、大臣等纷纷要求清廷转变政策,如何开放蒙地也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讨论。光绪二十三年(1897)国子监司业黄思永向朝廷上奏开垦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的牧地。②《奏为遵旨查明内蒙古伊克昭等盟牧地与直录远不相接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24-0164-065,缩微号:04-01-24-029-0291。庚子之役后,清廷为纾解财政困境,再次将目光转向蒙古地区。光绪二十七年(1901),借清廷颁发“变法”上谕之机,张之洞、刘坤一等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将劝农兴垦、开发边疆等作为变法自强的重要内容③《“江楚会奏变法”第三折》,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4758—4761 页。,成为开放蒙地的先声。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向朝廷建议放垦蒙地,随后便正式派贻谷赴察哈尔、乌兰察布等处督办垦务。①《清德宗实录》卷490,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本,第58 册,第483 页。这次开垦蒙地的重点虽在“西垦”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但以察哈尔左右两翼为主的“东垦”区垦殖成效显著,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于清末蒙地放垦,以及清朝蒙古地区治理研究的成果颇多,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清末蒙地垦务活动的研究,主要梳理了察哈尔②邢亦尘:《清末察哈尔垦务探述》;王艳萍:《清末察哈尔八旗蒙地的放垦》,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年。、绥远③安斋库治:《清末绥远的开垦》,《满铁调查报告》1938 年第18 卷第12 号,载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63 年第6 辑;赵兵:《清末绥远城八旗牧厂放垦探述》,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等等。、伊克昭盟④王龙耿:《清末民初伊克昭盟的放垦》;李克仁:《浅析伊盟王公贵族对官垦的态度》,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乌兰察布盟⑤李克仁:《清代乌兰察布盟垦务初探》,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等处的垦务活动。二是对清代蒙古地区治理与放垦蒙地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清代蒙古地区的治理政策、管理制度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 年;赵云田:《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张永江:《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二元管理体制》,《清史研究》1998 年第2 期;等等。,清代蒙地政策的变化⑦乌云格日勒:《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1 期;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赵毅:《清代蒙地政策的阶段性演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1 期;等等。以及晚清时期边疆秩序重建下全面放垦蒙地与移民实边、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关系⑧珠飒:《18—20 世纪初东部内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田宓:《村落、蒙旗与国家:清代以来内蒙古土默特的乡村社会变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年第5 期;等等。。三是对内蒙古垦务进行专题研究,主要关注垦务活动引发的政区沿革变化⑨王玉海:《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年;乌兰:《从察哈尔放垦章程看察哈尔垦务》,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哈斯巴根:《清代口外王公牧厂探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 期;等等。,社会经济发展变迁⑩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以准噶尔旗为中心》,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衣保中、张立伟:《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史学集刊》2011 年第5 期;张力仁:《清代伊克昭盟南部蒙汉经济共同体的建构与解散——以“禁留地”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2018 年第3 期;珠飒、佟双喜:《“走西口”与晋蒙地区社会变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2 期;等等。以及垦务大臣相关活动⑪代表性论文有张世明:《清末贻谷参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年第4 期;吴春梅:《贻谷与内蒙古垦务》,《民族研究》2000 年第4 期;张文平:《岑春煊与清末内蒙古垦务》,《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 年第1 期等。等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论述开垦背景、过程、影响等具体内容,较少阐发清末内蒙古垦务活动对于巩固大一统格局以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意义。随着档案的进一步整理和公布,加之丰厚的先行研究成果,本文以清末察哈尔垦务为切入点,在《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一辑)、《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⑫参见赵全兵、朝克主编:《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以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所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嵌入式互动理论⑬嵌入式互动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多种力量合力而成的结果,也是所有民众互动的实践综合。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族群、集团、部落、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嵌入式互动是以战争、和亲、通婚、贸易、和平、互助等为表达手段的一种横向的历史互动。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才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得以形成,也是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关键。”参见吕文利:《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 年。,尝试对清末蒙地放垦活动作进一步探究。
二、由“防边”到“边防”:清末蒙地放垦的起因
清廷的封禁政策旨在提防蒙古力量壮大,然而承平日久、人口繁衍,无论是内地还是蒙古地区都出现了地狭人稠的矛盾,生计的压力使得封禁政策“半遮半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呈现“禁者自禁”“垦者自垦”的局面。①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682 页。19 世纪中叶以来,这一“祖宗旧法”越来越难以应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迫使清廷实行“摊”款制度以分担巨额赔款,各省分摊的数额是甲午战争以前的六倍。当时,仅山西一省所分摊的赔款银每年就多达百万两之多。②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76 页。有鉴于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向清廷上《筹议开垦蒙地奏折》《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潘属而弭隐患折》,以纾解“东挪西垫、寅支卯粮”的困窘。山西省因与察哈尔、土默特及鄂尔多斯等地接壤,康熙年间就已出现民众罔顾禁令,移居蒙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一些大臣早有开放蒙禁之议,如张之洞《详筹边计折》、胡聘之《奏为筹议开垦晋边蒙古荒地情形事》等。而岑春煊的奏议则从开辟利源的角度指出取消蒙禁、放垦蒙地的意义,由此促使清廷不得不重新思考对蒙政策,开启了清末全面放垦蒙地的序幕。
1880 年,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强调了蒙古地区防务的重要性,他认为“蒙古强则我之候遮也,蒙古弱则彼之鱼肉也”③《详筹边计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366—384 页。。要有效遏制俄人乘机阑入、“径叩边墙”的威胁,使蒙古富强起来才是关键措施,为此他建议实行屯田、牧政等政策。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山西巡抚胡聘之多次派人到河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其后在奏折中阐述了在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蒙旗地方实行招民放垦的原因、条件、具体办法以及有利之处。胡聘之开篇便指出当时时势艰难,开源节流如开矿经商、裁撤兵勇等途径“效难骤睹……其上裨国计,下益民生,程工速而兴利溥,莫若广开蒙地一事,较有把握而无流弊”。为此他又详细分析放垦蒙地有四大好处:第一,加强边备,“今既议开蒙地,拟请兼置兵屯,……既可慰蒙盟以安耕作,并可供征调以应缓急,……棋布星罗,声势联络,以实边备”;第二,体恤蒙古,“况蒙古贫弱至斯已极,若不早为设法,势将无以自存。今既议租以瞻其身,复置兵以卫其地,为蒙民策安全”;第三,增加财政,“近来时事艰棘,国用浩繁,……若能全行开垦,除议给蒙租及一切费用外,约岁可得官租二三百万两,……帑藏空虚之际,岁增钜款,以裨度支”;第四,筹粮备荒,“今既重开蒙地,粮食自必充牣,……择地建仓,广为储积,以备灾荒”。最后他还提出了设局、筹费、定租、驻兵等具体方法,在三湖湾(笔者注:山湖湾)地方设立屯政局,派员总司其事,办公费用的筹划则仿照奉天、吉林之例酌提租银,地租未征收前从归绥道押荒银内提动款项。地租的多少视土地之贫瘠而定,所收租银“除应给蒙租外,其余概作官租,分三成,做屯兵津贴、办公、仓储之用”④《奏为筹议开垦晋边蒙古荒地事》(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01-1019-026,缩微号:04-01-01-153-1936。,胡聘之的设想对岑春煊全面开垦的思想与计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充分吸收前人奏议的基础上,岑春煊的第一道奏折解释了开垦蒙地的重要性,第二道奏折则主要列举一些具体开垦蒙地的方法。第一折中岑春煊开头引用历年督抚的奏议,“同治九年,前库伦大臣张廷岳有‘蒙兵不足恃’之奏;光绪六年,前司经局洗马张之洞有‘练蒙兵’之奏;十一年,查办土默特争地大臣绍祺有‘蒙古有租乃能练兵’之奏;十二年,前伊犁领队大臣长庚有‘缠金屯田’之奏”⑤《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3 页。。认为四人的奏议从不同层面阐述了解决蒙疆危机的办法,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正因“蒙兵不足恃”,才有“练蒙兵”之议,“有租乃能练兵”落实到地便是屯田、收租,岑春煊的建议也围绕着这四个维度展开。岑春煊认为近年“俄人之势日益盛强,蒙古之众日就贫弱”,蒙古早已无法发挥当年“屏藩朔漠”的作用。增强边防力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练兵,但边疆官员“皆知蒙兵宜练而苦于无饷,蒙长皆欲自练其兵而苦于无力。是则欲练蒙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练费,非开蒙地不可”,蒙地田土丰饶,乌拉特、鄂尔多斯两部靠近河流,“灌溉之利,甲于天下”,因而“备之之策,莫如开蒙部之地为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练蒙部之兵”①《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3—4 页。,并进一步指出蒙地开垦有“四利”:
其一,利在实边,蒙地开禁,广筑屯堡,则可“斥堠城戍,直接甘疆,戍事虽兴,必无瑕隙”;其二,利在强兵,“蒙地开则地租所出取供练饷,租入有赢,兼购军火、器械一新,胆气自壮。”如此便可“膏腴以垦,壁垒以新,汉纳其租,蒙练其伍”;其三,利在密防,漠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三城是阻挡俄国的咽喉要地,“蒙地开则置营乌盟,声援近接三城,有警克期可赴。晋防以固,边镇不危”;其四,利在靖盗,“蒙地开则建驿通途,驻官务梳剔宄、安辑善良,散勇之内有愿耕者,编为兵屯,使受约束,牌甲之设,一仿内地莠良不杂,萑蒲自靖”。②《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4 页。此四利充分体现了岑春煊强兵实边的目的。
岑春煊第二折更是指明开垦蒙地的必要性,他首先指出,“现在时局艰难,度支竭蹶,兵费赔款之巨,实为历来所为未有。”其次,岑春煊又举实例说明开垦蒙地对于国家的益处,“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将来开垦以后,烟户日多,釐税自旺,无形之利,何可胜言,是利国也”。③《奏为筹议晋省兴利必以开垦蒙地为先恭折再陈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22-0065-116,缩微号:04-01-22-011-0157。最后,他认为保证蒙古屯垦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是“不急在征收官租,而急在开浚地利,不必夺蒙部之产,而贵联蒙部之心。利在蒙、利在民,即利在国也”④《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5 页。。岑春煊的两折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后,兵部左侍郎贻谷不久便被任命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前赴蒙地主持全面放垦活动。
清末蒙地放垦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岑春煊的奏折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结果。禁止内地民众随意进入蒙古地区是清廷封禁政策一项基本内容,促使清廷下定决心抛弃传统的“蒙禁”政策,其背后存在多重原因,可以说民间涌入蒙地开垦人数不断增多和清廷将禁耕之地范围不断缩小这两条线并不是简单地单向决定,而是相互影响,在各种因素、条件相互交织下同时进行。全面放垦蒙地从表面来看,移民实边似乎是其主要目的,实质上却反映了一些时局的深刻变化。
其一,蒙古边防地位的转变。“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⑤《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6 册,第700 页。是蒙古在清代边疆防卫格局中地位的体现。与历代相比,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特点是通过应用“硬治理”“软治理”两种办法,“以最小的治理成本达到了‘大一统’的治理效能”⑥参见吕文利:《硬治理:清朝盟旗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施效能》,《河北学刊》2022 年第1 期。。对此康熙皇帝曾自豪地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⑦《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5 册,第677 页。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古代经常发生的“北患”问题至清代结束,蒙古诸部充分发挥“屏藩朔漠”、稳定北部边疆的作用。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清廷在蒙古地区的诸多政策越来越难以应对新情况。当年蒙古骑兵“环长城万里,隐伏百万强弩,以捍卫边陲”⑧(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上·蒙旗篇》,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388 页。的局面不复存在。满—蒙军事联盟作为清朝统治力量的核心,逐渐丧失原有的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士人阶层,他们通过平息国内的起事,又凭借洋务运动在清朝统治阶层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改变了清朝以满蒙贵族为主的统治结构,间接影响到清廷对蒙古地区的边防部署。
其二,治边思想的转变。晚清朝廷试图通过放垦蒙地,增强边防力量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蒙疆危机,体现了清朝由“防边”到“边防”思想的转变。对此清末荣升有详细的阐释,他认为:“今一变锁国时代为交通时代,故昔者对蒙藏所行之政策,遂不可复行于今日。盖锁国之时代,患在藩属,谋国家者,必重防边。防边云者,防边人之或内侵也。交通之时代,患在敌国,谋国家者,必重边防。边防云者,用边人以御外侮也。”①荣升:《经营蒙藏以保存中国论(上)》,《大同报》(东京)第七号,南京图书馆收藏,1908 年6 月28 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载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年,第59 页。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和封禁政策,实际上是以“边防”思想为指导通过,保障蒙古王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以维护“大一统”。所谓蒙地开垦“利蒙、利民、利国”②《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5 页。,核心是让蒙古地区再次发挥捍卫北方疆土的屏藩“长城”的作用,恢复清中期“资游牧为奇兵,列穹庐为坚壁也”③(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上·蒙旗篇》,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388 页。的局面,实质上仍彰显了清廷维护“大一统”格局的努力。
三、民为邦本:全面开垦蒙地的施政表达与实践
作为垦务政策的主政者,贻谷在接到朝廷任命的旨意后,与岑春煊进行反复会商,制订了放垦办法的大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循途而进之办法。“乌拉特各旗之山湖湾、缠金、乌拉河一带,有可垦之地约二十一段,水旱各地约二十万顷,……数百里间,极易开渠,足资浸溉,是以历来称为沃壤”,贻谷想从临近山西省的乌拉特各旗入手,逐渐扩大放垦范围;其二,经费所出之办法。“此次开垦西盟蒙地,地广事繁,……所有一切局用、薪水、工食等项费用,不赀刻下晋省库款万拙,既未敢多议开支,亦未便过从简约。经费一项,拟仿照奉天办荒成案,于荒价外另征二成,以资办公”;其三,押荒岁租之办法。“蒙旗放地,向无定价,并不计顷数,……现拟将水旱各地各分上、中两等,价亦因之,……押荒所入以一半归之公家,一半归之蒙部,……至常年地租,自应照奉天成案,归蒙部征收,今用款繁多,度支竭蹶,各蒙旗历受厚恩,理应报效”④《贻谷等奏为会筹堪办蒙旗垦务大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10—11 页。。
贻谷的这套办法实际上延续了胡聘之先前提出放垦方案的思路,只是将放垦范围、重点、目标以及筹费的用途进一步具体化、清晰化了。内蒙古西部的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以及乌兰察布盟等广大地区都纳入放垦范围,可谓是“经画三千余里,操纵二十余旗”⑤《贻谷为会奏办理垦务拟将设立各局处分委员司书差人等额数暨薪工车马费等项开支书目章程缮单饬部立案一折奉朱批抄奏分行户部等处查照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131—133 页。。其中,重点放垦区域为尚未开垦的乌、伊两盟十三旗的牧地。已有一定开垦基础的察哈尔、土默特各旗则以清理旧垦为主。由国家和蒙旗平分放垦蒙地所得押荒银⑥“押荒”又称“荒价银”。清末在内蒙古等地实行放垦政策后,历代垦务机构向承垦佃户(多为外地汉人农民)征收的垦荒押金,也称“押荒租银”。,并让蒙旗上缴报效银是这个大纲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缓解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案。
由于乌、伊两盟盟长的强烈抵制,贻谷只好“暂缓会商西盟垦务,趁便赴察哈尔,先行筹办右翼旗清垦事宜”⑦赵全兵、朝克主编:《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1 页。,此时蒙地全面放垦活动的工作重心便转移到了察哈尔地区。
察哈尔、土默特属内属蒙古地区,实行总管旗制度,康熙年间部分内地汉民以“雁行人”的方式进入此地从事农业生产,雍正朝以后,清廷便公开实行招民放垦。⑧“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相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参见《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7 册,第137 页。贻谷认为当时察哈尔地区“向来私放私开,从未能行官垦”,“即如察哈尔左右翼已垦地亩甚多,其缴押荒、报升科者,不过十之一二”⑨(清)贻谷:《垦务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47 页。,所以才制定“清旧垦、招新垦、恤蒙艰、定限期、筹经费、预储备”①《贻谷等奏为筹拟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务办法量为变通以清弊窦而浚利源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5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6—9 页。等基本的垦务步骤。所谓“清垦”主要是指停止私垦,将长期以来私招、私垦的土地重新勘丈、清理,目的在于把私垦变为官垦,用新设立的官办垦务机构取代地商,以获取押荒银和升科银②所谓“升科”,是指无主荒地晋升为科税田地。通过升科,国家获得田赋,而农户获得拥有土地的凭证。升科时,农户会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即升科银,一般要低于当时地价。充裕国库。
察哈尔地区的王公牧厂是为了满足清朝皇室、军队的需要而设,自乾隆中叶以后,有不少牧地陆续私自开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贻谷上奏王公牧厂地也应一同开垦,而王公牧厂土地关系复杂,界址不清,据档案载:“王公马厂,与察哈尔各旗地界毗连交错,牵混最多,辨认不易。蒙古山名、地名,重复隐奥,翻译猝难辨析。往往东西易位,壕堑无凭。度其地,在恩赏之初,不过括指地段,本无里数可稽。久之,各便私图遂至任意开拓,漫无限制。”③《贻谷为附奏王公马厂请令一律报销开垦一片奉到朱批恭录谕旨分行事(附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8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22—23 页。贻谷据此决定从丈量地亩、确定界址入手,下令各旗总管,将旗中所有苏木分别绘制详细地图,并标注已垦、未垦土地之大致面积,上报垦务局等候勘丈。④《贻谷札饬察哈尔八旗将所管界内王公马厂若干坐落处所已否开垦查明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8 册,第24 页。在基本了解各旗开垦情况下,“无论为台、为群,凡系已垦之地,一律划清丈明,饬即照章押荒、升科,……至于地已全开,余荒无几,则据蒙员之陈请,不得已而为之移群、并群,……惟此外该群台所有草地,关系牧养滋生之计,亟应严为限制”⑤《奏为察左毗连群台私垦地亩遵案一律勘明丈放分清界地各安垦牧而泯争端折》(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4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344 页。,王公牧厂仍旧可以向官府领取每亩四厘的私租之利,变化之一是新开垦的地亩在押荒二钱外,新增收办公银一钱,六分充做官局经费,四分作蒙旗协同办垦公费。⑥《贻谷为附奏王公马厂请令一律报销开垦一片奉到朱批恭录谕旨分行事(附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8 册,第22—23 页。自此,察哈尔左右两翼十二旗群,除了官兵随缺地、公共牧场、群地及少量的台庙地、牧丁养赠地和学堂地等外,其余的察哈尔蒙地一律接受垦务局的勘丈,在全部放垦的同时招民承领。
在设置具体机构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上任后,先后在归化城设立了“垦务大臣行辕”及行辕文案处、收支处等办事机构。为提高行政效率,贻谷改组丰宁押荒局为督办丰宁垦务局目的是专理察哈尔右翼垦务,不久又将丰宁垦务局分为丰镇、宁远垦务两个分局,以解决镶红、镶蓝二旗“兼顾难周”的问题。⑦《贻谷附片具陈所有丰宁垦务分办情形》(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汇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765 页。察哈尔左翼四旗的垦务则由在张家口设立察哈尔左翼垦务总局负责办理,并兼管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的垦务事宜。⑧《贻谷咨行察哈尔左翼四旗蒙地拟另设垦务局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3 册,第4 页。
察哈尔八旗蒙地的放垦、转租向来由地商承办,他们穿插于官方、地主与佃户三者之间,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与各方利益进行互动联系。衙门、旗署借由他们的活动,减少行政成本,故而清廷对此类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地商和户总持默认态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贻谷奏请设立由官商集资合办的东路垦务公司,该公司的性质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垦务公司,“分设张家口、丰镇两处,凡地属察哈尔左翼者,归张家口公司办理;属右翼者归丰镇公司办理。”⑨《张家口东路垦务公司申报开用关防日期事》(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0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14 页。该机构的设立意在办垦集资,排除地商、户总势力,将地商私得的部分收归国有。与之前的押荒局等机构相比,垦务公司通过发行股本的方式进行合法的融资活动,既缓解清朝各地政府启动资金不足、经费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又能减轻官府、地方民众的负担。贻谷还设立西路垦务公司,负责承领转租乌、伊两盟部分土地。总之,准备放垦的蒙旗土地都要经过垦务局勘丈,由公司照章缴价承领,或放垦或招典,归公司自主,这样一方面保证放垦程序正当规范,另一方面引导地方民间资本流入官府控制的领域,使之不至于出现地商私设地局与国争利的现象。①赵全兵、朝克主编:《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213 页。
在察哈尔,无论清垦还是放垦,都进行得较为顺利。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对察哈尔八旗官私牧厂的清理和丈放工作基本结束,其中右翼四旗放垦牧地约24800 余顷,左翼四旗放垦牧地20000 余顷。②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第80 页。在耕地数增加的同时,人口数也在大量增加,据哈斯巴根估计,仅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清末民初的移民人口就达10—15 万人。③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以准噶尔旗为中心》,第85 页。
“东垦就竣,西垦畅兴”,察哈尔地区放垦只是全面开垦蒙地的第一步,西部地区的开垦一直是计划之中的重点。由于当地王公贵族多持反对意见,清廷并未急于推进放垦活动,一直在徐图缓进,从容布置,正如贻谷所说:“幸仰蒙朝廷假以岁时,宽其文法,俾得从容筹布,逐渐经营,四载于兹,始有今日。惟念兴利之举,在开源亦在节流,尤须有与时变通之事。”④《贻谷为具奏东垦就竣西垦畅兴谨将裁减员司暨并添伊盟各旗局所情形一折奉朱批札饬西盟垦务总局遵照事(附奏、清单)》(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176—178 页。可知清廷放垦蒙地,并不完全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仅仅是为了开辟利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贻谷的两则告示更加体现了清廷治理蒙疆的远谋。
第一,“修教齐政”的策略。察哈尔八旗制不同于西部乌、伊两盟扎萨克旗,乌、伊两盟各扎萨克旗的王公对土地有相当的支配权,奏放地⑤由蒙旗扎萨克王公上奏清廷并获得批准后招民放垦的土地。、私垦地⑥即王公贵族及官员等未经清廷许可,私租私放的土地。这两类土地收入所得都归于当地的王公、扎萨克。贻谷推行放垦活动无疑阻断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所以才发生“伊乌两盟十三旗,昔既屡议而未行,更并作兼营之匪易。当筹办之始,一则百端纠遶,一则相与阻挠,几有窘于清釐,穷于操纵者”⑦《贻谷为具奏东垦就竣西垦畅兴谨将裁减员司暨并添伊盟各旗局所情形一折奉朱批札饬西盟垦务总局遵照事(附奏、清单)》(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176—178 页。的现象。贻谷并未气馁,仍发布告示,悉心劝谕两盟王公、扎萨克接受开垦蒙地的新政策。他首先指出清廷对乌、伊两盟十三个扎萨克旗的优惠政策:“矧在乌、伊两盟,地为封建之地,前已示将所征押荒归尔蒙旗一半,其常年地租银,则尽数全归蒙旗,是乌、伊两盟蒙古应得押荒岁租,较之察哈尔蒙古所得款项,极为优厚。此系奏奉谕旨允行之案,决无更易,本大臣自当钦遵办理,以示朝廷优待蒙藩之恩意”⑧《贻谷示谕乌伊两盟押荒岁租归蒙旗一半租银全归蒙旗由》(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汇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7 页。。考虑到乌、伊两盟土地并非如内地郡县那般是朝廷征粮地,清廷在充分尊重蒙古王公权利的前提下,以优厚的押荒、岁租作为交换条件,促使各旗王公渐渐改变态度,自愿报垦,充分彰显清朝修教齐政的统治智慧。
第二,“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康熙皇帝对此有一段经典阐发:“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⑨《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四月丙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5 册,第677—678 页。清代蒙古政策历经重大变化,仍充分延续了修德安民,体恤民情的施政理念。贻谷特别从“蒙古生计”角度出发强调清廷开垦蒙地的目标:“此次所办垦务,必期于蒙古生计有益,决不使蒙古进项有损……尔等当知本大臣为尔蒙旗计,胜于尔蒙旗自为计。将来两盟养生有资,练兵有饷,端在此举。”①《贻谷示谕乌伊两盟押荒岁租归蒙旗一半租银全归蒙旗由》(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汇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第27 页。在实际放垦过程中,虽有清廷派兵镇压蒙旗群众抗垦斗争的现象,但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并非其初衷。清末察哈尔地区的土地几乎垦辟殆尽,但“未经勘丈、未报升科,涣散隐匿”的现象仍然存在。对内地垦户而言,一方面“领地于商人,无官府文书之凭执,视若倘来不同世业,荒熟任天,耕耘不力”,另一方面“旗员衙蠹,互串需索、予夺不常、科派百出”。②《筹议丰宁押荒办法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622 页。就蒙旗而言,“客民与蒙民平分花利”,实则“霸犁强割、此壤彼争、逋欠逃亡”③《筹议丰宁押荒办法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 辑,第625 页。。为使民众“呈交押荒,即可领照,承为世业”④《筹议丰宁押荒办法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 辑,第624 页。,清廷才在察哈尔地区重新勘测丈量土地。这种“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也体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进程中,早在施行之初,清廷曾特意批示:“惟兴办屯田,固所以裕税课而重边防,亦须无碍蒙民生计。”⑤《清德宗实录》卷406,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癸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本,第57 册,第303—304 页。在《办理蒙旗垦务示谕》中贻谷更声明此次放垦“并非欲侵取蒙旗之地利、收回地商之产,……实以益蒙部,非以损蒙部,实以安边民,非以扰边民,苦心苦口,无非欲拯厥艰穷,共登丰乐”⑥《贻谷办理蒙旗垦务示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2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114 页。。
需要说明的是清廷并不是一味“体恤仁爱”,而是恩威相济,宽严得当。在上述办理示谕中贻谷也强调了当地各盟长、扎萨克如“能格外出力,定奏请特恩格外优奖”,倘若“仍以有碍游牧为由,阻挠开垦,本大臣纵不忍重拂蒙情,亦未便听其违抗”。至于“匪类棍徒,捏造谣言,以一经官办田即归官为词,煽惑地户”⑦《贻谷办理蒙旗垦务示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2 册,第114 页。,则更加严惩不贷。此后清廷还给贻谷理藩院尚书衔和绥远城将军一职,赋予他直辖乌、伊两盟各旗的权力⑧《贻谷奏为得加理藩院尚书衔叩谢天恩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47 页;《兵部为奉上谕绥远将军着贻谷补授咨行新授绥远城将军钦遵事(附、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1 辑,第1 册,第115 页。,以期顺利推进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垦务活动。据此可知,其后由强制推行垦务所引发的“势将激变”局面,不应完全归结为清廷放垦政策本身,以上两则史料表明,清廷全面开垦蒙地政策自有一定施政逻辑,政策表达与实践存在一定张力,不能因为实践的偏差就完全否定政策本身合理性。
四、嵌入式互动:蒙地放垦形成的新局面
清末蒙地放垦对今天内蒙古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放垦蒙地不仅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而且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笔者认为清末放垦蒙地标志着清廷治理边疆模式的转型,推动了北部边疆地区形成嵌入式互动发展局面,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一)清廷治理边疆模式的转型
蒙地放垦是清末“筹蒙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招民开垦为先导,通过遍设州县,施行一体化,清廷加强了对蒙地的统治。自清中叶以降,蒙禁政策已开始松弛,朝廷对内地大批民众进入蒙地垦种定居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末派遣贻谷督办蒙旗垦务,宣告“封禁蒙地”政策的终止。封禁政策是为了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使内地农民不与其争利,然而随着内地流向边疆的民人日益增多,当时,沿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等都建议清朝进行筹蒙改制,即改变蒙古旧有的盟旗制度,废除扎萨克旗制,通过增设州县加强与内地的一体化趋势。蒙古各部的改制问题已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焦点之一,具有代表性的是岑春煊的奏折。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向清廷上奏《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折》,从统筹西北全局的角度,着重阐述了蒙古各部的改制问题,他首先指出西北边疆地区“财日以匮,民日以困,治日以麻,兵日以弱,即是晏然无事,已不可支,何况界约屡更,事变日迫,不为补救,必悔后时。”①四川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921—926 页。岑春煊认为清廷对西北边疆各部的因俗施治,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变通”,不可墨守成规。“不必徒侈改制之名,而当先尽振兴之实;不必大耗度支之力,而当先谋生殖之图”②四川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921—926 页。。受此徐图渐进、务实避虚思想的影响,清末的放垦活动从土地关系、制度架构、垦务机构人员构成等方面入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蒙旗土地管理权限的一元化。各旗放垦的土地由私垦变为官垦,按一定比例缴纳田赋,既改变了以往蒙旗土地不征收赋税的惯例,也进一步减小了内蒙古地区王公贵族的权力,缩减了蒙旗的管辖范围。从前清政府在漠南蒙古地区实施的二元管理体制下的两种权力运行机制已渐渐无法兼容③张永江:《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二元管理体制》,《清史研究》1998 年第2 期。,清末蒙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了清朝蒙疆治理模式的转型。
(二)经济多元化趋势加强
清末蒙地放垦活动的发展,改变了该地区较为单一的经济形态,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察哈尔地区为例,作为清廷的直辖区域,早在康熙年间官方招垦和民间私垦就已交叉进行。内地民众迫于生计压力不断涌入该地,蒙古王公上层为了个人利益私招、私垦,一内一外两股力量相结合,使得察哈尔的农垦区逐渐扩大,牧场日渐缩小。至18 世纪中末叶,察哈尔南部已经变成半农半牧区。清末放垦蒙地的活动实质上是既成事实下的历史延续。虽然清廷在推行蒙旗垦务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放垦”已垦熟地的现象。时任署理练兵处军政司副使姚锡光经考察后说:“闻东省之放牧场,西边之放河套,皆取民间已经开垦成熟之地,勒收押荒银两,实未放出荒地一亩。”④姚锡光:《实边条议》,《筹蒙刍议》卷上,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 年,第38 页。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影响察哈尔地区土地开垦的意义,首先,农业的开垦无疑对原本脆弱的游牧经济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次,解决了当地牧民的粮食需求问题,也为大量的内地贫民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最后,突破了清代以来该地区较为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局面,农业区和半农业区日益扩大,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粮、货、钱、当四大商业体系,⑤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31 页。促使当时整个蒙古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三)民族关系嵌入式互动发展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即便是历史上政权强制推行民族隔离政策,也难以阻断底层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趋势,遑论作为清朝“大一统”格局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地区。“大一统”国家为民众自发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晚清蒙垦活动推动蒙、汉等各族人民之间形成嵌入式互动的关系。康熙年间“卓索图盟的许多蒙古族,就向汉族农民学会了种地,汉族农民也向蒙古族学到了放牧和制作奶制品的本领”⑥况浩林:《评说清代内蒙古地区垦殖的得失》,《民族研究》1985 年第1 期。。在清末垦务发展的过程中,贻谷还在绥远地区开设学堂,“广开蒙智”⑦《奏为绥远城改建中学堂及添设蒙养学堂蒙小学堂情形事》(光绪三十二年),《附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38-0194-072,缩微号:04-01-38-009-0297。,随后内蒙古各地也纷纷开始兴办学堂⑧《奏为喀喇沁蒙旗建设师范学堂宣解讲堂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38-0195-024,缩微号:04-01-38-009-0366。,渐渐出现了“蒙汉相融”的局面,这些都有利于蒙、汉等各族人民之间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发展。
内地人口增长与土地狭窄的矛盾在晚清时期越来越突出,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由内地往边疆的人口迁移趋势,清廷在蒙地全面推行放垦,既顺应了这种趋势,也满足了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需要。内地移民的大量迁入,促使蒙古地区演变成为蒙、汉、满、回等多民族聚居区,由少数民族占多数转变为汉族占多数,民族结构逐渐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①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第162 页。。以绥远地区为例,依据乾隆年间统计,绥远地区蒙古族人口(包括乌伊两盟、归化土默特旗)共289500 人,如加上察哈尔八旗在绥境内的人口,当时绥远境内蒙古族人口当在30万左右。②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第252—253 页。到清末,绥远地区蒙古族人口略有下降,总数约为25 万人(见右表),而汉族人口已达101 万人。③参见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2 期。
据学者统计,至19 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总人口约为215 万,其中汉族100 万。又根据1912 年公布的宣统年间民政部调查数目,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7 万,汉族人口约为155 万。100 年间,汉族人口增加了55 万。⑤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344 页。总体而言,随着清末蒙地的逐步开垦,蒙古族人口数量有所下降,汉族人口则主要因蒙荒土地的不断开垦而增加,这些新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间嵌入式互动发展。

表 清末绥远地区蒙古族人口统计表④本表依据《修正民国元年内务部汇造宣统年间民政部调查户口统计表》改制。由于绥远所辖两盟未列报,各盟旗户口按照普通民户列入,所以表格中“全部”这一行数据的统计并不是下列四地数据相加而得,而表示绥远地区的整体人口数据。《中国经济年鉴》第3 章《人口》,1935 年1 月再版,C15 页。另参见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第254 页。
五、结语
汪炳明认为晚清放垦蒙地的活动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权宜之计,直到1910 年清廷全面解除“蒙禁”,各边省督抚、将军奏请开放未经招垦的各蒙旗时,仍以“开浚利源”“辟地利”为具体目标。⑥汪炳明:《是“放垦蒙地”还是“移民实边”》,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189—197 页。这也导致了在推行垦务的过程中,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不仅将原有蒙旗的“私租”地纳入州县管理之下,征收押荒银,而且还普遍存在放垦“熟地”的现象,察哈尔地区尤为明显。相关史料文献中的记述多关注放垦地亩数、征收的荒银等信息,有关于人口户籍的情况、承领垦种土地之类的记载较少,正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言:“凡历年所开垦,或已及全旗,或量为设治。但经理者第以筹款为主义,……所谓筹备边荒之策,茫乎无闻也。”⑦《会同三省巡抚桩奏三省内蒙垦务情形并预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3-6738-075,缩微号:511-257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革职查办贻谷的上谕中,清廷又明确指出:“朝廷放垦蒙地,意在开荒备边,并非攘地图利,……既须振兴垦务,尤须深恤蒙艰,以示朝廷抚绥落部之至意。”⑧《清德宗实录》卷589,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本,第59 册,第789—790 页。
如何理解清廷这一政策表达与实践情况的偏离,笔者认为之所以没有一定程度上实现“深恤蒙艰”“实边固圉”的治理效能,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度支竭蹶”的现实困难,清廷想要通过放垦蒙地来缓解庚子赔款带来的财政压力,这才不顾蒙古王公的反对,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请,开始放垦蒙地。岑春煊也在其奏文中以实在的物质利益说服清朝统治者,他明确提出:“光绪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恩泽奏放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⑨《奏为筹议晋省兴利必以开垦蒙地为先恭折再陈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22-0065-116,缩微号:04-01-22-011-0157。姚锡光也认为昭乌达、哲里木二盟尚可开垦数十万顷地,“此荒若以光绪三十二年办理,扎萨克图荒价预算共可得银千万余两”①《锡光奏请拣大员办内蒙垦务折》,《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卷1,于逢春、厉声主编,姜维恭、刘立强分册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第9 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26—27 页。。可见,清廷最初放垦蒙地的初衷固然是“实边固圉”,但更直接的现实目的显然是以筹款为主,弥补极度匮乏的财政收入。难怪徐世昌感叹“一经清丈放价,便无余事,甚或欺弱蒙民,侵吞款项;绳丈则多寡不均,放荒则肥硗任意,缠讼互控、轇轕纷纭,莫可究诘,而于垦务之兴衰,蒙情之向背,地势之险夷,从未考究”②《会同三省巡抚桩奏三省内蒙垦务情形并预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3-6738-075,缩微号:511-2576。。但是学界也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放垦政策中蕴含“蒙古生计在租不在牧”的思想,它表明此时的“放垦政策的提出不再着眼于私垦,而开始更深入思考和解决蒙古社会发展中农牧经济的主体地位问题。它针对蒙地农业化过程里清政府最担心的‘蒙古生计’问题作出回答,正面驳斥了蒙古王公以有碍‘蒙古生计’的理由抵制放垦的做法。它在阐明蒙地发展农业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清代后期传统畜牧业经济在蒙古社会的主体经济地位”③侯甬坚主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305 页。。清末蒙古地区经济发展的这一变化也有利于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一体化。
北部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治理是整个清代边疆嵌入式互动的典型代表。高翔认为:“明清时期,中原和边疆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出现了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统一不但成为政治的需要,而且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清朝的大统一,实际上是数千年中国社会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④高翔:《在历史的深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55—56 页。“大一统”作为历朝历代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动力。⑤吕文利:《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以清代“大一统”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23 年第5 期。清末的蒙地放垦活动既体现了清廷维护“大一统”局面的努力,也是中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一种体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一方面是二者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的自发凝聚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综合发展的需要。盟旗制度是清前期“因俗而治”的产物,同时也是蒙古各部归附清朝的政治基础。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护清朝广阔的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无法应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北部边疆蒙地放垦活动虽然出现了急功近利、顾此失彼的行为,但清廷仍能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不失时宜地开发边疆,这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于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形成不可分割的水乳交融关系,增强大一统中国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