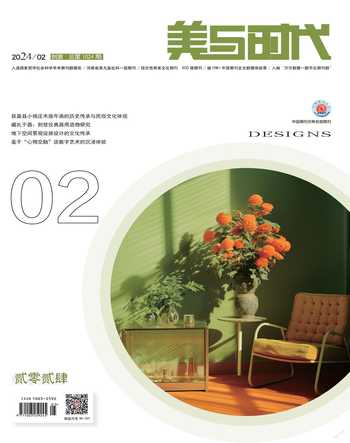“具身”与空间: 传统手工造纸传承与复兴研究



摘 要:“具身”理论主张身体与环境互动引发知觉感受,传递认知信息,从而产生记忆、情绪、感情等认知。身体、认知与环境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完整运作系统,身体是基本前提,是发生认知的关键基础。夹江的手工造纸技艺就是一种“具身化”的技艺,这种技艺的传承不靠书籍纸本的明晰知识和记录,而是依赖于口口相传的身体实践经验,更多地偏向于一种手工艺人默会性的技艺。本文将“具身”理论引入对传统手工艺复兴与传统民居的保护研究,从空间角度探索一条基于“具身”理论的路径,遵循身体、认知与环境的内在有机系统,从传统手工艺的“具身性”延续到身体与空间的学说,保护与活化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民居建筑,推动传统造纸技艺的多元化发展,拓宽夹江造纸产业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具身;具身设计;传统手工艺;传统民居;手工造纸
一、“具身”的空间解读
(一)“具身”
“具身(embodied)”一词来源于哲学领域,并且广泛涉及到心理学、现象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方向,后来逐渐被用于空间与身体的缺失研究中。“具身”理论主张身体与环境互动触发知觉感受,转化为认知信息,从而产生记忆、情绪、感情等认知。身体、认知与环境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完整系统,身体是基本前提,是发生认知的关键基础,身体与环境互动产生认知,且身体的局限因素和条件会影响认知的生成。
“身体是所有表达的基础。”[1]梅洛-庞蒂所提出的具身现象学是关于身体的觉知、身体的意识的“现象学”。他主张从身体向度审视空间,并且身体是人对空间理解的基础,一切人对于空间的认知都基于身体。身体本身的空间性是人们感知外部空间的原始条件,但从认知层面来看,人认知外部世界的方式又受到人类对自我身体认知的限制,自我身体的空间向度奠基了对外在世界的认知。
将“具身”理论引入对空间场所的研究,从空间体验者的认知与身体向度审视空间的合理性。由于人对空间理解的身体性,身体带来的直观体验和认知经验都会影响人对建筑的感受,从而在空间的设计上能更加地契合使用群体的需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中,“身体性”是极为重要的核心特质,中西方对“身体”与空间的认知虽存在差异,但都肯定了“身体”的重要性,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建筑拟合,从身体的感知影响认知的产生,从传统手工艺的“具身性”解读空间,从而起到活化手工艺生产空间、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的作用。
(二)“具身设计”
“具身设计(Embodied Design)”是一种基于身体的生命特性以建筑中人的精神影响为出发点的建筑设计方法[2]。现代建筑的的超尺度性、单一性及抽象性极大程度上远离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建筑被称为“冰冷的居住机器”,单一地追求视觉效果,而忽略了空间所需的文化性、实用性以及尺度性。“具身设计”以身体为介质研究人与空间的互动,通过身体的特性推动人与建筑更加融合、多样的互动,通过身体的感受传递认知,从而形成身体、认知与环境的良性互動。传统的建筑设计中的场地、功能、材质、结构等问题,在“具身设计”中极大地受到人类的感知、认知和行为的身体性的影响,从而在设计过程中生成新的方向和解决方式。
“身体”在空间的研究中越来越成为重要议题,身体的物理特征直接影响人与空间的互动,其互动在身体与空间中体现为身体与建筑在感知、认知和行为三个层次上的关联。建筑的精神内核来源于人类身体与空间的互动,身体是感知建筑主体的向度,人类通过身体特性触碰建筑的空间范围,从而生成建筑感知,身体与空间的互动产生认知,身体的局限性也会限制对空间的认知,这些感知和认知又反作用影响建筑空间中人类的行为。如此在感知、认知和行为三个层次上的互动都遵循身体的尺度、感受以及意象,能更有效的反馈于建筑空间与人类的互动以及人类的行为。
二、“具身”与传统手工艺
(一)凝结的技艺:夹江手工造纸
夹江县隶属于四川省乐山市,坐落于四川省西南部,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丰厚。夹江县富有“千年纸乡”的美誉,当地手工造纸的历史起源还未有准确时间论断,但根据已有的记载,夹江手工造纸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明末清初,夹江的手工竹纸已经初具规模,在清朝发展最为鼎盛,因生产的竹纸质地上乘,被送入宫中成为“贡纸”。抗战时期,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寓居夹江县石堰村,他在夹江和纸农一起研究改良夹江纸,研发出质量更加优质的“大千书画纸”,闻名全国。夹江竹纸技艺精湛,工序复杂,在2006年就已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为珍贵的文化财产。夹江的竹纸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模式,因此生产周期长、产量小且人力资源耗费极大。虽然机器生产已经是时代的宿命,但手工造纸的制作技艺仍然无法被机器完全替代。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定会带来民居建筑的差异化,夹江竹纸的主要生产场所就是纸农们的家,夹江的民居建筑与普遍的川西民居有所不同,在历史的发展中,为适应当地的竹纸生产,当地的建筑极具地域性特色(如图1)。夹江造纸的生产与生活紧密相连,整体民居排布为沿溪修建,更加便于抄纸生产。建筑以木构结构为主,墙体由特定的泥土、稻草以及石灰修建而成,由于用于晒纸,墙体表面光滑细腻,洁白无瑕,纸农们会将抄好的纸铺在墙体上阴干,为避免太阳直射,屋檐普遍出挑较长,能达到1~2米,同时也能防止雨水的滴溅。与此同时,家家户户都会在民居附近单独修建用于生产的小作坊,面积较小,设备简陋,但都能适应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如图2)。
(二)传统手工艺的“具身性”
在中国广袤的历史中,产生了大量的传统手工技艺,这些技艺跨越时间,在传承者中共享,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然而在传承的过程中,数以万计宝贵的手工技艺在历史中失传。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是一项极具地域性与记忆化的“技艺”,这种技艺的传承不靠书籍纸本的明晰知识和记录,而是存在于言传身教的身体的实操经验,偏向于一种手工艺人默会的、经验性的、情景依赖性的技艺[3]。传统手工艺的技艺者们在生产过程中依赖于身体千百次的实践经验,不必完全依照着规定好的生产条件和要求,这些技艺都深深地植根于生产者的肢体和血液里,是身体本身与认知相互作用下进行的生产活动。“默会”知识是一种隐性知识,其存在于身体的感悟与自然而然的行为中,来源于环境中长期的行为实践,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式有共通之处。
夹江的造纸技艺传承以家族血脉为路径进行技术再生产,传承者们从小耳濡目染,经过数年的言传身教和实践经验,才得以继承到这一复杂的技艺。夹江造纸工序与《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古法造纸术一脉相传,皆由七十二道工序组成,主要由“制料”与“抄纸”构成,但纸本上的记载并不能完全如说明书一般指导手工竹纸的生产。德国学者雅各布·伊弗斯对夹江手工造纸技艺有大量研究,他提出夹江造纸技艺是一种“具身”的技艺,“造纸行业的技术是具身化的”。造纸的技艺对身体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且造纸的过程中造纸匠人只需通过听觉、嗅觉等感觉就可以判断生产是否有效,在长年累月的生产中生成了一种直觉上的反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造纸匠人在造纸生产的千百次反复机械式运动中产生了对技艺的认知,手即是他们生产时的“尺”,生产不依赖于纸本的教程标准和明确的定性,而是依靠手的体会,从而形成了一种“默会的”知识(如图3、图4)。
(三)生产空间的具身认知
环境是“具身”理论系统中重要的三个构成要素之一,身体通过感知环境从而传递认知。具身设计在建筑基于身体的理论学说中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以人类的身体性的空间感受为视角,探讨身体、行为与建筑的关系。环境是承载身体感知、传递认知的空间基础。身体与建筑三维世界内存在的三维物质,身体在建筑中的感受来源于自身个体对边界的认知,对于建筑的认同感来源于建筑特性是否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对建筑空间最直接的感受是通过尺度、方位、质感来实现的,这些最基础的感受由于人理解空间的差异化,会转变为情绪、记忆等认知。对传统手工艺的生产空间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生产时所需的空间范围、操作程序,以及制作需求。工序的不同直接导致生产空间的差异,以生产需求为导向衍生出高屋檐、低矮墙、高烟囱或是光洁墙面等特殊空间。生产时的情景又赋予场所生产的意义,生产空间不能独立于生产活动存在。
三、传统手工艺的“具身性”活化
(一)“居”以载道:生产性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
传统民居及其聚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最直接地反映出不同的阶段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及经济体制、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状态,是历经风雨的活历史。由于我国地大物博,纵横跨度广阔且地势地貌差异较大,中国的传统民居在细微末节上呈现出多样的地域差异性,也因此能更大程度地获得建筑形式的自由度,有更丰富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质。
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开发相得益彰,开发以保护为基础,保护是核心行动,开发是方式和手段,开发为保护提供经济保障,两者相互作用使得传统民居获得新生,更大限度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夹江的传统民居特殊的风貌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生产的需要,当地的民居建筑不仅有川西传统民居建筑的穿斗结构、斜屋顶、薄封檐,还有适应生产需要的晒纸墙、宽屋檐等形态,这些独特的建筑形态和内部结构都反映了数百年来当地造纸技艺的发展和文化的延续。当地保存良好的传统民居应定期维护,保留其生活状态,对保存状况较差的民居进行修复重建,在修复和重建过程中尽量保持原始风貌,保留夹江造纸民居的木构结构和内部形态,复兴当地特有的晒纸墙工序,呈现出它原汁原味的本质特征(如图5)。
由于夹江传统民居的特殊性,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不仅要保护民居建筑本身,还要关注到夹江传统民居特有的生活习性和历史肌理。夹江的传统建筑由于当地手工造纸技艺的独特性与地域性,建筑空间生产与生活紧密相连,像这样的生产性民居的保护开发应当以恢复生产时的生活状态为基础,鼓励村民恢复手工造纸的家庭作坊式生产。生产性的传统民居空间保护应激活其生产时的历史场景,让空间重新获得手工造纸技艺文化延续其中的生产状态,由此实现活化夹江造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如图6)。
夹江传统民居是夹江造纸技艺的活历史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经济和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物质与人文资源。只有动态与静态两者结合,建筑的空间保护与生活状态恢复齐头并进,从人文和物质两条路径双管齐下,夹江传统民居才能够继承下来,并且得到永续发展。当承载身体与认知发生的环境被激活,能更有效地反作用于身体感知与认知,使夹江竹纸的生产民居得到有效保护与适度开发,从而实现夹江传统造纸工艺的复兴。
(二)以纸为媒:传统造纸技艺的多元发展
造纸术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并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对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都影响深远,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夹江的造纸技艺高超,产出来的宣纸品质优良,在清朝一度成为“贡纸”,在迈入现代社会之际,却逐渐荒废,被机器生产的造纸工厂所替代。夹江的造纸工艺独特,就地取材,以竹为原料,工序复杂,是极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珍贵的文化和技艺应得到延续与传承。
1.重视造纸工艺保护与创新
首先,重视夹江手工造纸的文化价值,加强对夹江手工造纸技艺的研究,兼顾物质与非物质的双重保护。大力鼓励纸农们恢复生产,传承手工造纸技艺,出台相关政策来鼓励和引导当地纸农生产,吸引青壮年生产力回流。在传承和利用方面,防止文化断层与现代化背离,兼顾造纸技艺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发展,重视创新的重要性,灵活地运用各种可以推动它永续发展的方式,鼓励技艺互换与创新,使手工造纸技艺不断地推陈出新,适应时代发展。与此同时,以纸业的发展带动随之产生的民俗活动与文化的发展,如夹江年画和竹麻号子等。随着国民对非物质遗产与传统文化的逐步重视,只有充足的手工技艺与创新的文化创意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通过相互交流與合作,形成具有相当强的文化共性与产业互补性的造纸产业集群。这种集群效应有助于促进手工造纸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实现纸品创新,从而形成夹江的特色支柱产业(如图7、图8)。
2.推动“产学研”模式多元合作
扩大夹江造纸业的影响受众人群,与教育资源展开“产学研”多元合作的模式,产教融合,通过高等教育对传统造纸工艺进行传承与创新。利用四川地区的高校资源,开办夹江手工造纸产学研合作基地,将夹江的造纸技艺带入课堂,在高校内组织造纸文化体验与交流活动,传授造纸技艺。如此既可以在年轻的一代中扩大夹江造纸的知名度,同时又为夹江造纸寻求了新的发展方向,带动手工造纸工艺人才的培养。在这样的模式下,使学生们更加了解夹江的造纸工艺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夹江造纸工艺的创新与研发,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夹江造纸工艺得到延续与弘扬。
3.促进造纸工艺与新兴产业融合
顺应时代潮流,促进造纸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夹江造纸宣传的新模式,提高社会文化认知度;将夹江造纸工艺融入现代生活物品,创新非遗传承方式,提升存续能力;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提供非遗造纸工艺体验,开拓生存空间。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促进夹江造纸与“互联网+”模式的融合,结合本地特色文化与民俗打造独特的夹江文创产品,可以实现从手工技艺品到文化产品的转变,赋予其更高的价值体现,强化人们对传统手工艺保护的观念。
四、结语
传统手工艺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一直以来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夹江古法手工造纸是当地地域文化的凝聚和展现,是夹江文化的内核,并且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复兴,本文从空间角度探索一条基于“具身”理论的路径,遵循身体、认知与环境的内在有机系统,从传统手工艺的“具身性”延续到身体与空间的学说,致力于保护与活化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民居建筑,推动传统造纸技艺的多元化发展,拓宽夹江造纸产业的发展思路,以实现传统手工艺的永续发展与延续。
参考文献:
[1]燕燕.梅洛—庞蒂具身性现象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2]李若星.试论具身设计[D].北京:清华大学,2014.
[3]雅各布·伊弗斯,胡冬雯,张洁.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的技术定位[J].民族学刊,2012(2):1-10,91.
作者简介:蒲晶晶,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