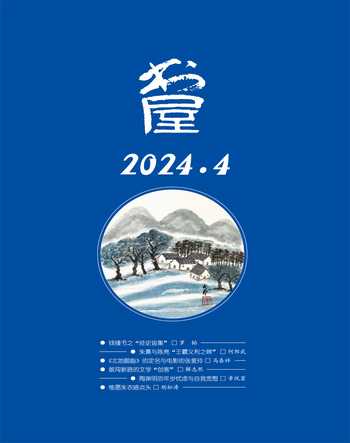“星期标准书”与周其勋
邝启漳
畅销书是指一个时期内非常受欢迎的书,即英语里的bestsellers,由出版社或报刊社推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这个词来源于美国,而最具权威性的好书推荐当属《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一旦上了《纽约时报》的榜单,下一步很可能就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普利策奖,而普利策奖之后则往往是诺贝尔奖的荣衔了。例如赛珍珠,其作品《大地》1931年问世,同年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次年(1932)获普利策奖,六年之后的1938年就摘得诺奖的桂冠,可见《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可以说是获诺奖的初阶或敲门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一份类似《纽约时报》的好书推荐榜,那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归功于两个人:该馆最为重要的掌舵人张元济和张后来网罗到的总经理王云五。张元济,浙江海盐人,是一位兼具深厚传统教育与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他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两年,戊戌变法后,因支持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于是,他南下来到上海,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他从著名的南洋公学辞职到一个小小的印刷所,开始了出版生涯,然而当时几乎无人理解他的决定。但是,人生的正确选择不仅让他的人生放出耀眼的光芒,也使这小小的印刷所从此蒸蒸日上,成为中国顶尖的出版机构。彼时商务印书馆刚成立六年,四位创办人都是排字工人,文化程度有限,主要做印刷业务,也在尝试向出版转型。张元济1901年投身商务之始就对创始人夏瑞芳说,要做出版就要有自己的编译所。于是1903年,他出任该馆编译所所长,此后历任经理、监理、董事长直至逝世,艰苦创业,历尽艰辛,殚精竭虑,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活动,使商务印书馆实力迅速壮大,最终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重镇。
为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还有王云五,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具远见卓识的大出版家,“有远见卓识,也有襟怀抱负;擅长科学管理,也有力排众议的魄力”。如果说张元济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饱学之士,王云五则是出身贩夫走卒之流而自学成才之人。王云五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在上海出生,只受过五年私塾教育便辍学,其父将他送到五金店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英语。十七岁时进入上海的同文馆修习英文等课程。十八岁时担任同文馆教生,并广泛阅读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名著。十九岁时受聘至中国新公学,担任英文教员。二十一岁时购得英文《大英百科全书》,以三年时间将全书三十五巨册阅览一遍,后来又修完土木工程及物理数学与机械等各种课程;先后加入两所美国的函授学校,获得许多高等数学、物理知识,并取得美国法学士预备资格;二十五岁时,受聘到国民大学讲授政治学、英美法学概论等课,又通德语、法语,《纽约时报》报道他为“活的百科全书”。1921年,经胡适推荐,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任总经理。王云五主理商务印书馆期间,陆续出版了《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万有文库》以及张元济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各类丛书、各种词典以及百科全书,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对中国的知识传播起到重要作用。须知,要出版这些大部头的书籍,主事者除了需要有相当眼光、组织能力,更得具备执行的魄力和勇气。这些书籍不仅在当时风行,今天仍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同时,王云五亦以科学方法改革商务印书馆,大力推行各种编辑计划,延揽专家主持编译所各部业务,聘请馆外特约编辑,开展各式各样的促销增量的活动。经过这样的改革,一时间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业务扶摇直上。“星期标准书”就是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期间所推出的一种书籍营销模式。从1935年10月开始,商务印书馆创立以“名人荐书”为手段,每个星期都向读者推荐一本新书的营销模式。这堪称中国出版界的创举,标志着“名人荐书”商业化的尝试之始。向读者大众荐书的名人,当然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如蔡元培、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冯友兰、马寅初、潘光旦等,可以说,当时文化、学术、教育界有几分影响的人物,几乎都参与了“星期标准书”的评选工作。在这些名人的推动下,“星期标准书”在当时的畅销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营销模式推出不久,由周其勋领衔翻译的《英国小说发展史》就有幸成为“星期标准书”之一。当时由哪位名人推荐已不可考,不过也有线索可循。荐书者在甄选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书的质量、内容以及读者反馈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从而推选出最优秀的作品。究竟是哪位呢?周其勋在《英国小说发展史》初版译序上写道:“译稿有几章曾经梁实秋、朱光潜、方光焘诸先生指正。”这三位都是英美文学名家,他们通读了译稿,对照了英语原著,自然就了解译者在信、雅、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功力,因而我估计,荐书者很可能出自这三位。他们通读了译稿,流利通畅而且忠实原文的译文使他们赞叹,所以从译文质量考虑,他们也推介了此书;他们又对照了原著,原著“提要钩玄,讨论精密,是一部权威的著作,因而是研究英国小说的人所不可少的参考书”,荐书者从内容考虑也看中了此书。
《英国小说发展史》问世以后,学界好评不断,一年之内就加印了三次。至于读者的反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发表在1936年《是非公论》第七期上署名“罗正晫”的长篇书评。罗正晫即罗皑岚,湖南湘潭人,1922年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曾任南开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湖南大学教授,既是一位有名的外国文学教授,也是享誉国内的小说作家,他作此书评时应是在南开大学任上。书评一开始就指出了翻譯这部学术著作的重大意义。他说:“国立编译馆最近出版的《英国小说发展史》是值得注意的一本书。原著者Cross先生对英国小说有很深的研究,是权威的学者,这部著作更是研究英国小说史的人必读的一部书,国内的大学如清华等已采用它做课本。编译馆选定了这部书来翻译,是极有眼光的。”接着,书评者赞扬了译文的质量:“译笔是非常忠实而简洁的,虽因译者不同,前后文气间有不一律的毛病,但无害于全书整个的‘信和‘达。”末了,最为书评者所称道的,也是我们作为周先生的学生最佩服的,就是书后的注释和索引。对于注释,书评作者说:“译者于每章后另注释至八九十条之多,都是很吃力的工作,便利初学,良非浅鲜。这是我们应向译者致敬意的地方。”对于索引,书评作者也说:“卷末的附录三,英美小说之中文译本书目,也是译者很辛勤的工作之一。原书索引,另按译本的页数注出,尤便翻阅检查。”罗正晫的书评并非过誉,这部体现了周先生学术功力的译著自问世以来不断再版。就我所知,除了1936年的初版,还有成都1945年2月商务印书馆版、1945年12月重庆国立编译馆版,1949年后海峡两岸也都时有重印。2007年左右,此书还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因为它一直被该校列入中外文学比较史的参考文献,由此可见这部译著影响之深远。
罗正晫的书评在赞扬《英国小说发展史》及其译者的同时,还不忘寄语国立编译馆当局:“一国的文化如果不是专靠飞机大炮来建筑的话,我希望国立编译馆当局继续这种有远大眼光的工作,它的影响,不是目前一点看得见的小小成就或失败,它的功效是写在我们文化史上未来的每一页上。”国立编译馆自然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据其《馆务汇录》第九期载:“又本馆出版之《战时经济学》及《我之奋斗》两书,经杨端六、罗家伦两先生(推荐)分别选入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内发行云。”这两本书无疑都与时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的周其勋有关:前者是经周校阅并力促出版的,后者则是由周领衔的团队奉命翻译的。
徐宗士译的《战时经济学》是国立编译馆继《英国小说发展史》后的第二本出版物。国立编译馆馆刊民国廿四年(1935)5月1日第一期载:“二周(周其勋、周骏章)及李君(李未农)合译Cross氏《英国小说发展史》业已葳事,正在补译附录并校阅已成之稿,大约五月底可全部告竣。”同期又载:“本馆出版之书,自书籍目录印行以后,最近续出者为四种;一为徐宗士译《战时经济学》……”由此可见该馆对此书的重视。而译者徐宗士在该书的序中则说:“(本书)复承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童冠贤先生,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周其勋先生……为之校阅,多所指正,合并志谢。”由此也可见,周其勋曾参与其事。该书甫一出版即受到杨端六先生的青睐。杨端六,湖南长沙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赴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28年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民政府军委会审计厅厅长、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杨先生推荐此书当然有其现实的考虑和形势的需求。
1936年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外侮日亟,战云密布,战机的轰鸣笼罩在南京的上空,市内人心浮动,民众在做逃难的准备,报纸上是一连串“国难当头”的报道,中日必有一战已成人们的共识。大战在即,身为军委会审计厅厅长的杨端六先生自然对战时的经济布局和举措深感关切,迫切想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战时经济学》一书会进入他的视野。果然,战争一爆发,国民政府便依照书中所载的战时经济学理论,实行“战时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于军委会。全国军队,凡在抗战军队序列的官兵都到“军委会”领饷;政府各部门以及全国大专以上学校的教职员也比照军官军衔在“军委会”支薪。周其勋先生那时是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领少将工资;杨端六先生则领中将工资。
罗家伦推荐《我之奋斗》当然也是考虑到此书的现实意义。罗家伦,浙江绍兴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等成立“新潮社”;五四运动中,起草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1920年秋,罗家伦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我之奋斗》是希特勒的传记。二战之前,希特勒还没有显露出世界公敌的真面目,德国由一战以来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负债累累的窘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骤然崛起,重新跻身欧洲列强,其军备实力更居欧洲之首,中国一些知识精英如朱家骅、钱端升等大力鼓吹“以德为师”,尤其在军备武器方面,以抗衡步步进逼的日本。朱家骅介绍德国陆军上校马克斯·鲍尔到上海与国民政府要员会晤,提出了中国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计划,大力洽购德造枪械以装备中国若干个陆军师。1926—1944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都经朱家骅之手,小到钢盔,大到飞机,大量的德制装备运到中国,一些研究部门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不到十年内,政府在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德械陆军,为日后的抗日战争打下了基础。因之,潮流下的国内舆论,甚至当局都渴望知道,希特勒究竟有什么能耐,能让一战战败的国家复兴强盛。据说,此书也是朱家骅直接让周其勋翻译的。朱家骅之所以委托周其勋,一来是周的德文和英文均有很高的造诣,二来是周深得朱的信任,朱(时任教育部部长)曾有意让周做他的秘书,因周的婉拒而作罢,后来秘书之职由顾颉刚先生担任。
但是,我们需要严肃指出的是,《我之奋斗》其实是一部烂书,无论是观点主张、逻辑论证、语言风格,都相当糟糕。该书主张纳粹主义,而希特勒却靠这本书赚得盆满钵满。1925年,《我之奋斗》首版一万册,被抢购一空,每本十二马克,按当时的生活成本计,买这书的钱可买三十二公斤的面包;到希特勒1933年上台前,该书已经销售二十二万套,每三百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主动购买了这本书;希特勒上台后,《我之奋斗》成了五千万德国人几乎人手一本的书籍。依靠版税收入,希特勒在慕尼黑郊外用情妇爱娃的名义购置了二十多套房产。这样一本超级枯燥、晦涩难懂的德国政治书籍竟然越过重洋,受到当时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推崇,现在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检索国立编译馆从1935年5月1日起到1937年7月1日的各期《馆务汇录》,能看到这些“星期标准书”一版再版的消息,如第一期,最近续出者有四种,“一为徐宗士译《战時经济学》一种”;第五期,本馆出版之书籍有四种”为本馆所译之希特勒《我之奋斗》”;第十三期,本馆最近出版之书有“《英国小说发展史》”,“四版之书有希特勒《我之奋斗》一种”;第廿四期“再版者有《英国小说发展史》一种”。接连不断的再版消息足以说明这些“星期标准书”在当时畅销的程度。另外,检索国立编译馆当时出版的书,其版权页上都如《英语当代四小说家》一样列出以下信息:
译述者 国立编译馆编译 李未农
章绍烈 蒋石洲
校阅者 中央大学英文系主任 范存忠
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 周其勋
出版者 国立编译馆
发行人 王云五
印刷所 商务印书馆
发行所 商务印书馆
这种把译者和校阅者的身份名衔一并列出的做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是为了表示负责,还是为了表明译文的权威性,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很可能是想说明,能列入“星期标准书”者,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