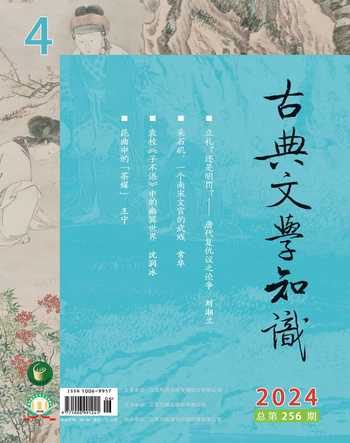情辞共生
李世磊?宋展云
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与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共朝京师,不久之后,任城王暴薨。曹丕即位以来,严密监视宗室藩王,划定诸侯活动范围,诸侯动辄得咎,以至于“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猜疑与恐惧笼罩于兄弟之间;又因七月离别之时,曹丕又要求曹植、曹彪异路而归,前有丧亲之痛,后遭离别之苦,曹植感慨万千,愤然成篇。历代评论家对此篇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朱绪曾曰“语极混融”(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引),南朝梁的《昭明文选》、沈德潜《古诗源》、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等历代重要的古诗选本都选录了这首诗。那么,这首诗歌在艺术上究竟有何魅力,能让历代的选本、评论家对其如此关注?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首诗的情辞关系中所体现的建安文学的特点来观察这首诗歌。
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曾总结曹植等人的文学特点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情辞相称是其文学创作的特点。这句话表明了,建安文学的情与文(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赠白马王彪》中,作者所传达的抑郁不平、哀切悲痛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受文辞的影响极大。因此,从沈约情辞相称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赠白马王彪》一诗,我们会发现,诗歌情感表达的需要来自沉重压抑的现实,其表达方式则是通过文辞的错落安排呈现,而文辞的错落有致则又增添了情感的跌宕不平,在曹植高妙的实际创作中,其文辞与情感实现了共生。
诗作全文如下:
谒帝承明庐,逝將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细读这首作品,玩味其文辞,其情感寄托亦可见乎其中矣!
首先,声节的错落,造成了情感的跌宕。其情绪之起伏,在韵脚之平仄转移,或上或去,或平或入,即陆机《文赋》所言:“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声节的交替使用,好像色彩的交相辉映,使人悦神悦志。当然,这里所指的是自然音节。全诗共分为七章,第一、二、三章用平声韵,想象了自己告别后所看到的山川景物,对曹丕不顾兄弟之亲的残忍进行了暗讽,仿佛湖中之平波流水,虽偶有波澜,而终为平静,故这三章读起来语气较为平缓,显示了情感的悠长缅邈,此三章的每句第三字,有提挈全句的作用,是情感的起伏点,喜用仄声,而仄声易传达情感的激切,则又表明了表面的平静之下还翻涌着情绪的波涛。第四章用入声韵,入声字语调急速,一般用于情感激烈之处,将前处对景物的描写集束在此处,作为情感的迸发点。在经历了前三章平铺与起伏后,情感在此处终因自然的感发而慷慨阐发,“极”“侧”“匿”“翼”“食”“息”,语气急促,情感激烈,此处,作者还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以动物的活动来铺写自己内心情感的哀伤,略显含蓄,但入声韵的使用又是情感激烈的体现,在一张一弛的安排中,文辞很好地展现了作者的哀切,又颇显节制。第五、六、七章又恢复平声韵,此处,作者重念天道人生,将思绪投射至整个宇宙人生,在思索宇宙人生中,作者意识到个体的渺小与现实的荒谬,又念及王弟的早逝,情绪趋向沉重,语调哀痛,声韵的选择与人的情绪相应。在这七章中,韵脚由平而仄,再由仄而平,情绪亦由起初的缓和悠长而偶有起伏,到情感的急促哀切,再转为沉重的哀悼与苦楚,可以说,韵脚平仄的交替配合了情感的转变,使我们在阅读中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情感的转换。
其次,虚词的使用亦对作者情感的抒发多有帮助。清代刘淇《助字辨略·序》认为,虚词乃文章性情之所在。这是从理解古文的角度来说的。但虚词对诗歌性情的表达亦多有帮助,甚至可化板滞为流畅。在《赠白马王彪》中,曹植多用“莫”“不”“必”“何”等虚词,在错落的使用中,增强了诗歌的情感。我们可以尝试将诗中的虚词分为两类:一类为否定性的虚词,“莫”“不”等;另一类则为非否定性虚词,“何”“其”等。否定性的虚词,是作者强烈情绪的展现,如“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心情苦悲触动了我的神情,请把这件事情放在一旁,“莫”要再说了。这是承接上文之语,对爱弟一去不再,而人世短促难猜的无限感慨,情转哀痛。又如:“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不”,否定之意,希望之渺茫,愿望之难成,一一由此字而显露,情绪更为哀伤,既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又是对痛失亲人的追念。而非否定性虚词则使情绪转向悠长沉重。以第七章为例,“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何”,当为“一何”之省,表程度,苦悲辛劳多么令人焦虑愁思,天命真可疑,此为首句,上承第六章末句反问的激切,而代之以情绪的绵长哀重。又如“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此句已是第七章的结尾句了,“其”,商量恳请之语,大王还请多珍爱身体,一起享受年老之乐吧!此已丧失了前几章语气激烈哀切的光彩,转为对现实无奈后的痛苦的接受,又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总的来说,这些虚词增添了诗句的情感色彩,时而哀切激烈,时而平和悠长,虚词的频繁使用与交替,使得本为平淡的句子有了情感的变化。在虚词的切换中,我们随着作者情绪的起伏流动,而更易把握情感的爆发点。
再者,句式的变化,也造成了情感的一波三折。诗歌的情感不仅体现在声节、虚词,还与诗歌的句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感叹句为情感强烈之体现,而疑问句(反问、设问等)则较感叹句更能激荡情感,而陈述句则较前二者为平缓,三者的错落使用,恰如乐声之轻重缓急,井然有致。在前三章中,作者皆用陈述的语句行文,平叙自己的遭遇,情感总体仍处于平缓之际,到第四章,语气转为激烈,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说的韵脚转向入声,还体现在句式由陈述转向反问:“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停留此处又能做什么呢?思念亲人之情是不会停止的。前两句为第三章的末句,后两句为第四章的首句,情绪在陈述转至反问中登上了一个台阶,仿佛巨川入江,汹涌激切。及至后面的三章,反问与感叹不断出现,表明作者的情感已难以压抑:“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手足仓促而去,谁又能不苦悲呢?既是对前文自我安慰的否定,更是一种回到现实的痛苦,情绪由前文“丈夫志四海”的陈述之平泛,转向反问之跌宕。而“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感叹一句,前承了上文的反问,又将这种情绪往更沉痛的状态推进,及至后文“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连续的发问,更显情感的急切。可以说,作者成功地将情感的跌宕起伏,通过句式的转换表达出来,显示了作者对语言极强的把握能力,诗歌极具感染力,令人不忍卒读。
总的来说,作者的情感在声节、虚词和句式等文辞的错落安排中跌宕昭彰、感人至深,展现了作者面对生命、离别、亲情乃至宇宙人生的种种困惑、不解与愤怒。因此,以《赠白马王彪》为代表的汉魏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其醇厚深远的意味,正体现在其文辞与情感的相契无间。在阅读与赏析中,不断地探求文辞与情感的联系,我们将体味到汉魏诗人那种真挚而深沉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