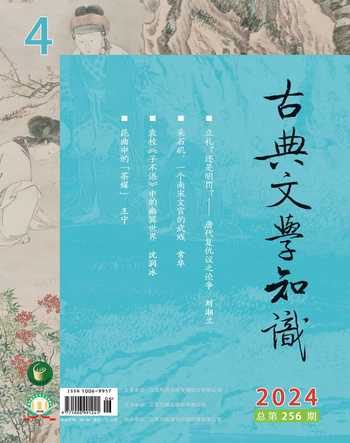辨宝钗扑蝶所持之扇
陈曾媛
“宝钗扑蝶”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情节片段。该情节在绣像、回目画、绘本、画报等众多《红楼梦》图像中均有绘制,但其持扇形制却始终存在分歧。
《红楼梦》图像史肇始于1791年萃文书屋木活字印刷的《红楼梦》程甲本,但此时选取的宝钗造像是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宝钗坐在宝玉床边做针线的场景。直到1818年左右《绣像红楼梦》藤花榭本的刊刻出版,才开始以扑蝶情节作为宝钗造像,这也是后来大部分图像选取的人物造像场景。由此,在文本视觉化、具象化的图文转化过程中,牵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即宝钗所持之扇是折扇还是团扇。
《红楼梦》脂本写道:“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的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该情节未明确提及持扇形制,导致各类“宝钗扑蝶”图像在此问题上一直未达成共识。但这个问题又与文本紧密相连、于小说理解至关重要。通过梳理文本的细部描写,读者能真切感受小说之体大思精;同时图像选择暗含着绘制者的阅读诠释倾向,更为一探清人的阅读习惯和风尚提供可能,连接起文学化理想世界与真实社会语境。
折扇与团扇
不同于男佩折扇、女佩团扇的一般认知,《红楼梦》中的佩扇种类与性别并无直接关系—即男子可以用团扇,女子亦可用折扇。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袭人命小丫头将元春的赏赐之物取出来给宝玉过目,“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当宝玉问及其他人得到的赏赐,袭人以宝玉获得之物为参照,在此基础上增减,依次提及老太太、太太、老爷、姨太太、薛宝钗、林黛玉一干人等的获赏,其中就包含人皆有之的上等宫扇。宫扇即团扇,宫内赏赐的对象和物件一定是经过细致考量的,不得有任何差错。从宝玉和贾政都得到了团扇这一赏赐来看,团扇的使用不区分男女,其并非女子专属物。
而折扇也并非男子专属物,《红楼梦》中女子同样使用折扇。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情节里,宝玉听晴雯说喜欢撕扇,把自己的递与她撕以外,见麝月持扇路过,“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几半子”。尽管文中均未提及被跌和被撕的扇子是团扇还是折扇,但返回事件发生的起因,“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扇股指折扇扇骨的数量,由此,这些撕碎的扇子包括麝月所持均为折扇。
在小说语境中,从扇子的使用情况来看,可放入袖中的是折扇。贾宝玉初见蒋玉菡时“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此处尚不能确定这把从袖子里取出的扇子究竟是团扇还是折扇,直至后续扇坠送人才知晓。“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扇坠儿没了,便问他往那里去了。”从折扇的佩戴来看,由于折扇和扇套是挂在外衣上的(沈从文《中国服饰史》“清代男子腰带上挂满刺绣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饰物”),袭人为宝玉宽去外衣时自然会发现,时常挂在外衣扇柄上的吊坠不见了。可见那把从袖中拿出来的是折扇,折扇既能挂于腰间,也可以放在袖中。
从女子使用折扇以及折扇可放置袖中的文本细节来看,宝钗扑蝶“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很可能使用的是折扇。当然,还需结合服饰和扇制的现实情况进一步讨论。
折扇书写:现实经验的重塑
《红楼梦》故事背景的时空定位存在模糊化情况,似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但不妨碍行止坐卧、衣冠服饰、家具陈设等等细节,融入作者的现实社会生活经验。沈从文、郭若愚等学者亦提出,小说中服饰描写真实反映了清代前期的服饰面貌。那么曹雪芹从小生活在江宁织造署,对式样、图案、色彩、质地等衣饰的认知,就是《红楼梦》人物衣着服饰描写的经验基础,根据清前期的服饰可以大致获悉《红楼梦》中的人物服制。
《红楼梦》中上层阶级贵族女子所着多为满族服饰(王云英《从〈红楼梦〉谈满族服饰》:“诚恳呼吁画家、艺术家们……要绘出旗装的《红楼梦》人物来。”),从服制和团扇形制来说,不具备团扇放入衣袖的条件。康熙、雍正时期衣袖不超一尺,且袖口较窄,为求利落,多为箭袖,到乾隆以后衣服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而贵族用宫扇,从现存藏品看,基本尺寸在纵30厘米,横25厘米,放入衣袖不甚现实,由此宝钗扑蝶所持当为折扇。
但在清代,折扇多为男子随身携带,曹雪芹也将此现实经验融入了小说。折扇和扇袋作为时髦的装饰物,常被男子挂于外衣腰带上,曹雪芹写及宝玉得老爷欢喜被小厮们讨要彩头以及抄检紫鹃房中得到的宝玉的旧扇和扇套,即得印证。
在小说的折扇书写中,曹雪芹立足现实经验,又借宝钗扑蝶、晴雯撕扇、麝月持扇等情节,重塑现实经验,突破折扇使用常规,以少女扑蝶嬉戏场景的欢快感,消解了折扇多被男子携带、用于正式场合的严肃性。代表文人士大夫高雅情趣的折扇,进入闺阁女子的生活空间,一方面打破了世俗对女性持团扇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在大观园保护起来的自由之境中,赋予她们挥洒情思、任情恣性的权利。
制造团扇:图文表达的错位
图像是画家、刻书商等绘图者阅读《红楼梦》的产物,但是文字与图像的表达内容和效果并不是对等的,除了大致呈现小说场景以外,具体刻画和细节填补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包括人物持扇的選择和处理。《红楼梦》图像中绝大部分都背离文本绘制了团扇,可以说持团扇的宝钗形象,是书商和画家选择和制造的结果。
团扇的大量使用与明清美人画程式发展密切关联。人物画作为绘画史上的主流画科之一,自汉代开始其“正人心,淳风俗”的功能就备受历代帝王推崇,作政治教化之用。至明清,以视觉吸引力为卖点的美人画开始颠覆人物画中仕女图的严肃性,不再是单纯的士人文化的产物,而是商品经济和市井趣味催生的程式化图式,其中不只包含了画家或画工的主观处理,更反映了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影响下读者的审美情趣。
团扇就是高度程式化的一环,包含着受众对女性温柔端庄形象塑造的执着,也是女性空间中的代表性物件,迎合了清代读者对宝钗形象的心理期待。团扇虽男女通用,但其精巧雅致的特点,总与美人形象勾连。同时,扇面的隐约通透感,在作为遮掩妆容、拒绝观赏的障碍物外,也以半遮面的神秘性满足男性对女性柔美含蓄形象的意淫。
曹雪芹着意描写女子持折扇,用以扑蝶也好,撕着玩也罢,都赋予了大观园女子才气纵横、自由任性的权利。画家和画工们普遍忽略文本,绘制象征一团和气、温柔婉约的团扇,无疑是对小说文本和作者本意的颠覆,这种图文表达之间的错位造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折扇文本描写打破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凝视,在图像表达中落入世俗趣味的窠臼,在程式化的商业刊刻出版影响下,侵入《红楼梦》建立起来的文学化自由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