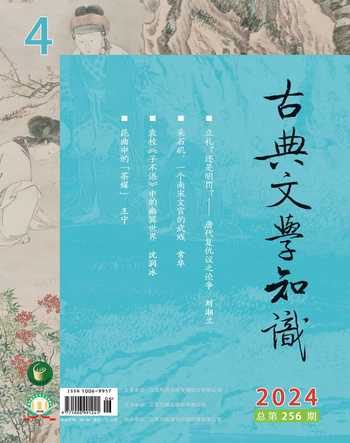《楚辞·渔父》与汨罗文学
孙明君
汨罗文学成熟的标志
《楚辞·渔父》云: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旧说或以为《楚辞·渔父》为屈原自作。说见王逸《楚辞章句》:“《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王夫之《楚辞通释》所见略同:“《渔父》者,屈原述所遇而赋之。……原感而述之,以明己非不知此,而休戚与俱,含情难忍,修能已夙,素节难污,未尝不知冥飞蠖屈者之笑己徒劳,而固不能从也。”
《渔父》非屈原自作甚明。若是屈原自作,作者不会自云“屈原既放”。《离骚》等篇中屈原以“余”“吾”自称;“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等句是他人眼里的屈原形貌,不能看作作者的自我描摹;《渔父》以“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不复与言”结尾,说明这篇文章的重点人物是渔父,起码渔父是重点人物之一。如果是屈原自作,应该不会以渔父结尾。
《史记·屈原列传》云: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司马迁把屈原与渔父的对答看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遂把《渔父》主要内容录入传中,但并没有说明此为屈原作品摘录。他也没有引用“渔父莞尔而笑……不复与言”一段,因为这个结尾与塑造屈原形象无关。
《楚辞·渔父》的作者应该是一位汨罗人。王逸《楚辞章句》并不否认楚人参与《渔父》的后期创作:“(渔父)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明确推断《渔父》是楚人的作品:“应该是后人的著作。但作者只是把屈原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并无存心假托。它们之被认为是屈原作品,是收辑《屈原赋》者的误会。这两篇(《卜居》《渔父》)由于所用的还是先秦古韵,应该是楚人的作品。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说楚人并没有错,这与汨罗人也不矛盾。宽泛一点说是楚人,具体一点说是汨罗人。
《楚辞·渔父》云“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王逸《楚辞章句》云“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时遇屈原川泽之域”。以上地理环境为汨罗江一带的景色。《渔父》中屈原自云“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等句更是直接证明屈原自杀之地是在汨罗。屈原投水自尽,距离他最近的人就是汨罗人,深知其生命终点思想状态的只有汨罗人,于是他们以屈原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楚辞·渔父》这篇汨罗文学的千古名作。
印证九死未悔的屈原精神
《渔父》通过屈原路遇汨罗渔父之后,两人之间的对话,表现了屈原生命临终前的思想状况,肯定赞扬了屈原明辨是非而绝不同流合污、坚持真理而至死不渝的伟大精神。王夫之《楚辞通释》曰:“(渔父)闵原之忠贞,将及于祸,而欲以其道易之。原感而述之,以明己非不知此,而休戚与俱,含情难忍,修能已夙,素节难污,未尝不知冥飞蠖屈者之笑己徒劳,而固不能从也。” 渔父在屈原生前悯其忠贞而殷勤劝告,汨罗人在屈原死后悯原之忠贞而赋《渔父》。
《楚辞·渔父》中两次写到屈原对渔父的回答,第一次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第二次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是屈原离世之前与他人最后的对话,汨罗人忠实记录了屈原的遗言。
屈原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诗人,具体来说他具有爱国精神、民本精神、求索精神、斗争精神。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他很早就确立了宁死不屈的志向,这个志向反复出现在《楚辞》中。《离骚》云:“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思美人》云:“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惜往日》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如果说人在距离死亡尚早的时期,想象一下死亡并不难。到了屈原写作《怀沙》的时候,到了楚人写作《渔父》的时候,生存或者毁灭成为一桩迫在眉睫的事。屈原的斗争精神和赴死决心始终没有丝毫动摇,《怀沙》云:“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质抱青,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將以为类兮。”面对滔滔巨流,他没有任何畏惧,愿意以死亡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渔父》用他者的眼光再现了屈原的思想与性格,足以与屈原的《怀沙》等作品互相印证,充分表现了屈原九死未悔的崇高精神,进一步突出了屈原为理想抱负而献身的坚定意志。《渔父》的作者“闵原之忠贞”,对屈原精神进行了真实记录,为后人了解屈原精神留下了最后的珍贵遗产。
体现兼容并蓄的汨罗精神
《渔父》的作者一方面歌颂屈原,肯定屈原,同时又具有兼容并蓄的开阔心胸,也为我们塑造了汨罗隐士的形象。渔父提醒屈原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他的劝说出于一片好意。朱熹《楚辞集注》:“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王夫之《楚辞通释》曰:“江汉之间,古多高蹈之士,隐于耕钓,若接舆、庄周之流,皆以全身远害为道。渔父盖其类也;闵原之忠贞,将及于祸,而欲以其道易之。”又曰:“君子遇有道则行吾志,无道则全吾身,何凝滞之有哉?”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江汉之间活跃着一大批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高蹈之士,渔父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這从侧面说明汨罗一带文化氛围浓郁,形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士人群体。《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汨罗渔父是一位知书达理的高士,他代表了汨罗隐士群体的思想境界。他温文尔雅而不咄咄逼人,他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并予以尊重。在听到屈原的陈述之后,他知道士各有志,无法勉强,于是潇洒离去。
《楚辞·渔父》与《庄子·渔父》的关系。渔父是先秦时代的隐士,他常常与道家思想联系在一起,成为道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庄子·渔父》为庄子后学所作,意在表现庄子后学中“法天贵真”的新思想,与《楚辞·渔父》相比,它更加具有学术性。在《楚辞·渔父》中渔父则主张贤者居世顺时而变,与时推移,不凝滞于物。这种处世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庄子思想,可以说是广义的道家思想中的一派。而《楚辞·渔父》中的渔父是为了解决屈原的现实问题而帮助屈原分析问题,所说的也符合人之常情,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庄子·渔父》是现存“渔父”文献中的第一篇作品,《楚辞·渔父》是第一篇模拟前人名篇的同名作品。两篇《渔父》先后问世说明中国文学中的“渔父”体文学在先秦时代已经成熟,即将对后世渔父体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楚辞·渔父》的作者并不排斥屈原的选择,他尊重屈原的选择,敬仰屈原的人格。但比较起来,他似乎更欣赏渔父的处世态度。作者自己很可能就是一位隐于耕钓的高蹈之士。两位人物并存于文章中,充分说明汨罗文学的巨大包容性。
《渔父》作为汨罗文学的开山之作,描写了汨罗山川河流,歌颂了屹立在汨罗江畔的伟大诗人屈原,塑造了汨罗隐士形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汨罗文学典型的《楚辞·渔父》具有与其他《楚辞》篇章鼎足而立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