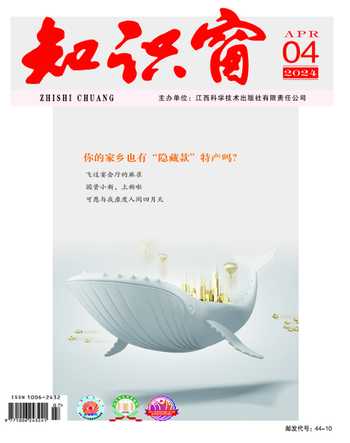慢火车的窗外
洛风
慢火车的窗外,是冬日下的无声话剧。
火车没有停下的迹象,一直晃晃悠悠的,或许是因为穿越山区的路不能疾驰,所以我能看清眼前的景象。黄褐色的土地上,一层冬小麦的麦苗在阳光下排列得整整齐齐,在坡上偶尔裸露的土地里,或许埋藏着作为种子的红薯块根。
豫西的土地大都是如此,比如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在这两个大区域稍稍交界的秦岭余脉间,带着角度的沟垄岭坡反而成了更常见的存在。在这片丘陵与黄河水涤荡过的冲积平原上,中原的传统作物总能找下落脚之地。
村庄,杨树林,光秃秃的树铺满田野的尽头。小片的林木作为农人的副业,在这个燃气已经通到千家万户的时代,仍然会有人到树林里捡些干木棍当柴火——毕竟丘陵间的气温忽冷忽热,夜的寒冷总是沉在人们居住的盆地间。而到来年三四月份,包含着杨树种子的杨絮就会乘风漫天纷飞,飞到它们能飞到的任何地方。
再往前,荒草潦草地铺在那些枯黄的田野上,似乎一个火星就能点燃这干枯了两三个月的草。目光再往上看去,黄叶裹着的野酸枣树三三两两地排列在上山的土路两侧。树与树,坡与坡,层层叠叠,此起彼伏,出现在豫西山区的每一个角落。
又近了,红砖与水泥交叠的村庄终于缓缓变成电影的定格杨面。绿色与褐色的菜地散落在村边,杨树稀稀拉拉地立在村子周围,水泥电线杆就从杨树的缝隙间手拉着手,将那看不见的能量送进每一家。偶然在这红砖水泥间能看见贴着瓷砖的小洋楼,在一众房子间十分显眼,与小洋楼相应的是房顶上不多见的太阳能板和不少太阳能热水器,它们一道懒洋洋地卧在房顶上。村子外,几道沟渠从田间延伸进村中,又汇合到村外的大沟里。再往坡上看去,黄色的荒草、落叶与褐色的土地一道,组成中原农民最基本的底色。
我的双眼猛然一黑,话剧到了转场的时间,火车驰进漆黑的隧道,双耳随即便有被压缩的空气堵塞的负压感。又是一瞬间,车窗外的世界明亮了起来,我来不及反应,耳道里的空气就被释放出来了。这一路上,火车要过好几个隧道,穿过或高或低的山丘,让本该曲折的路变得平直。
新的一幕里,我不知是池塘还是水库,闪烁着的水面在这荒野里显得格外柔和。如果是在夏天,水面上可能会有三两只鸭子,水边会有垂钓的人,但在冬天,只有一捧阳光洒在波纹间。
拉着煤与集装箱的货运火车呼啸着与我擦肩而过,不知这是从西部送往东部的货物,还是从北方送往南方的煤炭。火车与火车纵横交织,源源不断地迸发活力。
到汝州了。
汝州是洛阳至南阳这一场旅途的分水岭,汝州以北的水系,属于黄河;汝州以南的水系,属于长江;汝州以东的水系,则属于淮河。北汝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汝州,与秦岭的余脉伏牛山一道,将中国地理的南北方由此分开。
火车继续行进,开进层层山峦间。或许是迎着东南风的缘故,面朝南方的山总是要青翠不少,丘陵与耕地并不显得那么荒芜,即便是褐色的未耕之地,土壤也似乎湿润许多。古中原的文化就埋藏在崇山峻岭间的土壤下,这片大地默默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原农民。
从小米到小麦,从红薯到玉米,中华五千余年的农耕文化在这片大地上从未被改变。脚下的土地,是中原农民最后的生命底线,也是整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基石。火车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我再往窗外看去,山在一层一层地往后退,环绕在盆地里的耕地终于连接成大块绿色。这是冬小麦,到了来年六月一日前后,这些青色的麦苗将成为金色的麦浪。
一条约百米宽的大渠横在了我的脚下。水平静地流着,没有河流的激荡翻涌,有的只是北上的平坦。这是南水北调的干渠,漢江水自丹江口水库出发,沿着京广线,越过黄河,顺着太行山脚一路直抵。干渴的城市得以缓解,荆楚大地的水滋润了燕赵山坡。
村庄与农田就此交错重叠,火车穿过一片片厂房,逐渐拉闸减速步入市区。火车站的月台已清晰可见,躁动不安的旅客已收拾起身,这场冬日下的无声话剧就此谢幕。一路旅途,唯有带入车厢的两脚乡土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