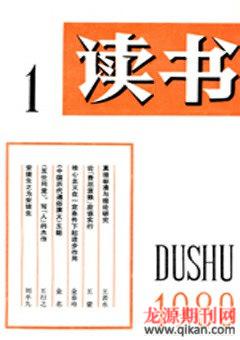《四世同堂》,写“人”的杰作
王行之 丁 聪
一九三六年,《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开始连载的时候,老舍先生写信给编者说:“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当时,很可能有人讥笑这是“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因为,那时候,只有把自己的儿子叫作“犬子”或“小犬”,才配算是“谦虚”。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和实践证明的却是:老舍先生说的是老实话,“骆驼祥子”这个中国洋车夫,后来成为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的“国际名人”。
祥子的成名,没有什么秘诀在内,无非是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老问题:文学创作重在写“人”,写社会中真实的人,写有生命的活人。多少中外名家名作的创作经验,说明的都是这句“老生常谈”。老舍在他的《老牛破车》中,也发表过一段精彩之极的“旧说法”,他说:“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这是老舍关于小说创作和文学特性的真知灼见,更是他自己的创作追求的自白。
看看老舍一生所写的几十部短、中、长篇小说和几十部话
三教九流的人物写得多,是《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特色之一。一般来说,长篇小说之“长”,常常长在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或一家一事,细细地叙述其来龙去脉,成长、发展和演变。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把时代的、社会的诸多有关因素带进来。象老舍自己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牛天赐传》和《离婚》,顾名思义就是以一人、一事为主的。写好这类单线索贯穿的长篇小说当然很不易;而且,大手笔也常常是把笔触伸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在广阔的天地里写出人物群像来的。但是,相对的说,象《四世同堂》这样一骨脑写出一条胡同各家各户(实为各行各业)的沉浮兴衰,为沦陷时期的“北平”老百姓们立传,遇到的困难毕竟要更多一些,作家的生活阅历是否深广,艺术表达才能是否精湛,都将遇到更为严峻的考验。弄不好,就会心有余而力不逮:要么,书中的人物虽有姓名而无生命,事件的叙述淹没了人,所谓“人物”只不过是些形象模糊的影子;要么——干脆写不出来。
然而,人物众多、热闹非凡的《四世同堂》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只要读过这部书,就好象也在“小羊圈”里住了好些年,那么多胖的、瘦的、村的、俏的、贫的、富的、贤的、愚的、高的、矮的……,七个大门里的几十口子男女老少,都成了使我们感到兴趣的老熟人。起码,教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的人物有:“四世同堂”的“老人星”祁老者,被日本人逼得投河自杀的布店掌柜祁天佑,正直善良的中学教员祁瑞宣,贤妻良母“小顺儿的妈”,匹马单枪和日本人死拚的爱国诗人钱默吟,一心想巴结日本人的下台北洋官僚冠晓荷,女光棍兼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大赤包,唱大鼓书出身的姨太太尤桐芳,后来当了女特务的摩登女郎招弟,老年间的搬运工人“窝脖儿的”李四爷,眼神不济可心眼极好的李四大妈,给洋人“摆台儿”的丁约翰,会耍狮子的棚匠刘师傅,京戏女艺人文苦霞,说相声的方六,沿街叫唤“转盘儿话匣子”的程长顺,被日本人砍了头挂在前门五牌楼上示众的车夫小崔,小崔的吵架对手兼生平第一好友的剃头师傅孙七,因受日本人侮辱而气死的农民常二爷,江湖好汉金三爷,窝囊废书生陈野求,无聊浅薄的小汉奸、干巴瘦猴祁瑞丰,一身肥肉全无心肝的胖菊子……还有李空山、蓝东阳、高亦陀、牛教授等大大小小的各类汉奸。这么多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物,出现在一部作品中,在别的书里我们还很少见识过。人海茫茫,世途惟艰。《四世同堂》创造出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反映了时代面貌,可以说再现出一座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城。
是的,我们在《四世同堂》里,能够看见一座黄沙
注重写人物和善于写人物,从作品的艺术效果看,当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时会横亘着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君不见古往今来的文坛上,不少人写出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终其一生却留不下一个值得人们记忆的人物。多少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里,无声无息,随着逝水东流了。只有《四世同堂》这样写出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的作品,才永葆青春。
前述《四世同堂》中的三教九流人物,他们不是书中某个中心人物的所谓陪衬者,在各自的地位上都是主要的角色,谁也无法代替谁。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一样,错综复杂,互不重复,一人有一人的相貌,一人有一人的性格,一人有一人的行为,一人有一人的语言。这些人,每个人的出场都为我们的视野开辟出一块新天地,在每个人物的身上都能闪烁着艺术创造的光彩。
比如,女汉奸大赤包儿这个人物,在我国文学人物的画廊中,就是不会被别一个人的艺术光芒所遮盖的“这一个”。
此人外号所以叫做大赤包儿,因为这个快五十岁了的老女人专门爱穿红衣服,厚厚的脂粉藏不住脸上的皱纹和雀斑,很象是北方夏天的一种小瓜“赤包儿”,经儿童玩耍揉弄之后,皮儿皱起来,红皮下露出了里面的黑种子。大赤包儿的气派大得很,一举一动都颇象西太后。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个子比丈夫冠晓荷高出一头去,还因为她比丈夫更早地巴结上了日本人和大汉奸,当上了在她看来是光宗耀祖的“新朝”官儿——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大赤包儿的一部升官发财史,就是她无耻、贪婪、暴戾、狠毒、奸诈、残忍,外带泼辣、干练等独特个性的大展览。大赤包儿串门子,大赤包儿过年,大赤包儿逛北海,大赤包儿打麻将,大赤包儿和小崔打架,大赤包儿欢迎日本特使,……这都是她历史上的大关节目,由老舍先生幽默、辛辣的语言艺术写出来,真是好看煞人。这里只讲一件小事吧。那一次,冠晓荷想去日本人那里密告紧邻、爱国诗人钱默吟,却又犹豫辗转听来的消息不真切。此时,大赤包儿发话了:“真也罢,假也罢,告他一状再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教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地向着日本人,不也有点好处吗?你要是胆子小,我去!”这段话,在她称霸“小羊圈”,以“北平第一个女人”自居的全部霸业中,算不了什么。但就是她的这几句话,把钱默吟一家害得家破人亡了。由于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异常生动,在她身上概括了国难时期应运而生的许多恶人的特点,形象的认识作用就跨越了时代。从她的为人行事中,我们必然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期间的许多人和事。
大赤包儿和她的丈夫冠晓荷,是“人”中的丑类,小羊圈的居民们都用憎恶、愤恨的眼睛瞪着他们所居住的“三号”。但是,三号并不就是清一色的汉奸窝,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两个受到邻里谅解的人物:个子瘦小眉眼很俏的姨太太尤桐芳,后影儿很好看面孔不怎么样的大小姐高第。这两个人物谈不上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可她们决不是大赤包儿夫妇的同类。象尤桐芳,她的身世,她在冠家的地位,她和邻居们的关系,她一心要杀死几个日本兵报仇的决心等等,都很值得人们同情甚至于尊敬。然而,这个人的为人行事,又处处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姨太太。
同样,“四世同堂”的五号祁家,是全胡同的人们都敬佩的好人家。老一辈的祁老人、祁天佑、天佑太太,是忠厚善良的老实人,他们的形象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自己的祖父、父亲那一代人,这里暂且不说。单说少一辈的祁瑞宣、祁瑞丰、祁瑞全三兄弟吧,老三瑞全是个爱国者,日本人进了“北平”城,他第一个逃出“北平”去参加了抗日的军队;老大瑞宣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亡国之痛的磨难,既要担负全家的生活重担,又时时受到汉奸们的排挤和迫害,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始终坚守住内心深处的民族气节。就在这个家庭里,偏偏出了个一心要当汉奸、而又一直得不到汉奸赏识的祁瑞丰。这是个老婆被汉奸抢去他都感到无所谓的卑污小人。他也生活在祁家,在气氛上似乎不谐调,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小羊圈”的其他人家,比如那个不愿作汉奸而终于作了汉奸的牛教授,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里,就涉及到《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一个重要特点:真实,发人深思的真实。在老舍先生笔下,人物不是机械地复述作者政治见解的傀儡,生活不是为图解某种观点而人为地去简单化。他把生活、人物的全部复杂性,如实地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进行再认识,加深对生活的理解。老舍先生是一位充分信任读者的鉴赏力和理解力的大作家。
我认为,《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这种真实感,是极为可贵的。我所说的真实感,不仅指的是书中那么多的细节真实描写,不仅指的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那些浓厚的人情味,还指的是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四世同堂》全书几十个登场人物中,没有一个鹤立鸡群的“英雄典型”,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中的某些人,曾把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当局的身上。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表现“北平”人民的悲惨遭遇,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们阅读《四世同堂》时在感情上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正是如此。书中所写的是眼泪,是痛苦;而在我们的耳畔,却响起“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脑际想到了我党领导着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为拯救祖国、拯救人民进行着伟大的斗争。要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联想力,因为这是历史事实。须知,我们不能要求文艺作品——而且是“一部”文艺作品,把生活的一切方面写尽。如果有谁想看抗日战争期间的英雄故事,尽可以去读别的作品嘛!《四世同堂》专门记载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页痛史,我们同样感谢作者。至于《四世同堂》的人物口中有关于“中央政府”、“蒋委员长”之类的极个别词句,这是特定的时代、生活打在人物身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什么奇怪。事实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一方面表现了“北平”普通老百姓对国民党“打回来”抱有希望,一方面写出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弃保定,丢南京,武汉撤退,广州失守等事件,“北平”人民盼望国民党军队打回来的幻想逐个破灭。这既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也含有极为深沉的讽刺、批判意味在内。
也许就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吧,《四世同堂》这部书,自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一九四九年将它的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印到四版之后,在过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间,新中国的出版界对《四世同堂》持冷淡态度,一直没有重印它。在此期间,国外不仅出版了英文译本,日本的铃木择郎先生也将《四世同堂》全书(包括第三部《饥荒》)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这种怪现象的出现,难道是光彩的吗?!
现在,《四世同堂》终于时来运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而且,这次重印,只是以老舍先生的工整手稿为底本,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一些错别字和衍、漏之处,至于长期以来被误认为“不合时宜”的字句,则“不删、不改”,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好!我为出版界这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常作法鼓掌喝彩,为广大读者终于能够读到老舍先生的艺术杰作感到高兴!
瑞丰的中山装好象有几千斤重似的。他觉得非常的压得慌。……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的各处立着,……他们好名胜都害着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