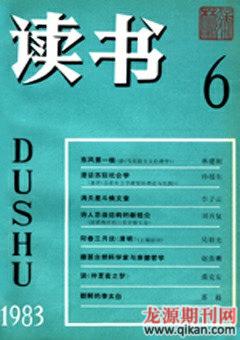漫话苏联社会学
兼评奥西波夫著《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沙俄时代,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画过一幅名为《弗拉基米尔卡》的历史风景画。这是一条向西伯利亚发配流犯的必经之路。阿·托尔斯泰曾这样描写流犯们走在这条充军路上的情景:
草原上夕阳西沉,
远处的羽茅草金光如焚,
囚徒的脚镣,
扬起了道路的灰尘……
在这条路上,有过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明天的美好社会,在镣烤声里和风沙尘中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如今,当我们面对这幅名画,回顾六十多年来苏联社会学如何研究这个曾是希望中的社会,将不是“乏味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安家落户
苏联的开国之父列宁,在领导劳动人民赢得自己的社会之后,又带领他们从事建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事业。他深刻理解科学知识在帮助党和国家管理社会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屡屡告诫共产党员“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的狂妄自大。他特别强调“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党要正确地了解社会的状况和人民的要求,社会学是不可缺少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此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不必再借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含义更广泛的名词来代表自己。所以,第一个把社会学这个名词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列宁。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有丰富的理论社会学原理,而且也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学先驱们发明的经验研究的手段和资料,他们还亲自编制过工人状况调查表或提纲,从事过大量社会调查研究。列宁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在他的倡导下,苏联社会学家如斯特鲁米林、卡博等在二十年代做了一些为国家所需要的社会学研究工作。
社会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分化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正是科学进步的标志,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进步的标志。
苏联社会学不能调查苏联社会
三十年代,刚刚渡过惊涛骇浪的苏联社会,一旦驶入比较平稳的航道以后,过渡时期就已萌发的个人迷信的官僚主义综合症开始一步步侵蚀党和国家的健康机体。当社会主体因个人迷信而遭到贬损的时候,社会学研究客体就只能成为禁区。一个失去了研究对象的科学,即使是列宁亲手培育的,也只好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囚徒而被打入封建主义冷宫,就象中国传统笑话所说的:“公文、包袱、雨伞和被押解的和尚都在,就是公差我不见了!”公差的官服一旦和袈裟易位,公差就成了犯人。革命的社会学一旦失去客体,立即成了社会学的反革命,这种事例,人们见得多了。笑话并不比现实更可笑,然而现实却比笑话更辛酸!
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约二十年间,苏联社会学唯一保持一口游丝般的气息的,是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存在的、事后勉强可以追认为“理论社会学”的东西。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家只能由哲学家来顶替。
报户口又用了二十年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一些遭到贬黜的学科和流派开始小心翼翼地露头,但社会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却迟迟未能开始。要期待有一个人能象恩格斯那样勇敢地宣布哲学原本就不该越俎代庖地囊括一切学问,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苏联社会学向称霸了二十年之久的哲学与社会学“同一论”的挑战,却是由国外的学者首先发难的。他们是东德的尤·库钦斯基和保加利亚的托·巴甫洛夫。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学术多面手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向哲学和社会学的“同一论”(实质上是“哲学代替社会学论”)开了一炮,要求“落实政策”,发还被没收的社会学阵地和研究对象。自此以后,讨论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再收,甚至到了今天,还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这场争论的产生,本来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争论为什么如此旷日持久。在局外人看来,简直是一场从概念到概念的疲劳轰炸,由牛角尖钻进鹿角尖的文字游戏。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绝不是烦琐哲学的无谓之争,而是苏联革新派既同保守派又同超革新派进行两条战线的复杂斗争的反映:触犯众怒的“同一论”固然要大力加以反对,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学领域完全排挤出去的自由化倾向尤须严加防范。由于三者内部又有分歧,所以争论的过程就呈现为一片目迷五色的杂乱景象。到《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出版的一九七九年以前不久,总算把一个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作为结论暂时敲定下来。二十年光阴总算换来了一个煞费苦心的提法: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担负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功能。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分身有术,一身而兼二任焉: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同哲学合而为一;它作为社会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础,就是普通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苏联社会学的阵地扩大到居然囊括哲学而有之,另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吃亏,除了原有的哲学阵地外,还在社会学中占有一块除方法论之外的关键性飞地——普通社会学。这确实是一个为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而非此莫属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实质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在逻辑上,它的阿基里斯之踵毕竟是明显的。因为,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既是哲学又是普通社会学为例而类推之,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岂不应该也是普通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普通政治学、普通人类学、普通心理学等等了吗!但这些老大哥学科却并不谦虚到多此一举,把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膨胀到成为普通理论的地步,而把本系统固有的特殊理论方法论排斥在普通理论之外。当然,这类争论的考验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寻求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并非坏事,而对于绝处逢生的社会学来说,犹如透过眼泪的阳光更闪耀,经过囚禁的自由更风魔,它或许会兴奋得“欲往城南往城北”,也是意料中事。
以上是理论方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苏联社会学组织工作重新起步的时间表。
在苏联,要立一门科学,最好先立一个机构。但设立机构一事,却不是学者的生花妙笔所能济事的。苏联社会学,从一九五七年东山再起以后,国内第一个社会学机构迟至一九六○年才建立,而且是附属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麾下的一个小小的研究组,名称也很生硬别扭,叫做“劳动与生活新形式”研究组,好象革命胜利四十多年,“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也搞过好一阵子,却到这时才第一次发现劳动与生活有了“新形式”,不得不打发一支小小力量去研究研究,至于其他属于旧形式的劳动与生活,则对不起,不屑一顾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劳动与生活的新形式,无疑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吧,但却偏偏派了一员专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大将奥西波夫出任该组组长!不过,这种“借你一个早安”的做法,比起阿巴公“一个早安也不借”,总算有了进步。并且,在苏联,只要有一个探索者被批准冒了头,其他的也就可以援例跟上,象树上有十只鸟儿,打掉一只会使其他九只统统飞掉的逻辑同样灵验。所以,奥西波夫的组不久便扩充为研究室,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大专院校也先后成立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室。一九六六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建立直属于自己的具体社会研究学术委员会,并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缅采夫院士任主席。随之,其他一些研究所也相继设立社会研究室、实验室和组。该委员会还与作为国际社会学协会会员的苏联社会学学会于同年联合出版《社会研究》季刊(后改称《社会学研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在哲学研究所具体社会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具体社会研究所。请注意,直到这个时候,还舍不得在“社会”二字之后,缀以“学”字。迟至一九七二年终于取得“社会学研究所”之名,至此,社会学才勉勉强强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报上了正式的户口,取得了与其他兄弟学科平等的身份,尽管它的普通社会学部分还明显地留有一块哲学保护人的胎记。
急起直追的策略:“东边日出西边雨”
无可讳言,苏联社会学走了一大段弯路之后,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验研究和社会工程研究方面,已失去了一大段宝贵的时间。苏联社会学家为缩短此中差距,做了颇为可观的工作,其积极性是很高的。据粗略统计,从五十年代末迄今,其重要论著已超过二千种。苏联社会学进展迅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演进已经到了不得不提出这种需要的程度。而学术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大量向西方经验借鉴,然后再加一番消化改造的功夫。
本来,有选择地进行文化交流,利用西方学术成就,并非蠢事,也不丢脸。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不讳言自己学说的三个资产阶级文化来源。列宁更坦率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入木三分,而利用其合理成分则涓滴不弃,绝不因人废言,也不“言以人贵”。《资本论》就是利用这一科学学法则的明证。但是,经过多次思想政治风波的苏联社会学,却用了一套策略来实现科学学的这一规律,那就是先批判后借用。苏联当前最有代表性的这部权威著作《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一个例证。这部总结性著作的作者是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起家的苏联老资格社会学家奥西波夫博士,责任编辑是格维希安尼通讯院士。全书俄文正文二百五十八页。第一编六十页讲马恩的社会学思想和苏联社会学史,其中第二、三章是真正阐述苏联社会学的,有三十九页,占全书篇幅百分之十五;第二编一百页,占全书百分之三十九,都是讲资产阶级社会学,应属于世界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容;第三编和结论共九十九页,讲的是苏联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但其末一章“社会发展的指标和指示器”是实践部分的重点,共四十三页,却明显地属于向西方借鉴的部分,很多内容还处于消化过程,有的不过是空洞的设想,并且其中至少有十页以上纯属介绍国外的东西。因此,全书正文真正属于苏联的部分,即使包括从西方引进后改造过的理论和方法,充其量不过占百分之五十的篇幅。可是全书的行文语气给人的印象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学摆出一副无情批判的架势。这好象封建礼教束缚下出现的一首谐音情歌所唱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哩!
历史的潮流推动着社会学前进
在世界历史潮流的推动下,苏联社会学从它复苏之日起,就带着一个日益明显的特征,即强调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强调以个人的需求和心理状态及主观态度作为研究的重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宣传中强调满足人民需要的思想,甚至提出给予“社会学保证”的口号。二、更全面地综合地看待人的问题,从片面的人手论恢复到了全面的人口论,强调把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经济和社会结合起来,对生活方式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全面研究。三、更深入地发掘个人的内容,开始对生动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感受、兴趣、态度、个人的心理需要、个人对生活与工作条件的满意程度等等予以关注了。
由于苏联社会学的服务对象发生了这种质的转向,反过来促使了社会学本身在结构、方法与手段上发生相应的变化。它表现为苏联社会学的分科化加速发展和社会学家队伍迅速增长,目前,苏联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已达到四、五十个,在科教、党政、企业部门中已有数百个社会学服务处在开展工作。此外,还表现在苏联社会学家试图利用按各种社会水平和各个社会领域拟订的社会指标和指示器系统及其统计情报来补充经济计划的不足。因为经济计划指标只反映“平均统计数的个人”,而无法了解各种现实的个人对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态度,从而难以确切了解经济计划的实际效果。
当然,上述变化和进展,哪些已进入认真研究和实施的阶段,哪些只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苏联社会学家对他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明确了。
如果说,人民的发展,社会的演进,促进了社会学科学的发展,那么,反过来看,科学的社会学是否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的水平,反映出社会学主体和客体相符的程度。
历史足迹的规律
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斥力,它把多少过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抛进历史的尘埃;而社会生活水平则是一个很大的引力,它吸引着自古迄今千万颗革命家的心和亿万双平民的眼睛。要对抗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压力,只有发展本国的社会生产力;要对抗西方社会生活水平的威胁,只有提高本国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高社会生产力与生活水平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一种统一的社会机制,应该如何求得其中的平衡与协调,得到相互促进的最大效果,而不是使两者相互促退,这是人类很高的艺术-政治。看来,世界已经进步到这种艺术越来越不能由个别人物来掌握的地步,社会的命运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要由广大的有各种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决定。社会学家们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不管历史的道路上留下多少形形色色的剥削与压迫的足迹,但是,越往前去,就会留下越来越多的作为社会主体的普通人的足迹。
弗拉基米尔路上的职业革命家们悲壮动人的呼声,唤起了十月革命后保尔·柯察金式的普通工农的战斗激情。把列维坦画笔下大自然的惨淡意境用现代文明装点成一派壮丽景色的,正是他们代代相继的业绩。人民终究是历史的主人。
(《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苏〕奥西波夫著,孙越生、张进京、马国泉译,孙越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