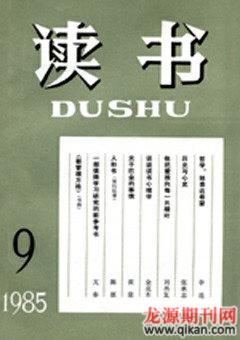《秘密的分享者》的秘密
裘小龙
长时间以来,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被认为是个海洋作家。确实,在康拉德的笔下,海洋尊严、伟大、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一次次惊险的航程中又有着异国情调的点缀,浪漫气氛的渲染,读来令人神往,遐想不已。不过,康拉德更善于把大海作为一种独特的背景,揭示出他的人物——那些远离陆地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狭隘和束缚的人们,他们的内心世界中深藏的种种愿望和情感,在这个背景下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台风》等作品,都着重刻划了人们在惊涛骇浪中的心理状态。《秘密的分享者》更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被誉为是一篇具有多层象征意义的杰作。
从表面的一层看,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船长刚要开始他指挥下的初航,一个名叫莱格特的杀了人的青年逃到了他的船上;船长与莱格特素昧平生,却冒着很大的风险,想尽种种的方法,营救了他。而在船长为什么要救莱格特这个问题上,康拉德从船长、莱格特、追捕者三个不同视角,展开了多角度的叙事方法,展示出了小说情节掩盖下的另一层更为深奥的含义。从这多侧面的交代中,我们可以看到,莱格特是个勇敢的人,他在另一艘船上当大副,船遇到了特大的风暴,他冒着生命危险,升起前桅帆救了船,但一个无赖却在此时与他捣乱,他在搏斗中失手,误杀了这个坏事的家伙;相反,那个追捕他的人是个懦夫,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声誉,如果他逮住了莱格特,必然会把无意的误杀说成故意的杀人,将莱格特送上绞架。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是否认为莱格特有罪,而是在于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来衡量、来处理。生活是复杂的,抽象的原则往往不能说明具体的事例,一件在众人眼中看来是错误的事,很可能恰恰有它正确的一面。作品中的船长所作出的选择,实际上代表了他作为一个人的理想。从这个意义说,这部小说已经是一个有着独特的思想性的故事了。
然而,康拉德似乎还不止于此。他又步步深入地告诉读者,船长对莱格特的同情和帮助,不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因素,还有着一些更深刻的心理上的复杂原因。现代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船长是把莱格特看作了“第二个自我”。这里所谓的“第二个自我”,在容格的心理学术语中称为“影子”。“这种影子并非是潜意识的个性的全部。它代表着自我所不知的或所知甚少的属性和特征——这些方面大都属于个人的领域,而且也可能是意识到的”。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人平时表现出来的性格的一种对立面,它在一般情况下是人所难以意识到的,然而它却深深地存在着,甚至包含着黑暗的冲动和残酷的内容。然而,认识这种“第二个自我”(影子)是人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就象船只要在神秘的大海中完成她的初航。小说意味深长地一再描绘了船长和莱格特的相似之处:他们毕业于英国同一个商船学校,年纪较轻就提到了指挥的岗位,但在各自的船上又都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些都是作者含蓄的伏笔。船长遇见莱格特后就更深切地感到,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也郁积着对周围的人的不满和敌意,稍有缝隙,愤懑的岩浆就会喷射出来。从某种意义说,莱格特做的一切,正是他潜意识里想做而没做出来的事。于是在这特殊的情形中,船长仿佛真把莱格特当作了“第二个自我”。作者设计了让莱格特穿上了与船长完全相同的睡衣,“在别人眼里,完全一个样”,这个情节即是点睛的一笔。在深层心理学中,这种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潜意识中倾向的情形,是用“投射”(投影)来概括解释的。这是一种既朦胧又清晰的认识,它影响并制约了船长的一举一动。从莱格特一上船,船长就称他为“我的幽灵”,还多次直接说成“我的第二个自我”,正反映了这种潜意识的折射。船长异乎寻常的同情和焦虑,也可以由此得到一些解释。当然,并不是说船长对“第二个自我”是一味赞同的。在小说的最后,莱格特要逃入孤岛,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个情节,包含了(船长)意识中对他杀人行为的否定和惩罚。尽管如此,“第二个自我”却是船长身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可毁灭;否则,船长作为精神上一个完整的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莱格特这个“幽灵”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甚至可以说,他作为一个人物是虚的,而作为一种意识才是实的。
在文学作品中,重视对人的复杂性的描写,是很常见也很有意义的,史蒂文生的《吉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即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然而,把人性中的“善”和“恶”抽象出来,拔到本体论的高度,或者神秘地把它们解释为某种先天的、超验的东西,就走到了一个极端。《秘密的分享者》在一定程度上即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毕竟,人的复杂性不能离开生活,尤其不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孤立地来谈。事实上船长的“秘密”并非是不可解释的,它所包含的内容正是社会中所存在的矛盾的集中反映。
在小说中,船长出现时就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他救莱格特这段经历,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作者并没有再追溯船长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是怎样形成的。不过,在一些段落里,读者们可以看到,他对陆地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不满的,对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抱有怀疑。不满和怀疑,决定了他追求大海上的生涯。这多少(不自觉地)有些逃避现实的意味,但现实是逃避不掉的,在海上,船长还是同样遇到了问题。小说着意渲染了船长的孤独和陌生感,他虽是船长,却并不了解他的副手和水手,对这条船也很陌生,甚至“对自己也多少是个陌生人”。他和周围环境依然格格不入;然而作为一个船长,他又要承担起种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对于这些同样是由陆地上社会的标准决定的责任和义务,他是不解而“陌生”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朦胧地有着否定这种社会存在的倾向。这些模糊的意向,在船长所厕身的社会的概念里,自然是“恶”,也是船长自己所不愿正视和承认的,因而,这也可以说只能是一种“秘密”。恰巧在莱格特的身上,船长内心种种“秘密”的东西似乎得到了“投射”,找到了一种“客观对应物”。于是,船长尽力救下莱格特,这其实包含了一种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对社会的挑战。当然,船长毕竟还是船长,他的“挑战”也只能是朦胧地在意识的秘密中存在。对于这样一种矛盾,康拉德是意识到了的。然而,康拉德解决的方法是悲观的,在《秘密的分享者》中,他只能让“第二个自我”一辈子孤独地流浪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康拉德与船长及“第二个自我”的共同的局限性。
为了烘托这“秘密”,康拉德还设计了一个爱“解释”一切的大副。在情节的发展上,大副几乎没起任何作用,但他与船长的怀疑精神形成了对比,他不能也不愿理解人的复杂,这多少象征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理性主义者一种沾沾自喜的态度。这是作品中隐隐可以听到的一个不同的旋律,颇象现代音乐中故意插入的不和谐音。他与作品中其他一些人物和细节一样,都在现实主义的处理中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值得玩味。
康拉德是个日益受到重视并好评的作家,他的“价值”在人们的认识中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十九世纪,评论家们看重的是他早期的一些海洋惊险小说,到了二十世纪,他的一些发掘人的内心的作品开始受到了关注,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其中就包括《秘密的分享者》。由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一些思想敏感而又精神痛苦的知识分子看不到出路,开始形而上地对人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想从人的“复杂性”(非理性)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因此,他们往往在康拉德的这些作品中寻找“知音”。上面提到的一部分评论观点,也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其实,《秘密的分享者》这篇出色的小说所体现的思想,是和现实生活一样丰富的,发展的,变化的。按照现代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在读者与作品接触时才产生的。对于一部作品,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的人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这部作品,至少会对作者笔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困境,获得一种新的认识。
(《秘密的分享者》,〔英〕康拉德著,载《小说界》一九八四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