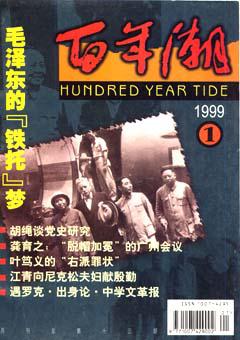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
牟志京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的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及对真理的幼稚向往,使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卷入了一场围绕家庭出身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一系列的巧合又导致了《中学文革报》的诞生,发表了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所写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小的震荡。从1980年起,有关《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记述在中外报刊文献上虽时有所见,但多出于局外人之手,传讹疏漏自然难免。今撰此短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我卷入了一场风波
在我国,出身与权利的关系在文革前也已十分明显。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马前卒,红卫兵从一出世就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这就是文革前所谓阶级路线的一个逻辑发展。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的唯一资格就是家庭出身。在红卫兵组织中地位高低的根据是其老子的地位。这确实是古今中外颇为罕见的。
出于无知或勇气,我在1966年“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同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发言时,遭一群红卫兵对我捶打唾骂,心中颇感滑稽。不久,在四中我们班上,又与同学辩论,我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在学校的处境日渐险恶,终于遭到一位红卫兵打手所率之众的殴打。于是借串连之机,到外地一去二月有余,拜访了江南、西南、西北多处革命胜迹。一路上天天烛下学“毛选”,虔诚之极,还自愿下乡劳动。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之后,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不想,此时京城风向已转,第一代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了。通过有周恩来、江青出席的12月16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宣判了反动“对联”的死刑,收缴了老兵们行使“党卫军”权利的牌照,并造成了一个导致造反派或曰第二代红卫兵诞生的真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兵所推动的政治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使老兵中的核心人物变成了走资派的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变成了狗崽子。但是老兵们毫无困难地断然拒绝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并形成了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为代表的一股非同小可的、与造反派对立的威慑力量,活跃于1966年底到1967年初。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1966年12月底,我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感油然而生。我在“对联”的辩论中表现的是无私所生的勇气,天真所致的义愤,仅此而已。我所持有的理论武器和血统论一样的原始与空洞。《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升高到一个理论课题去研究,其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一不引入醒目。我当即将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抄下,找到了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文是遇罗克的长弟,一副硕长的身材,带有几分书生气,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讲到扩大宣传途径。我便利用自己当时在四中由反对“对联”的历史所形成的地位,向校总务室借贷500元。然后通过小学的同学朱大年弄到了“三司”宣传部的一张介绍信,闯进人民解放军1201印刷厂,商妥了印刷业务。纸张在那个大字报和宣传品铺天盖地的年头是十分紧张的,在六部口纸张批发部购不到,但由他们介绍到农工民主党中央买到了两令上好的道林纸。所有这些事情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办成,罗文不禁喜出望外。随即由他联系“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送来了一份新的《出身论》手稿,准备以传单形式出版。
我在仔细拜读了新稿之后,感到有诸多不太满意的地方。我特别反感的是,在文章的调子中,一些地方渗透出一股怨气,另一些地方下笔刻薄,两者的结合,就失掉了客观理论的身份,让人情不自禁地猜想作者本人在出身上的恩怨利害。
我虽然对“小组”仍是十分崇拜,却没有妨碍我对《出身论》的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理论上我的新意几乎没有,但确实改变了文章的色彩。这一改装对我的重要性,来源于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辩论的一个简便或许是片面的认识——我在为一个自己没有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奋斗。
不料罗文见到遭我涂改的《出身论》之后,竟一反我对他温文尔雅的印象,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却又换了个脸,回到四中,并向我道歉,说小组的人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可按我的修改稿付印。
1201厂业务科的金科长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不久,排版完毕,传单大约三页,金科长询问如何处理所空的一页,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办报纸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请四中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做技术咨询(他出于对政治的谨慎,拒不参加组织),请朱大年的三中好友拼凑了毛体的报头,并由我起了一个朴素的报名,打出了“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旗子。第一期由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写了一篇杂文,选用了师大女附中陶洛诵、汪静姗处的一些活动消息,朱大年为首的三中“刺刀见红”的一篇文章。我连夜编排,并撰写了《出身论》的编者按和“司令部”的一篇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文章。天亮之时,我把在四中小院办公室里鼾声大作的罗文唤醒后,只身到1201厂交了稿,又经过校订、签字,《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在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了。
《出身论》与第一期报纸面世之后
遇罗克的大作在文革报上以《出身论》为始点,而非终点。在报纸的第二期到第六期上,分别发表了:《说“纯”》(2月2日)、《“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2月10日)、《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2月21日)、《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3月6日)、《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4月1日)。
文革报创刊的第二天,就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不断。大多数来访者抱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即索购报纸,但也有相当多的个人以他们的切身经历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反对《出身论》。
反对我们的首先是原来的老兵。北大附中的彭小蒙(他曾在红卫兵运动早期广为流传的讲话上引用“对联”)率百余之众来砸文革报。我们的联络处的外墙被糊满了侮辱咒骂《出身论》与文革报的大字报。
文革报的出版量每期在三万到六万之间,虽只在北京发行,与当时受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从全国收到的读者来信,迅速达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成了一项庞大的任务。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来信是向我们倾诉他们的遭遇和心声。其惨烈与真诚,往往使我们沧然泪下。
一个贵阳市的青年来信,讲到他在市中心闹市见到人们簇拥在一份长大字报前(那是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的全文《出身论》,洋洋约一万五千字的文章,要多少纸张和功夫!)。他好奇之余,从头
读起,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便跑回住宅,痛哭之余又想起回去读,便勉强抑制眼泪,赶回现场。不想此回才读几行,便又控制不住。这位读者告诉我们,他就这样不知痛哭着跑回住宅多少回才终于读完了《出身论》。
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北京的来信,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突出。
在文革报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多数报纸的销售滞缓,但文革报一直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我们在每一期出版之后,仅仅在市场上销出半数,另外半数留下,以飨外地邮购和来访的读者。
我因其他业务关系,很少参加卖报。但有一次随同去卖报,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手伸过来。我的手向前一伸,便被塞满大把的钞票。拿起报纸一递,便不知被谁扯去,根本说不上找钱。三轮车一空,双手哆嗦不停,方知卖报之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到他卖报时,人们排着队追他的经历。
当时相当多的小报也卷入了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辩论。其中包括《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除《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三家外,其余都对我们持敌对态度。那三家友好报纸,分别由朱大年、刘姜仁和四中同班同学主持,我亦是头两家的客串编辑。此外,李冬民的《兵团战报》还以首都兵团的名义登出了“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文革报创刊之始,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便定期造访。在第三期前后,他们对我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报纸活动期间,中央首长时常会晤第二代红卫兵,并有会晤记录。陈伯达就曾被直接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递上一份给他,他当时读得入了神,直到别人提醒他,请他回去再读。另一次会晤时,人们再问到他的看法,他就圆滑地回答说:“太长了,没时间看。”
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曾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说他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我本人也曾混入人民大会堂一次与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亲身递交了一套文革报。
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在1967年4月13日的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文革报,报纸的出版到此画上了句号。此前除第一期到第六期正刊外,还影印了第一期一万五千份,出特刊约六万份。
遇罗克其人
我在文革报第一期出版时;并不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组成,之后到罗文家造访,与罗克首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克与罗文几无相像,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一副圈圈重重的眼镜,扇风耳,严重驼背,可谓其貌不扬。但他的魅力在动态之中。一张口,声音宏亮,语言爽朗,妙趣横生,就连眼睛也能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犀利的光芒。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了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爽朗地大笑起来。之后的交谈,顿时使我感到他绝非一般人物,并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
第二期文革报出版后,我和他的交往渐深,他向我说明了他即是《出身论》作者的真相。基于当时的情势,他请我绝对保密。所以我们报纸的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正式地被告知小组的组成。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晰晰可辨。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泥而不染,不落时套,自成一统。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罗克的写作速度亦是惊人。我们当时的出版困难重重,事先不知下一期出版的日期。罗克讲,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便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各期发表的所有长文,便都是这样一夜交稿的。
罗克并不是一个书痴,他的小脑十分敏捷。和我玩一种拍手的游戏,他总能把我的手打得噼啪乱响。下象棋能同时暗对两局。我曾试着捉弄他,声称他所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便坚定地声称我所说不实。
罗克自己住在正房与院墙之间搭成的一个窄窄的小屋中,北京的严冬之日亦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这“冰窖”之中对坐,夜谈至天近拂晓。他的兴趣广泛,他与我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不是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罗克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当我提到自己1966年5月写过批判姚文元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说他是不会在那时发表那样的文章的。他向我出示了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出交稿日期是在1966年初。他自己则在当年3月就已看出此场辩论的政治背景,因而认定从学术上去探讨只能招祸至身。
罗克是一个很机敏的人。1967年夏天在一同去东北的火车上,他曾被一个面露凶气的人间到:“你还认识我吗?”在不知来由的情况下,他给了一个巧妙而最有余地的回答:“我看你面熟。”
蒯大富曾经对我们的报纸人员讲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可惜蒯从未应战。罗克对自己的口才是自信的。
罗克是在不断思索的。他曾与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我与他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之后多年的建筑,还不能与日本短期内在其领土之外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之后,罗克开始了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了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建设性地提出了工资政策的方案。可惜此文当时已无处可载,他被捕之后不知下落。他更进一步地观察了当时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汉是罗文的同学、好友,也是报社里唯一的大学生成员,曾讲过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中国十年之后的体制改革如能有罗克的参与,将不知获益多少。
罗克对毛泽东并非一概否定。罗克作为一个造诣颇高的古体诗人,对毛泽东的诗词造诣由衷钦佩,特别喜欢的是《蝶恋花》一词。他在临被捕之前,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长信,嘱托我在将来形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此信由我屡屡更改藏匿地点,但赴外地插队多年之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罗克的在天之灵。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我和我的同学王建复。四中语文老师毛宪文向我传授的编辑知识,使我受益匪浅。文革报的各期版面选字大方、美观,毛老师的作用不可抹煞。王建复是一个在“红八月”中大喊过
“对联”的人,大串连时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回京后,我在四中成了一个困难时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建复又成了我的一个忠实追随者。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也就成了报纸的元老成员。
陆续加入我们报纸的,还有罗克的多年好友、轻工业学院的郝汉(当时化名马列),气象学校的两位女学生李金环和王亚琴,二十五中的遇罗勉,男十三中的帖汉、阎世钧,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院的顾雷,二十五中的王嘉材、陈XX,女五中的张X、王XX,女十二中的张君若和张富英。
郝汉高个子,一张非常长的有喜剧效果的脸。取名马列,是因为别人不可予以打倒。在开会时以年长智深的姿态,时常对我的决策提出几分嘲讽。
李金环、王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工作艰苦,繁重,却毫无抱怨。
帖汉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一个汉人,然而他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的学生,他却显示了特有的稳重和才能。他是报社成员里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
阎世钧出身革干,为人憨厚,为报纸的各项事务跑前跑后,总是一副笑脸。
韩基山社交广泛,带有一分江湖气。他加入后,我一到会场,他每每大喊“司令到”。在被冲击的危急时刻,他不无认真地对我讲,“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卖报、联络和其他事务中,他都立过汗马功劳。
四中的赵京兴、刘力前因一篇我们选用的文章,深受罗克的赏识,力主邀请加入。不想在第五期加入,第六期就倒戈,给报纸带来不小的损失。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首都兵团曾派了一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我第一次见面就起了疑心,但罗文却极力推荐。之后,不仅我,其他的报纸成员也本能地感觉此人可疑,终于搞清其身份,随之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也博得大家一笑。
十年后的1978年,我召集大家重聚时,才知大多数非中学生的成员后均遭到校方的监禁,包括郝汉、李金环和王亚琴。罗文虽是中学生,亦未幸免。他后来与报纸的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生活困难,以至于不得不卖掉了出生的孩子。
报社的成员中另有两位后来成婚,即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和四中的赵京兴,演出了一场众人难忘的罗曼史,在此不谈。
我的两个小学同学、男三中的朱大年与京工附中的刘姜仁,也因为他们的报纸(《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与我们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至少刘姜仁曾被长期在校监禁。
报纸第三期出版时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以后,我曾陷入激烈的思想矛盾,几天不在报社露面。再度召集会议时,我向所有成员传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前途的危险,并请求对牺牲无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我不能忘记的是,没有一个人畏退。十三年后的1980年,在遇罗克平反的前夕,我再度召集部分成员相聚时,却从不少人嘴里听到了对当时之冒失的懊恼,使我惘然。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忘记文革报的成员当时所显示的勇气和之后付出的沉重代价。
遇罗克之冤案
遇罗克在1967年底被捕之后,曾被判刑十五年。罗克拒在判刑书上签字,不想忽然改判为死刑。
我记得在判决书里,其死刑的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只字未提。我不禁对“文革”当局懦弱和无耻的程度感到吃惊和愤怒。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1967年夏,东北武斗正盛之际,文革报的成员大部分一同北上,观一究竟。一路风险重重,不少人几乎丧掉性命。到长春时,在车站就发武器,站台上、草席堆下全是武斗中刚死的人。几天逗留中,饱观炮火纷飞。临别长春,我嘱大家将武器退还,以免给报纸落下话柄。
一年后有关当局在对我的审查中,一开始兴趣集中于罗克的“反动”言论,但忽然转向为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的下落。我对此确实一无所知,他们也就失去了对我的兴趣。数年后才得知,罗文并没有退还长春领到的手榴弹,反而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一个喜好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他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恶作剧地在我家撒下了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还给报纸的成员表演过火箭发射,其中的火药想必是从手榴弹中拆下来的。
手榴弹私下带回也罢,罗文却在风声正紧之时,联络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在香山埋藏。当局一恐吓,有人就将这一过程供出了。有关当局曾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这一切的幕后人,我当时不理解,直到见了罗克的判决书,才知有关当局当时的企图。
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个个聪敏过人,但有时又愚钝异常。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罗锦竟把它藏于中山公园公厕。罗克、罗文推荐人报的人,无一不走向了对立面。罗文从东北携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等,就是一些明显的例子。
反过来说,当时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出于愚蠢的推理,而是出于懦弱的陷害。我对罗文的痴呆应有包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划破夜幕的殒星》一文之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或转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可悲的是,文章的按语再次混淆出身与成分的概念,显示出对遇罗克《出身论》的基本理论都缺乏了解。
出身问题在中国大陆的严重性直到今天并未消逝。一方面,出身不同的人受教育的权利是被承认了;但在另一方面,某些出身带来的特权则被制度化和物质化了。当年老兵与造反派分手时,其中一位讲过,今后我们拿枪,你们拿笔,看谁斗得过谁。此话确存几分远见。现在我的同学,高干出身的大多为高干,知识分子子弟大多为知识分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论》的精辟抵挡不住社会的现实。罗克如在世,相信会写下一部崭新的《出身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