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业三掌门 对自己说我

对话人:新华信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民
北京标准咨询公司总经理 刘纪鹏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王璞
主持人:本刊记者 李岷
摄影:本刊记者 刘奔
派力营销老总屈云波去科龙作副总,有局外者不明白科龙为何请了个“光说不练”的。但业内人都很清楚,咨询界是职业经理人市场相当重要的一块。目前,屈云波能否“舞”活科龙还未可知,但屈云波明确表明:“即使我失败了,也是因为我个人和科龙没有磨合好,不是这条路走不得。”
可见,国人、乃至企业家对咨询业仍有相当的隔膜,不少人一提起咨询便想起策划、便想起何阳。
但就在隔膜和被误解中,中国本土咨询业已走到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有一些新信息陆续冒了出来,比如新华信兼并南洋林德,完成了中国咨询业中第一起兼并案。
一年以前,本刊曾报道过外国大咨询公司的本土化进程,今天把眼光向内,发现其实本土咨询公司的发展更应受到我们的关注和推动。基于此,我们请到了三家本土咨询公司,新华信、北京标准、北大纵横的老总,就他们关心、也应是中国企业家感兴趣的咨询业话题作了一次漫谈。
这三家咨询公司的背景特点、客户对象、咨询内容都有相当差异性和代表性,新华信是民营合伙制,核心能力在传统管理咨询上,标准公司在产权改制、融资、资本运作上有深厚实力,北大纵横则有浓厚的学院背景。
三位老总的第一个话题很自然地落到“什么单子最赚钱”、咨询业的“钱”景上,这恰恰也在告诉企业家,咨询公司能为你们做什么——
咨询业“钱”景:融合投资银行业务

王璞:我们对自己业务有两块划分,一块是传统的管理咨询,比如战略、市场、市场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另外一块是投资银行,从破产到融资、并购。目前后一块更容易被企业接受。前一块市场虽然已经启动,但和投资银行业务比,单子还是相对小。
赵民:我们也在发展投资银行业务这一块。因为传统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联系相当紧密,企业要上市,做IPO,一定要先做管理咨询。从前我们与投资银行中银国际有过战略同盟关系,我们一起做过两个项目,就是我们做完企业的管理咨询后他们接着做投资银行业务。但现在我们希望本身也拥有投资银行业务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通过购并来进入——新华信4月1号正式与温元凯教授的南洋林德投资咨询公司签订了购并协议,两家在业务上开始交叉。此外,现在还有一块比较大的是做大学生创业和风险投资项目、比较热的B2B,传统的网下业务转到网上去,这一块也是管理咨询业务和融资、投资银行业务合在一块的。
王璞:北大纵横的优势在于传统咨询项目的理论基础雄厚,同时由于依托北大管院,在培训项目上有较大优势,为什么还要进入投资银行咨询?因为这个市场目前的确很大,尤其最近两三年。现在做管理咨询业务往往做到最后与投资银行业务不交叉是不行的。因为帮一个企业做战略,做完战略以后就要考虑资本投入,如果没有为企业找到一个很好的资本出口,你这个方案落实不了,企业的市场表现也不会好。所以就涉及到了另一块业务,帮助企业寻找融资的通道。我们常常在帮企业做完战略后,还帮它做融资报告,包括商业模式、市场、潜在机会、利润来源。企业要吸引风险投资基金也好、海外投资也好、以至国内大企业集团来兼并它也好,都必须要有这份融资报告。更进一步,由于我们和投资银行的联系很紧密,是松散型的战略联盟,如果合适,企业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融资通道直接和投资银行接触。以上的工作是递进的、或者说是相互关联的。顺序反过来的情况也有,有的一开始提出融资,但在做融资过程中,又要帮他做融资报告、又要帮他选择项目。
赵民:现在资本运作成了管理咨询中收益最大的一块,把业务面从原来的管理咨询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也好,扩展到二板上市也好,扩展到创业管理咨询风险基金也好,都是管理咨询客户需求价值链上的一个横向延伸。
刘纪鹏:我们的业务确实在适当沿着投资银行拓展。我们特别费劲地在前期做一个方案,挣了几十万元钱,做好方案给了投资银行,投资银行进来一个承销,一千多万,或者几百万美元就收走了。这给我两点启示,一是业务要适当向投资银行拓展,一是收费可能也要从单一的现金到股权或期权。
其实资本运作不仅是管理手段,也是经营方式,反过来说也行。像债转股,必须从研究公司的内设机构入手。所以可想而知,这个领域很大。
几乎每个企业在选择咨询公司时都有过这样的困惑:是请国际大公司,还是请国内公司?那三位老总如何看待自己与麦肯锡们的优劣势?——
本土咨询公司能做过麦肯锡吗?

赵民:我们业务向投资银行拓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只做经典管理咨询,怎么也做不过麦肯锡、安达信这些巨无霸。到去年年底,全球咨询市场是970亿美元,如果把跨国公司的业务放进来,中国可能占1%以上的全球份额,如果单算我们这些本土公司,肯定超不过1亿美金,就是千分之一,然后我们这么多公司在这千分之一里分羹……如果你的人员规模达不到50个人,那你的营业额达到100万美元是很难的。要做经典管理咨询,和巨无霸走同一条道路,是很难的,虽然麦肯锡、科尔尼等在工业时代的增长率没我们现在高。但是他已经走过来了,形成了市场垄断,我后发展,追赶的难度很大。所以这时候做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这一块就成了我们为求快速发展的一个现实选择。
刘纪鹏:这一点我一定要给你鼓气,据我了解,国外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道路也非常曲折。麦肯锡做的几个大项目大家都反映失败了。现在中国企业的情况不是你把全世界的行业专家请过来就能做的。国家电力公司听了安达信讲了一次之后,说的话非常难听:“你们不要再讲了,你们要这样下去,这个项目是肯定失败了。你们讲话、写的文章能不能通俗一点,形成我们中国人看的文字?不要3个字加一张图,就完了,往投影仪一放,就值95万美金。”国外公司如果不调整自己思路,适应中国企业特点,那么他们的收费市场一样打不开。现在德勤在中国咨询这一块有100多人,但也是收不上钱来,只占1亿多收入的百分之十几,还是审计和税务这两块多一些。所以目前国外同行比我们更艰难。我们可说是薄利多销,而国外公司如费用少了根本接不下来,它一个专家从美国来一趟费用就得多少钱?
最近中铁12局非得让我出个上市的四字简称,又要叫公司,还要保留局,什么都不能丢,所以中国咨询业非常有意思,你必须得对中国企业相当认知。老外欠缺语言和文化上的沟通,找不到感觉的。我们企业家的心态,一定是我们这样的人才能了解,一个眼神都知道他在想什么。外国咨询公司,特别在与制度性相联的咨询领域中,将来一定落在中国公司后面。
还有他们的付费方式。当年麦肯锡为“今日”做项目,安达信为沈阳“和光”做项目,媒体都报道很多。其实有些企业就是为了追求一种“荣誉感”,“我请了一个什么什么”,这些企业都把品牌看得非常重,先弄一个品牌猛吹。国外咨询公司也需要这个,“你看,已经有中国企业请我,花了多少多少钱”。但是在他们协议背后——据说,有的还不是据说——我看过一个合同附本,咨询公司收一千万之后还要返还六七百万甚至七八百万的人员培训费。这就属于咨询业背后的东西了。找“标准”的企业从没有使劲吹“我经过标准咨询”,他们一定要实实在在的方案。
麦肯锡们为什么没有打开这个市场,有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管理咨询公司也在发展,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从长远看,这个对手会越来越大。但我的含义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市场,我们没法跟他到中国以外的市场去比。
王璞:我们为吸引人才用了很多办法,如薪酬、合伙人、事业感,麦肯锡也会面临人才问题,也在调整以适应中国市场。举个简单例子,它当年招本科生工资不到一万元钱,相当于实习生,而它在国外没有这个层级,进来就是助理。但它现在取消了这个层级,刚进来的毕业生一进来就是上万了。
赵民:但我认为规模问题不解决,最终很难在一个层面上与外国大公司竞争。现在我们和他们的目标市场层次不一样,因为这种差异性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很好地共存,你能做的他做不了,他能做的,你做不到,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发展大了,总会和他头跟头、脚跟脚争夺同一客户群体,所以这时候公司的规模就显得重要了。
看看咨询公司合伙人的数量,也可以了解国内咨询业发展程度。美国大的咨询公司主要就是合伙人制。这是一个制度安排。国外的管理咨询公司是个有机的生命载体,麦肯锡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这个公司名字还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500个合伙人个个都很优秀,能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制度下友好共处,这恰恰是我们欠缺的。
咨询业是实业的衍生品,它的发育度与市场环境及该市场中企业的成熟度成正比。三位老总说“土壤”问题——
什么在制约咨询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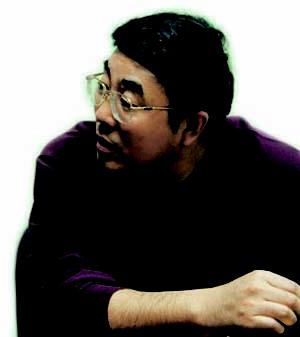
刘纪鹏:观念问题仍是制约中国咨询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对咨询业不够重视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及咨询业本身作出的贡献大小分不开的。这里我还想强调,业内人士的观念,也必须要跟上。中国咨询业是个被迫发展起来的产业,我办公司就是被迫的,从来就没有特别主动地要把它做大,前期是抱着“我要写出好文章、了解实际”这样一个朴素的感情把它做起来的。从前我做研究员时帮别人做一个大项目,最后拎回来的也许就是几瓶酒、甚至几条鱼。我收的第一笔钱是1992年和高西庆一块收的,做了天津一个大集团的上市方案后,他说你提钱,我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怎么不提钱,后来才提了4万。现在我提钱也不脸红了,这次国家电力公司项目的咨询费是400万。从4万到400万,这是一个特别曲折的过程。但回过头来说,这400万也不是我开的价,是人家开口就给我这么多,我应下来的。
赵民: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羞于谈钱,我们一开始的服务对象就是外商,就是高收费。所以我们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不把管理咨询当作产业来做,那就是学校教授和研究员做项目的层次。咨询服务要卖得专业,收费高、利润高,这样来达到它的良性循环。
我感觉有三个制约因素。一是国内MBA供应制约。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粗略的估计,国内一个MBA有5个工作可选,相当一部分MBA会流到其它行业里。在国际上,网络公司出来之前,全美前25所最大的商学院的1/3 MBA毕业后到咨询公司。在中国就不可能做到。而且MBA的质量也不能保证。
第二是国内大企业发展的规模。国际咨询公司收入和跨国大公司咨询费支出是有关系的,美国大咨询公司背后支撑他的是500家大公司。美国500大公司每家都雇了好多咨询公司在帮它做,它们每年的预算都有专门的咨询费。而国内电子行业第一的联想年销售额才200亿人民币,有能力请咨询公司的大公司比较少,一般中等企业资产规模在几千万到几亿元,他们的咨询规模可想而知。
第三就是我国咨询业还没形成垄断的产业结构。像家电行业已由多家公司走向垄断。咨询业现在还是春秋战国,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过渡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开始。外国咨询大公司早进入资本运作,所以可以加速度发展。这次我们和南洋林德的合并也不是购买关系,而是合伙人的资源合并。
王璞:目前市场有两点不配合。第一,咨询公司的社会地位还不够高。你看现在IT业宏观配合以后,资金、人才都流向它那去了。国外的商科学生往往把咨询公司当作通往大公司的一个必经的跳板,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就走,中国很多优秀人才没有这种意识。
第二,我们希望做一种制度安排来吸引人才,比如合伙制,但是中国现在没有相应的政策、法律给予必要的支持,制度创新不容易。比如在中国,有限责任制的退出机制靠什么保证,假如我们两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一旦我不满意了,要退出的话,这个议案由什么来决定,由股权决定呢,还是由合伙制一些本质的东西来决定。现在按照中国现有法律很难做。特别是我们是由北大完全控股,变通力度更小。我想知道新华信的合伙制是怎么做的?
赵民:你可以将公司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在内部签订合伙人协议,在公司章程上规定,如果你要离开,你的股份怎么处理,比如要优先卖给其他合伙人;如果合伙人退休了,那么会按一定算法给他退休金,而他的股份必须转让给新进来的,或者由公司收购,以后再卖给新合伙人。另外,公司的文化是很关键的。
刘纪鹏:这提到了中国咨询业产权解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到底是要走合伙制,还是走有限公司制,甚至今后上市的路?你整个责任是你个人以合伙的身份履行,还是你公司以有限责任身份履行?也许以后“标准”也要考虑是走私人公司的路子,还是走一个公众公司的路子。这样说起来,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的结合可能促进中国咨询业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