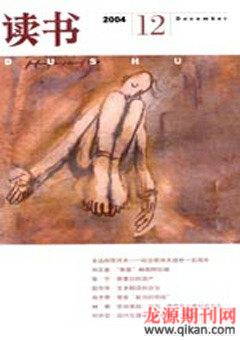我这十年的权利思考
夏 勇
著译者言
这本书起名《中国民权哲学》,是要表示,它既是关于中国的,也是中国的。编写这本书,有农民工拉车爬坡时步履维艰的痛沉,也有建筑师精心绘制蓝图时踌躇满志的愉悦。一九九二年,《人权概念起源》出版后,我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接地气”。在乡村行走,与乡民接触和交谈,的确使我这个自幼长于农村但离去甚久的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并增添了前行的力量。
在中国,“农村”既是个地域概念,又是个政治概念。“农民”既是职业身份,又是政策身份。农村和农民是国家最坚实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从人口的比例,还是从苦难的程度,我们都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当是乡民的权利;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当是农人的人权。我觉得,正是与城乡二元格局相适应的明显不平等的特殊身份,使乡下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和城里人很不相同,并拥有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过程的特殊经验。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乡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这预示着,倘若重新厘清权利义务关系,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把利益保护转化为权利保护,把发家致富、安定祥和的生活意愿凝聚为民主决策、尊重权利、依法办事的政治意愿,乡村就不仅是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策源地,而且还会成为实质性政治改革的策源地。正如我在《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一章开篇所说,这个思路,把我从对农人权利现状的记录和叙述,拉回到对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原理的思考。
那段时间里,我思考较多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同意关于权利是现代法制的“核心”或“基础”的预设,已经同意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动乱、法治不昌的祸根在于治人者有权、治于人者无权的解释,还同意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能够享受最广泛的民主、最真实的权利,那么,在权利观念空前兴盛的最近一百多年里,尤其是辛亥革命“立宪”、“共和”以后,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在面对强权的时候还是那么束手无策、虚弱无助?他们怎样才能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真正享有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他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权利的?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公民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过去由党和政府保护得好好的利益,现在却遭受侵害,过去不曾有过的权利要求现在却提了出来,而且越来越高涨?民众的权利要求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法律支持和文化支持吗?进一步,为什么最近一百多年来,权利在中国成了一个流行的术语?为什么中国社会在古代并没有强烈的个人权利要求,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标示“民主”、“自由”等字样的多次革命取得成功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要求反而越来越高涨?难道这是可以简单地用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谓“现代化”来解释的吗?如果说权利的语词及其相关联的制度设计初创于西方文化,难道中国人对权利的要求也出自西方文化不成?……带着这些问题,我把关注点放在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解释,尤其是试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构建解释权利发展的理论框架,进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权利意识和保护机制的变迁,并试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这个努力,体现在我和朋友们合作编写,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一书。及至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秋在查尔斯河畔的小阁楼里潜心读书和写作,看新书,修新课,遇新知,寻新理,我的思考又有了一些变化。例如,接触有权利斗争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居民,参与他们的多种社区活动,使我对西方人权利背后的社区、宗教、道德和制度因素更为关注。当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对这些人的前辈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感触有两点:其一,这些普通的居民其实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人权以及中国人了解更少。他们通常没有出国的机会,也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出国,有限的新闻媒体似乎是他们了解和判断外界是非、臧否人物、表达情感的主要渠道,所以,大多数人难免染有知寡而言多、强词而夺理的毛病。有时候,我想,倘若美国的霸权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真是十分危险的;其二,这些人在文化、学术意义上的预设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有着很大差异。在经典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如霍布斯、洛克的学说里,他们被预设为与他人没有积极关系的单纯的个体。在像我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那里,他们也向来仅仅被预设为典型的、纯粹的个人权利主体,预设为权利文化的代表者、个人自由的张扬者。实际上,他们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和社群观念。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主要是社区活动、宗教活动;各式各样的法律把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制度化、程序化了;违法犯罪虽然千奇百怪,但并非常态,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理解为对铁定秩序的反抗。权利是他们很少使用的物什,只是在制度上可以保证作为最后的诉诸手段。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说他们是“孤独的权利持有者”,似乎有些夸大了。
在《权利与德性》一文中,我似乎又回到权利的本原问题。不过,我已不再把关注点放在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意识到了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来建设性地提炼、融合或转化中国文化里的权利要素,以中国人的话语加入到当代世界的权利哲学对话里。在做出这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识别中国文化的个性,也要识别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性,既要交流,也要汇流,即,既要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主导思潮汇流,也与之有效地交流。
这个时候,我的思考范围还从编写《走向权利的时代》时对公民权利危机的忧虑伸展到对公民道德危机的关注。我逐渐认识到,对一个健全的人类生活和健全的社会制度来讲,对个人尊严的信仰和对社会责任的信仰是不应该分离的,也是不可分离的;应该更多地从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角度,来强调对民主和人权的道德承担,强调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强调关于妥协与中和的政治意愿;应该努力锻造一种德性,一种新德性。
于是,我提出“德性权利”概念,并以政治参与问题作为案例,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哲学和经验素材等视角多维度地阐释这个概念。德性权利论本身,标志着我不再像写乡民权利的文章时那样,把利益个别化和个别化利益的增长,作为叙述和解释当代中国人权利生长的不二法门。我开始从人的道德资格和意志的角度来研究权利,并由此开出一片权利的文化解释空间。在我看来,强调德性并不必然导致贬低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提升个人权利也并非必然削弱对集体利益的道德关怀。当代中国道德话语的枯竭,既导因于传统价值和学问的衰落,也导因于“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的附带结果,因为在这种模式里,德性遭到滥用。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政治道德化,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道德价值政治化,应当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既是德性的践履,又是权利的实行。
一九九九年写成的《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代表着我对人权的比较成熟的思考。我把人权称作“和女士”,既是取“human rights”(人权)的拼音字头,更重要的,是取“harmony”(和谐)的拼音字头,意在表示人权对人类和谐、人类大同(Great Harmony)的重要意义。称“女士”,乃是为了强调人权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所不可须臾离弃的,犹如阴阳之并存相济。同时,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人权之于民主、科学,还有本原的、母体的意蕴。在我看来,儒家的“仁”和康德的人道原则一样,都需要权利作为实践工具。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做的,就不是对“仁”本身大加挞伐,而是冷静、细致地设计为“仁”所要求的制度框架,从而让儒学在现时代具有从容大度的开放性。人权原则之所以可以使仁“必如是”,乃是因为它把同等数量和质量的权利赋予了每个人,同时,借助权利语言,人道主义的价值法则不仅得以转化为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而且得以转化为体现制度理性的程序法则。这样一来,作为平等的、自治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有权来亲自体认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价值;通过界定自己与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一方由自己自主自为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权利语言设立人民与政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制度和程序,每个人相互之间又可以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再被看作孤立的、分散的个人。由此,我认为,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向民权思想转化的过程中,这种关于权利的预设起到了关键作用。若没有权利观念作为支撑,便不能理解民主、主张民主,更遑论实行民主了。在此意义上,没有和女士,德先生是没法存活的。人权之于民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民主提供动力和基础,还在于保证民主不出偏差,如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正如民主需要人权来引导和限制那样,科学也需要人权来引导和限制,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战争一类恶行的时候。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讨论人权在中国的文化基础时,我认为,人权之所以是与生俱来的,乃是因为作为人权内容的人之作为人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例如,乡民们在一份正式的问卷面前可能会回答“人权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或“不懂人权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且是不可侵犯的(如生命、身体和自家祖传的房屋),却是一清二楚的。这是一种不依赖法律和政府而存在的规则和信念,一种关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规则和信念。所以,我强调,“和女士属于全人类。不过,在中国,她应该会讲中国话”。
最近几年来,我的权利思考的最大变化,是结构感、整体感有所增强。正是这种增强,引导我把十年来关于权利的写作编成具有内在逻辑的九章,并冠以《中国民权哲学》。显然,这种结构感已经不仅仅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权利的内部结构分析,更多的是关于权利与其他事物之关系的一种结构性把握。恩格斯说过,权利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这个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当然,权利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权利应当进入到结构中去,成为理想的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结构里,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他的德性或道德能力;每个人的意愿和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便都是重要的,都可以免受社会里其他个人和组织的漠视或践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消极关系,而是互相关爱、同舟共济的积极关系。这是一个人人共享的公民社会,每个人都努力去培养为自治所必需的个性和品质,并因此不断加强对社群的归属感。自由绝不仅仅停留在“不受拘束”的层面上,而是要通过个人对社群的完全参与表现出来的。自由的个人在社群生活里随时调整个体行为的能力,体现着个人自治的精髓。社会公共权力,无论对社会正义,还是对个人自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这样,我终于理解并赞同罗尔斯所说的“正义的结构”或“结构性的正义”。的确,如果事先没有资源的公平分配,公民权利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够适当地克制某些人的某些权利,社会弱势群体的状况便会江河日下。没有分配的正义,便没有有效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的价值要高于权利的价值。效率绝对不能优先于公平。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平等权利,不可能存在任何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
当然,这不意味着又要“打土豪,分田地”。我心里想的,是要铸造一个坚固、合理而又和谐的制度结构。这个制度结构,既是一个道德的结构,也是一个法律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正义的旋律,乃是道德大厦里的每一个有尊严和自由的人用权利与责任的音符循着法治的规则而奏出的天籁之声。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因维护尊严和自由之需,都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遇有不同主体的相同权利或不同权利的冲突,可按社会正义原则适当克减某些权利,并配合以某种补救或补偿,但不得从根本上否定任何一种权利。
这是我对权利的一种新理解,也是对中国要坚持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理解。西方有些学者根据我的权利观和法治观,认我为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ist)。其实,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识别。我只是认为,不能就权利谈权利。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权利话语就会像一本只有词汇和词组而没有语法和句法的书。当然,只有语法和句法而没有词汇和词组,也是可怕的,难以想像的。
还有另一层或许更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德沃金、罗尔斯那样的西方学问家不去想的。这就是,在中国的文化结构里,权利观念是如何生发出来的?如果说中国文化不是故纸堆,而是一道生命的活水,还在奔淌流转,中国的儒学之道还生生不息,那么,作为她的传人,我们如何去继承、改造和发展,就像包括罗尔斯在内的一代代西方学者总是在不断的批评和争论中继承、修正或改造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那样?这个问题引领我大胆改造或转化传统的民本学说,通过阐发中国思想里的民权因素,借用现代权利理论,把以民为本的民本论转变为民之所本的民本论,把他本的民本论转变为自本的民本论,把以民为手段的民本论转变为以民为目的的民本论,同时,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建构,借助民之本体建构来支撑民权的价值证立和政治实践,并由此而倡导一种同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呼应的新的民本学说。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把先秦以来的相关思想的历史脉络做了初步的梳理,提出了关于民权的政治浪漫主义、文化怀疑主义和制度规范主义的区分及其关系的见解,还着重批评了文化怀疑主义和相应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
对整体性、结构性问题的关注,还令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研究法治、宪法和司法改革问题,并试图把享受法治、建立宪政、获得司法正义,都解释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种对特定的制度安排所享有的权利,一种享有权利的权利。
权利思考的结构感、整体感增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因于从一九九二年到现在,我和同事们时常参加我国关于人权的立法、司法和外交的决策研究,并参与国际人权对话与交流。我深切感受到,在许多国际人权斗争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战略利益,甚至是某些政治派别的私利,而且,即便是在人权学术研讨的场合,也常常充斥以西方文化霸权为支撑的浅薄与无聊。当然,这绝对不能归咎于人权原则本身,尽管当代人权概念和制度本身还存在许多的缺陷。人权得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成为幌子、借口或工具,这个现象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当今世界,作为一种旨在借助权利语言和机制来维护弱势者、受压迫者的尊严和自由的普遍道德权利,人权在价值认受上已然无人敢于公开反对,在制度设计上已然成为普通法。就像古代罗马法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普通法时的情形,你可以依然维护或适用日耳曼法、教会法或其他的法律,但是,在私人经济交往和私法教育领域,你不能不尊重罗马法权威,不能不使用罗马法规则。同样,在文化丰富多彩、国情千差万别的当代世界,你可以依然维护或适用伊斯兰教规、天主教戒律或其他的法则,但是,在涉及政府与公民、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领域,你不能不尊重人权原则,不能不适用人权约法。
这类感受引领我认真考虑一些在过去似乎从不考虑的问题,例如,一个政府要实行良好的治理,究竟应当如何回应来自社会大众的人权要求?如何识别和表述人权要求?如何使用可得到的制度资源和非制度资源来满足人权要求?一个国家在不遗余力地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的同时,如何不遗余力地维护本国内每一位公民的主权和利益?一个国家要在国际上有地位、受尊重,究竟应当如何承担和履行关于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如何既对自己的人民负起责任、又对国际社会负起责任?如何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人权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价值共识与文化差异之间、理想目标与现实步骤之间、国际义务与国家利益之间以及反对霸权与增进合作之间,谋求一种恰当、有益而美妙的平衡?
这类思考和实践使我更加坚信,任何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在权利问题上都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充分地享有权利、妥善地保障权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众多的权利主体在人格尊严上的深刻自觉、在社会道德上的互敬互信、在制度运作上的积极行动。同时,也是这样的思考,使我倾向于从政治上把权利看作民之所本,开始为打通民本思想与权利思想做一些理论尝试。我坚信,一个国家的最高福祉,不在财富与秩序,而在美德与自由。只有每一位国民都尽可能地秉持内心的高贵,享有行动的自由,成为道德上仁义、经济上富足、政治上自主的健康、活跃的分子,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盛并受人尊重,财富与秩序也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设定每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人格、身体、财产、行为等拥有权利并通过法律予以平等的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总的说来,这本书是最近十年来我琢磨权利问题的一个结果。算不上“十年一剑”,嗟可曰“十年一砖”。此砖灰头土脸,但烧得还算牢实。若不为风雨所蚀,聊慰平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