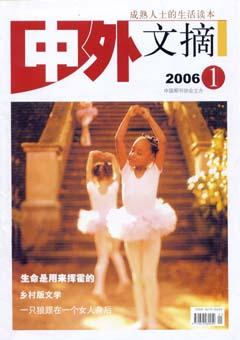燕京女子
陈哈林
她现在不再谈人生,谈七谈八了。她只说活着真好
阿萍至今还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奇迹了,这不是用普通的生命观可以解释得通的一件事!
阿萍从小失去母亲,因而知事很早,不论在家里还是后来上学都被公认为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某一天午后,她突然认为学校的老师都是些骗子,她认为社会太黑暗而老师总是说得太理想化,直到遇上我,那时我在一所县级高级中学教书,英语老师。时常喜欢写些文章到外面贩一贩以赚点烟钱饭钱什么的,那时候的我正处在意气风发的年龄段,在一些课堂上,常给学生讲一些学校与社会的事儿,比如怎样看社会,要学生拥有一些眼睛,什么孙悟空的眼睛,包公的眼睛,乞丐的眼睛,上帝的眼睛,儿童的眼睛,强盗的眼睛,囚犯的眼睛等,就是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观察社会,社会除了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学生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听了我读解的这些书理,认为我是个实话实说之人,因而对我增加了些信任,有些女生就开始在作业本儿里给我上纸条儿,有的是争辩与探讨,有的是佩服与认同,还有的是一种十多岁的小娃娃萌发的初恋情怀,我将这些分门别类后放人了我的教学问题研究的小盒里了。还有一次我又给学生谈上了《丑陋的中国人》、《山坳上的中国》等书,学生们慢慢儿在这些学习中开始认识咱们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了。那些试问上帝能否制造一块他所搬不动的大石头,比如说人是什么,为了什么?人民是什么?祖国又是什么?当我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开始意识到了一些危险性,但我不知道危险性又在哪里,只是觉得这样,自己则在教学日记中记到,给了学生一些逆向看问题的方法,开发了智力,纠正了视听。
这事儿也就来了,阿萍儿突然有一天在练习本儿中递给我一张条后就回家不上学了,那张纸条上写着些人生的1/0,人生是一条射线,人生是一个看不见底的黑洞……陈老师,你是我最信赖的朋友和哥哥,我爱你,但我不想活了。见了这留言,我和我的朋友迅速赶到了她家,那个时候,她已绝食三天了。她的70岁的老父亲已方寸大乱,这是他的断肠儿呀也就是幺儿,17岁便不想活了,我们一方面安慰阿萍的父亲,又一方面做开了阿萍的工作。我面对她直奔主题,既然有爱,而且爱老师,那就把爱进行到底呀,她听后似有所动,向我投来了怀疑的目光。我说是的,她的目光依旧是探寻式的。只要你读好书而后上大学,老师我就陪伴你呀,你说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最终是个哲学问题呀,人就是这么不断产生于尘土,又消失于尘土,这有什么值得劳神的,否则,古人不死,我们这个地球怎么能容得下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人生就在于它的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要去品的,比方说学习、成长、爱情等,你都还不解其中味呀。就这样阿萍一跃而起,说:“我不死了,我上学去,好好地品尝人生百味去。”
上学后,我将阿萍安排到了英语听说训练组,不让她有任何闲工夫,六年后她以十分好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这下该好了吧,到了皇城,我们都为她祝福,也的确,她每次从首都给我们捎来她品尝人生的好消息,她时常向我要一些我的作品看,她说这世上只有我的作品写的是真的,是令她喜欢和崇拜的,弄得我也不知怎么对待好,总是给她回信写稿谈感受。萍一次放暑假回来,那个时候我已不教书了,在一个小县城的行政部门谋上了一份儿活儿,阿萍回来就到了我的办公室和我亲吻拥抱起来,弄得那老主任我的上司目瞪口呆的,随后咳嗽一声便好心地为我们关上门出去了。为此事我入党的事又拖一年半,因为支部组织委员听说此事后认为我的作风问题有待考察。也是,那段时间阿萍就住到我家去了,我的二弟刚好和她是同学,便认为阿萍肯定要做嫂嫂了。那些天,阿萍就吃住在我家,尤其是到了晚上,她一直陪着我在单位分给我的两居室的套房里,那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一位住隔壁的同事常在夜半击墙警告,那时我跟阿萍每天都睡着一张床,连我母亲都担心她儿子我会出事儿,总找些理由到我的那间小屋子里光顾,其实我们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在那年暑期阿萍要返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在我们的师生男女关系上有所发展,那种记忆给了我们双方永久的生命记忆。那天,阿萍哭了,她哭着对我说,今生今世,我永远有你,无论是否有嫁,做哥们儿吧,我对她说:萍萍,就做哥们儿吧,她紧咬我一口,就返回北京了。之后就是信去信来的。当春绽枝头,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阿萍给我寄来了她在哈尔滨:她同学家的雪原北国的照片,那时的阿萍系着一条红丝巾,像是绽放在北国雪原的雪莲花呢。
于是我就想,或许阿萍找到了她人生的坐标呢。
就在这年的6月,她又给了我一封信,信上说,她对人生彻底绝望,觉得愈走愈黑暗……我接到这封信时是我下乡近一个月返回单位时收到的,就在第二天,她所在的大学系主任打了电话给我,说阿萍失踪了,并有留言说她的消失是她久有的念头;这事儿她高中时的英语老师该明白。于是英语系支部来到了我这里,我同他们交换了三天三夜,他们便有所收获地回去了。系里留下话,她是参加了学潮。
是啊,阿萍去了哪里呢?我失魂落魄了好些日子,后来接到一个不知从哪里打来一个只有一声呼吸的匿名电”话,连喂都没有一声,后来我想,那可能是阿萍。
这一别就是十多年,直到我2001年做了一次肿瘤手术之后的一个秋日明丽的日子,阿萍一下子又出现在北京了,她哭着说,陈老师,你不死,我也不死呢,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你的书,那本书叫《石板街的记忆》,她在电话中说:我要你和你的书,我的哥呀!
这样我便去了北京,那次是因为《中国肿瘤》发了一篇我写的“关于抗癌的十种药”的文章约我参加在上海北京举办的一次座谈会,北京肿瘤医院还为我们几个参-加座谈的病友做了免费检查,当我把这消息告诉阿萍的时候,她就径直奔我住的房间来了,一进房,她便旁若无人地退掉了所有衣裳冲淋浴去了,就那么婀娜地去到了浴室。完了又那么赤条条出来,我给你庆贺来了。我腹膜肿瘤切除后有一段连男人的功能都几乎没了,这一天,阿萍用那活力的身子让我复活了。
唉呀,我还行!
她现在再也不跟我谈人生谈七谈八了。她只说活着真好,北京真好。还有老师哥哥真好,写作真好,原来阿萍在干自由撰稿人呢。
阿萍脱胎换骨了啊,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活力更好?
这篇文章本不叫这个题目的,因为阿萍末了给我送来一本她写的书《燕京女子》,因而借用之。
(摘自《散文百家》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