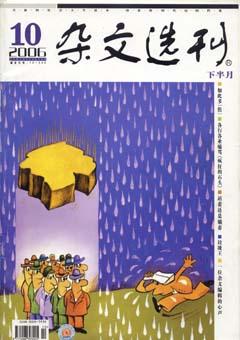一位杂文编辑的心声
朱大路简介
上海人,1947年生。《文汇报》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1965年9月1日进《文汇报》,1987年11月开始编“笔会”杂文专栏。身在新闻阵地,却常常踮起脚跟,想作文学的登攀。1978年起发表杂文、随笔。曾主编《杂文300篇》、《世纪末杂文200篇》。另外,著有长篇小说《上海爷叔》、《三教九流》、《梦断上海》、《末路皇孙》,传记集《上海笑星传奇》,报告文学集《盲流梦》等。
●记者:您作为资深杂文编辑,从事这项工作十八年有余。请谈谈您眼中的“杂文十八年”。
○朱大路:我识见浅陋,只能从“笔会”的角度来扫描。这十八年里,杂文有成长,有兴盛,有衰落。因此,心情有平静,有激动,有惆怅。这期间,杂文有两个繁盛期。第一个,是1987年到1989年上半年,约两年半。当时,思想开放,可写的题材相当多,也好发。一次征文,来稿三千篇,奖品是十辆崭新的自行车,很吸引眼球。第二个,是1996年到1998年上半年,也是两年半。这期间,“笔会”每年发表二百二三十篇杂文,数量空前,质量也可以。刘成信说,每期《杂文选刊》可转载其中的七八篇,但按规定,只转载两篇。我听了,饭量大增。
这十八年,我们为一批杂文家的成长,助过一臂之力。《新杂家专辑》推出的九位,至今早已是杂文界中坚,证明我们眼力不差。这几年发现,杂文人才比演员难觅得多。拿上海来说,刘运辉是新冒出的一个,潜力不小。周泽雄也是能写杂文的,可他偏去写随笔,而且一脸庄严地宣告:对当今杂文有反感。我很想约他写杂文,又怕碰一鼻子灰。
第三次繁盛期何时到来?说不准。好像听到有潮头在涌过来,可又怀疑是自己耳鸣。
●记者:您如何看待杂文的功用?
○朱大路:年近六十,心态越来越平和,所以,我自忖能冷静地看待杂文的功用。
把杂文的功用抬得过高,不符合实际。比如,对孙志刚事件,郎成平、顾雏军之争,杂文最多只能发表看法,提出建议,造一点舆论,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专业知识分子批评的介入,引起了政府关注,才在有关法律上,做出改进。上海有学者写文章,说这是法治进步,是专业化学者的参与显示了力度。这很对。那文章同时还批评了文学型批评“粗放含混”,“因笼统而流于空洞,于事无补”。我“嗅觉”很灵,一下就“嗅”出了这是在批评杂文,认为杂文不如专业化批评那样熟门熟路、药力直奔穴位、“代上苍鸣不平”的活儿做得理性而有效。我想,应把这当成好话来听,用以检点杂文的不足。
但把杂文的功用看得过低,也不符合实际。它的社会批评功能,不能小觑。被批判的恶人、小人读了,血压升高大概是必然的。杂文还重在拨正观念,新时期以来,不少混乱的思想,似是而非的提法,它都争着去澄清,焕发出一种斗士的气息,且日积月累,深化民主观念,推进了制度层面上的变化。有些,还取得直接效应。比如,前些日子,河南陈鲁民的《致癌消息何其多》一文,批评新闻媒体随意发布致癌消息,缺少科学论证,造成社会恐慌。有关部门关注此文,作批示。刹住了这股不正之风。而且,一个社会,批评的模式,是多样的,各具功能,相互不能替代,就像郎咸平和朱铁志不能相互替代。朱铁志是起“晴雨表”的作用,譬如,他指出要警惕老天刮台风下大雨,难道还要他去加固堤坝、落实防涝措施吗?而且,圈外看圈内,有时比圈内看圈内,反而多一份客观。鄢烈山用杂文。呼吁给全国民工每年放二十天探亲假,以解性饥渴,这就比有关专家更急迫、更具人性关怀。二十天呀,时间长短都提出来了,就看法律层面如何来研究了。
对中国今后的杂文,我比乐观者要悲观,比悲观者要乐观。能解决实际问题,最好;不能解决,让人思索思索,也不错。再说,一篇妙文,还有审美功能,比如流沙河的杂文便是,讽刺艺术到了老先生手里,炉火纯青了。我有空,常读。干吗呀?享受审美愉悦呀!
●记者:您认为在现在的杂文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朱大路:一是对“议论”二字有误解,提起笔,就急于把道理端出来,“因为”、“所以”,讲个不停。其实那些道理,我比你懂,你心急慌忙地端道理,就露短了。我要看的是,你展示道理的过程。过程很好看,常常能出彩。有时举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淋漓尽致地介绍出来,也能出彩。
二是面孔太板,没有幽默感。幽默是一种兴奋剂,能让你精神振奋地把文章读完。广西阮直,是添加兴奋剂的高手,他的杂文,以乐写悲,以笑写痛,一路形象到底,一路调侃到底,北方汉子(阮直本是东北人——编者注)的正直豪爽、疾恶如仇,全融化在“冷幽默”的笔调中,很耐读。我想学,就是学不来。还有北京刘齐,人绝对老实,文章绝对调皮,“歪点子”多。刘兄的贡献,是在为中美基金作交流的同时,一举打破了“文如其人”的千古定律。
三是缺少悬念。悬念也是一种兴奋剂,能让你充满好奇地把文章读完。这种悬念,不是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悬念,而是“给鸡喂米”式的悬念。给鸡喂米,不多给;吃完了,给一点,吃完了,给一点,逼得你想读完全篇。
四是写作手段单一,只会写杂文,结果写出的都是时评。如果也写写散文,散文诗,小说,把它们活泼灵动的长处吸收过来。可能会让你的杂文面貌从此改观。
五是产量过多。数量与质量永远矛盾,多了,就不容易好。有的初学写作的人,写稿的速度比我看稿的速度还快,令我佩服;但质量每每过不了关。又使我无奈。如果他们思想上来个“减负”,不以杂文家自居,而以“业余作者”的姿态上阵,会好得多。“业余”心态,可进可退:写出来了,喔唷,业余写作也出成果了!写不出,可以安慰自己,反正是业余的嘛,无所谓。这种心态,会让你从从容容,写出好文章。
●记者:您曾说过:“让被批评者从嘴里和心里接受批评,服输,是知识分子从事批评的重要方面”。请就此谈谈您对文艺批评和现今一些文艺争论的看法。
○朱大路:是的,杂文界,文艺界,争论很多。从事批评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但光有批评,还不够,还只完成了一半,要让人吃到批评之后,口服心服,这样对批评的理解,才算完整。
这一来,对批评和被批评双方,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我想,提升生命的批评,才容易让人服输。
先从张中行说起吧。十年前,他写文章,认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可以走冯道的第三条路。黄裳在“笔会”撰文批评,并以汪精卫和钱谦益在家国危亡之际的表现,说明走第三条路的危害性。话说得很重。当时我猜想:张中行会勃然大怒,写文章反驳。谁知他给“笔会”的一位老编辑写信说:“拙作确有不妥处”,“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至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检讨自己“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视为失误,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会不安然的”。并同意公开发表此信。说实话,我当时被震撼了,对张中行油然生出敬意。后来,我读了他的《顺生论》,才知他研究佛学,修身养性,道行很深。
黄裳和张中行,是高人遏高人——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一方是抱着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这是对“批评”一词的完美演绎。
我作为编辑,经常收到作者批评和反批评的稿子。对问题,争论越多,认识越深入。不少问题,见仁见智,没有明确答案。我们办报人,巴不得你多商榷商榷,好让版面活跃。但是,当对手明显占据了真理一方,自己明显站在下风头,怎么办?其实,人对外界的反应,可分两个概念:本能与境界。打一下会痛,挠一下会痒;受到批评,心里不舒服,这都是本能,人人如此,无可非议。接下来,如何应对,就是境界问题了。张中行公开认输,是一种高境界;此外,人家批评得对,默认,也是不错的境界。有位读者,认为牧惠在“笔会”上的一篇杂文用错史料,来稿纠谬。发表前,我打电话告诉牧惠:“有人要批评了,你能不能再反驳?”牧惠回答:“读了文章再说,可能反驳,可能不反驳。”结果,他没有动静,说明默认了。
当然,人家明明批评对了,却不服输,总在那里,找理由反驳,这种作者也有。他们与张中行、牧惠一比,差距便出来了。
盼望杂文界里,对批评和反批评,都能抱一种好心态。
●记者:作为杂文编辑,最想对读者说的话是什么?
○朱大路:在当前泛娱乐化倾向充斥荧屏的时候,恭请广大读者坚持对杂文的爱好。杂文是思想的产物,读杂文需要投入思想;而开动思想机器,比看“超女”表演要费力得多。一个社会,倘若只崇尚浮躁,拒绝深沉,是会暗藏凶险的。
要让杂文家在全社会吃香起来。荧屏上的“家庭演播室”节目,为何只见电影明星夫妇出场,不见杂文家夫妇出场?我对此颇感不平。面孔好看要紧,思想深刻也要紧呀。为此,拟了两句抑扬顿挫的话,作为广告语,请大家代为张贴——
“既要追捧徐静蕾,也要宣传徐迅雷。”
(本刊记者: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