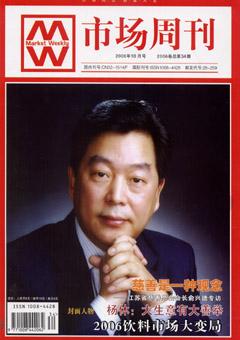扬子电气:民国股改往事
郑会欣
国有企业私营化在近代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其例,譬如本世纪初张之洞就将亏损巨大的湖北纺纱局及其他官办三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全部招商承办,规定四局产权为官方所有,经营管理由商董负责,嗣后逐渐转亏为盈,企业获得新生。当时外国人编纂的江汉关报告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报告指出:“这一个中国人办的纱厂开工有二十年了……它的命运是在变动的。当它在官厅的手中,常常是失败的;当它租给一个商人时。除了当地棉花收成不足以外,它总是赚钱的。”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国有企业私营化应该视为近代企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应该承认国营企业通过招收商股改为私有化可能会在经营管理方面发挥更突出的效益,办得更有起色。然而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这种方式很多时候往往因为并不是一种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官商私相授受大开方便之门。下关电厂的前身首都电厂在民国经历就是明证。

20世纪初叶,江南第一重镇南京却依然要靠蜡烛、油灯来照明。1909年6月(清宣统元年五月),江南财政局提调许星璧向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提议,拨款在南京西华门外的旗下街(今西华巷南段)建造了一家电灯厂,用以供给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两个衙门的晚间照明,该厂被定名为“金陵电灯官厂”,厂总办(即厂长)为许星璧,并向上海西门子洋行订购了3台各为100千瓦的发电机。后因余电太多,经张人骏同意,将官用电灯厂改为公用电灯厂,余电公开出售。1910年8月9日,金陵电灯官厂在《南洋官报》刊登装灯广告:凡官绅学士商各界,如需装电灯者,请即到电灯厂挂号,以便挨次装灯:每盏独光电灯安装费为大洋5元;每盏电灯每月电费为大洋一元二角;供电时间,无论冬夏迟早,每晚8个小时。
民国建立后,该厂易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用户方不断增加,设备亦逐渐更新。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遂接收该厂,改称南京市电灯厂,此时用户虽已达3000余户,但电压不足,灯光暗淡,电力供不应求,与首都之地位极不相符。在此情况下,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南京市电灯厂改隶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4月17日,建委会正式接收,将厂名改为“建设委员会首都电厂”,简称“首厂”。
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8年2月18日,直隶于国民政府,从事交通、水利、农林、渔牧、矿)台、垦殖、开辟商港、商埠及其他生产事业之设计开创,并对各省区建设厅负有监督指导之责,由张静江担任主席。同年10月,建设委员会更名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改隶于行政院,取消主席制,设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各一人,张静江旋任委员长。
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加紧扩张国家资本的势力,并以政府名义接收了不少私营企业,如交通部接管轮船招商局、建设委员会接管长兴煤矿以及耀明、震华两电厂;利用发行公债、增加官股的手段控制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建设委员会,将首都电厂划到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旗下也不足为奇。
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加紧扩张国家资本的势力,并以政府名义接收了不少私营企业,此时将属下的国有企业(其中还包括原本由私人手中接管的企业)以接受商股的名义改由商办,这岂不是与政府扩张国家资本的决策背道而驰?
但是,几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突然对外宣布将属下的骨干企业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等国有企业改为民营,并委托中国建设银公司代为招募商股,之后不久便成立了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完成了所谓“国有企业的私营化”的转变。此时将属下的国有企业(其中还包括原本由私人手中接管的企业)以接受商股的名义改由商办,这岂不是与政府扩张国家资本的决策背道而驰?
另外,首都电厂与戚墅堰电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当时经营十分成功、在同类产业中成绩优异的企业,而不是一般人心目中官营必定是效率低下、濒临破产的企业。数据表明,截至1937年6月底,首都电厂的资金大约为878万元。从资产情形上看,截至1936年12月,该厂总投资为8013000元,固定资产为9587000元,为建设委员会刚接管时(1928年5月)的44.9倍。戚墅堰电厂因原有设备相当完善,所以固定资产的增长情形远远比不上首都电厂,但即便如此,1933年12月时的资产也已较建委会刚接管时(1928年)增加了58%,达到266万元;若依据概算,该厂至1937年度总资产约为400万元,而实际固定资产至1936年度已达400万元以上,较1928年亦增长一倍有余。从赢利能力上说,首都电厂、戚墅堰两电厂的获利情形在江苏省乃至全国一直名列前矛,1935、1936年度一般均保持在20%-25名左右,这比当时国内供电规模最大的外资企业上海电力公司5%的年获利高出许多。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也一直以首都电厂及戚墅堰电厂“为本会发展全国电气事业之起点,一切技术设施、营业办法、会计制度,均力求精审完备,随时改进,以资他厂取法”。为什么偏偏在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将这种优质资产划归民营呢?
对此,建设委员会的说法是,发展实业需要巨额资金。据建委会估计,两年内需要筹措资金5230万元。而国家一时难以筹措,于是建议“为发展建设委员会主办之电矿事业,拟具招收商股办法,以提高社会投资”。
实际上,建设委员会招收商股的真正原因与张静江有着莫大的干系。建设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创办了不少企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然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张静江等人好大喜功,投资项目过多,摊子铺得太大,没有考虑本身的承受能力,以致于负债过重,最后则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据统计,截至1937年6月30日,建设委员会本部及其属下企业的负债负债总额合计达到17780751.48元。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出建设委员会负债累累的情形:当银公司刚刚宣布完成招募商股之后不久,1937年5月22日,建委会就以“现在本会本月内需用国币贰佰元万”,要求银公司立即将其所招募的款项拨交建委会的银行账户内。据统计,自1937年5月26日至1938年2月18日,银公司将其所招募的商股分7次共1165万元拨付给建设委员会。很明显,这些新招募来的商股大部分是用来偿付建设委员会各种到期债务的。张静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建设委员会前此办理电矿事业,纯恃其本身历年之盈余,与夫对外筹措之债款,经济能力甚属有限,对外负债超过本会投资约一倍半左右。”因此张静江和蒋介石认为:“只有设法吸收长期民资,藉图扩展”,其办法就是学习欧美等国成例,将部分电矿事业改归民营,以便让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在市场流通,使一般游资可以有正常的投资渠道。为此他们建议,首先将建设委员会经营多年、且已颇具成效的首都、戚墅堰两电厂等企业作为
国有企业私营化的试点。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负债过多,财政支出日益庞大,政府已无法注资以维持及扩大生产,反须将已投入之资金逐步抽出改作他用,国有企业的真空便只好招集民间资本来予以填补,从而企业的产权结构亦随之发生变化。
对于首都电厂和戚墅堰电厂这样经营效益良善、设备粗具规模、资产亦较为雄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对于一般商家来说自然极具吸引力。但是从实际操
从过程上来看,1937年4月1日国民政府训令批准张静江、蒋介石“为发展建设委员会主办之电矿事业、拟具招收商股办法”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4月9日,建设委员会拟定具体招股办法,主要内容为:(一)将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合并,组织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公司资本均定为1000万元,除建委会各保留20%(即公司200万元)之外,其余均招收商股,并委托中国建设银公司办理。短短的一个多星期就完成那么多复杂的评估工作。另外,在建委会在招收商股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拟具章程,还是吸收股份,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既未刊登招股广告,又未对外公开宣传,待到扬子电气公司召开发起人大会时,才突然对外宣布公司各1000万元的商股已经全部募足,令世人大吃一惊。1937年5月,建委会宣布将首都及戚墅堰两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一千万元,除建委会保留股本二百万元外,其他商股均由中国建设银公司募足。这也就是说,建设委员会将其苦心经营近十年的国营企业,以招募商股的名义拱手让出,交由银公司出面打理了。
此外,关于资产评估计也让人生疑,资产与负债居然完全相同。档案中一份“扬子电气公司财务报告”内中包含该公司1937年7月1日(公司正式成立的日期)资产负债表。(见下表)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建设银公司(China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呢?这究竟是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中国建设银公司是1934年由刚刚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亲自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从表面上看来,公司是根据《银行法》和《公司法》注册的私营公司,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简单。公司初期的股份中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与最大的十几家商业银行,并非个人投资;公司的股东乃至董事和监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高官,就是活跃于商界的金融大亨,或者本身就是身兼二任的人物,彼此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因此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与政府保持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即标志着国民政府成立后官僚与财阀的一种结合。而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张静江以及3名常务委员中的张嘉和李石曾二人既是建设银公司的发起人,又是银公司的股东,而且张静江还是排名第一的监察人,张嘉和李石曾则都是公司的常务董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建设委员会将属下经营得最好的企业交由银公司接办。
1937年5月14日,扬子电气公司在上海中国建设银公司所在地召开发起人会议,对外宣布资本业已募足。7月1日,两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并于10月29日经核准登记。从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名单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名单(1937年5月)
董事长:宋子文(商股)
常务董事:张人杰秦瑜(官股)
孔庸之孙哲生霍亚民吴震修(商股)
董事:吴敬恒潘铭新(官股)
李石曾曾养甫胡笔江陈光甫李馥荪
周作民钱新之汪楞伯宋子安贝淞荪
胡筠庄尹仲容(商股)
监察:张家祉(官股)
余梅荪陈康齐秦颖春赵季言卞仲(商股)
就此过程来看,其他商家绝无染指可能。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经过改组之后的扬子电气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完全操纵于中国建设银公司手中,如公司的董事长都是宋子文(建设银公司的实际创办人、公司执行董事),而董事会秘书长则由银公司副经理尹仲容担任。
其次,建设委员会所谓“提倡人民投资以扩充国内建设事业起见,拟为已有成效之事业招收商股,组织公司,继续经营”,只不过是一个对外宣传口号而已,实际上招收商股完全是在暗中进行,从未公开招募。待到公司召开发起人大会时才对外透露此事,并宣布股本业已募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商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股,公司的股东名单表明他们分别是各家银行的法人代表而并非是个人的投资,这也同中国建设银公司一样,公司初期的董监事所拥有的股份亦并非全部是私人投资,其中绝大部分是各股东银行参股的数额;但是到了抗战后期,这些官僚与财阀利用手中的特权,以极低的价格从国家银行收购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此时政府的资产已经和官僚财阀私人的利益混为一体、难以区分了(注: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时中国银行占有20%的股份,中央和交通二行则各占有15%的股份,此后公司的股份不断转移,如中央银行的股份就大量转移到孔祥熙名下(以敦厚、悦愉、嘉禾等户名代表),抗战后期(1944年1月)建设银公司又要求中国银行“援央行之例,将其股票让出一部分给友邦人士及民间,藉收普及之效”,结果中国银行即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其拥有的股份出售给私人。从后期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股东名单可以看出,新拥有这些股份的个人不是财政部门的高官,就是银公司的董事或高级职员,此时国家银行占有的股份迅速由50%下降到5%,而个人拥有量则从1O%大幅提高到70%左右。
第三,从扬子公司的股东名单可以得知,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其最大的股东,它不但占据了公司近一半的股权,而且其他参股的银行也大都是银公司的股东:再从各银行的股份来看,除了中国、交通、国货与上海4家银行所拥有的股权比较多之外,其他的几家银行或公司股份则完全一样,都是1250股,这就说明股份乃为分配摊派,而并非自由竞争,至于股份的比例则主要视银行实力及其在银公司中的地位而决定。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中国建设银公司控制了扬子公司,但公司的实际管理仍由原建设委员会的班底掌握。从法律的意义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将所有权中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四项权能中的一部分交由专门的经营者来行使,而与其所有者相分离,这也正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之一。比如扬子电气公司的总经理就由曾任首都电厂厂长(1933年2月-1935年8月)、时任建设委员会设计处处长(1935年8月-1937年12月)的潘铭新担任,首都、戚墅堰两电厂的厂长则分别由原厂长陆法曾、吴玉麟续任,后者还兼任公司的协理。
1937年7月1日,扬子公司顺利完成交接手续,正式开始营业。然而开业连一个星期都不到,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随着东南沿海大片国土的沦陷,扬子公司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扬子公司被日本人占领后,属于华中株式会社。首厂与南京自来水厂合并,改名为华中水电公司南京支店。抗战胜利后银公司依仗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迅速将其接收并予复业,1949年4月资源委员会又欲将其收归国有,但未几南京解放,银公司以及扬子公司及首厂均被视为官僚资本而被新政权予以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