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一九九三
王 蒙
1992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中国的形势又有大的发展变化,用一位党外老人的话来说,叫做“春潮澎湃”。
1993年这一年,我接到几个邀请:一个是香港岭南学院现代文学研究所梁锡华(又名梁佳萝)教授邀我去作一个月的研究交流;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院院长韩南教授请我做特邀学者,到他那里做三个月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关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研讨会,是由美国赖斯大学本杰明·李教授组织的;一个是新加坡文化部艺术委员会邀我做他们举办的“金点文学奖”华文小说组的主审评委;一个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还有一个是台湾《联合报》邀我参加他们主办的两岸三地中国文学四十年研讨会。
于是,1993年便成为了我的游学之年、旅行之年、环球之年、周游世界之年,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我的妻子崔瑞芳一起。
这一年是芳与我第一次同时出境观景,时芳已经60岁整。我们一起去了新疆,一起去了伊犁,一起去了巴彦岱人民公社,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走出国门,看看世界是怎么样的奇妙了。
飞往新加坡
出发前有一个插曲,在与新加坡方面联系我的出访安排时,我得到了香港方面偕夫人共同访问的邀请,而访港与访新都是往南走,从旅行路线上说宜于合并出访。最初我与新方友人探讨我与妻子同行的可能性的时候,新方迟迟没有答复。于是我决定单独一人赴新,然后在香港与芳会合,因为香港邀请的是我们夫妇二人,且已获准,办好了有关手续。新方行事很谨慎很严密,当他们得知我们夫妇将在香港会面时,立即发出了对芳的邀请。
直到登上飞机,升空飞行数分钟以后,我和芳才互相祝贺,我们终于实现了双双携手走世界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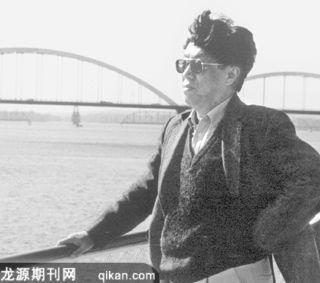
一路上,印象最深的是天上的云:傍晚时分,日落前后,各种白云,形状极其奇特,有的如蘑菇云,有的如大口袋,有的如一个巨钟,有的如葫芦,有的如团扇。平常在地面上,我们仰头看云,觉得云大体上是平铺在天上的。而此次坐在机舱看云,却觉得云是悬挂、站立、垂直在你的身边。而天色又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的调子,由明亮而昏暗,由润泽而沉重,由白而黄而酱色而黝黑。
等到了新加坡的宾馆,已经是将近午夜,我们又一次相互祝贺起来。
访问与评奖活动还是很正规的,在宣告评奖结果的会议上,要求每位评委用英语讲五分钟话,我也比较自然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文学讲座中,我听到一位菲律宾作家的讲演,他讲到,过去菲律宾作家们的写作是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现在,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已经被推翻了,作家们的写作反而失去了方向了。
此话对我并不陌生,因为此前我已经听到一位俄罗斯汉学家讲过,说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原来要民主要自由,得到了民主与自由以后,不知道自己还要做些什么。
与我讲这类话的人中也包括费德林博士,斯大林时期他曾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驻日大使。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北京,特别调他担任翻译。我1984年访问莫斯科时他任苏联作协外委会主任与《外国文学》主编。他90年代初两次来我家,情绪低沉,反复地说“我们失败了”。
我也想起了我的一首诗:冬天/盼望着春天/夏天/盼望着秋天/只有春天和秋天最难过/不知道应该盼望什么。(大意)
这次访新使我们有机会结识了从事慈善救助事业的张千玉女士,她对于一个温柔美丽的世界与人生的设想,令人感动。她的文字亦极佳。严峻苦斗的中国人已经好久没有接触过这样温和而且良善的文字了。
通过张千玉,我还拜访了国学大师潘受(又名国渠、虚之、虚舟等),他的书画诗俱极佳,被新加坡政府授予“国宝”的称号。我们在潘老师家中用了午餐。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正有学问的老人的格外谦和与雅致,潘老的微笑多于评论,聆听多于讲述。他的七律《黄鹤楼》上接崔灏、李白,下临今日实况,感慨万端,忧国忧民:
谪仙未敢题诗处,海客狂怀啸忽开。
芳草空余鹦鹉赋,残基曾踏凤凰台。
剩携秃笔三生泪,难写神州百劫哀。
今日倚楼试招手,白云重望鹤飞来。
“剩携秃笔三生泪,难写神州百劫哀。”十四个字写得如此沉痛深沉,寥阔空茫,我算是五体投地。先生生前,无缘朝夕聆教,先生去后,总算不断地背诵下来了这十四个字。无缘问学,有心攀附,就用这十四个字来咀嚼自己的经验和所余的日子吧。
张女士有一种真诚的,我要说是东方的基督徒的热忱。她谦逊也含蓄,但拯救迷途的羔羊的热忱是永远炽烈的。她到哪里去常常带一个大孩子,那个男生曾经流落在街头,流落在下九流的场所,在张女士的帮助下走上了正路。甚至于到潘受老人那里,她也带着他,我倒是觉得潘老恐怕不大好理解这种人和故事的。
访问马来西亚

接下来访问马来西亚,与先父的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有很大关系。他在汉堡大学退休后,常常住在吉隆坡的一所大学里,老年的他受不了汉堡的冬季。傅的女儿在北京时听说了我要访问新加坡,便告诉了她的父亲,傅教授推动了《星洲日报》对我访问马来西亚的邀请。
我们是晚间到达吉隆坡的,报社同仁打着横幅在机场欢迎我们,总编辑刘鉴铨先生与副刊《花踪》的主编萧依钊女士安排着与照顾着我们的访问。萧女士的工作作风与待人接物,给我的感觉是异域碰到了雷锋。刘总与我的交谈也是一见如故,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切与期待,担忧与亲爱,都非常令人感动,也都非常健康和富有建设性。他们的董事长张晓卿先生,祖籍福建,更是一片热诚,关心中华。我在那里做了一个讲座,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与夫人,以及使馆其他官员都参加了。
还有一点,根据马国的国情,据说我每天讲了什么,他们的安全工作人员都是要写汇报的,这次,汇报怎么写一直来问我的东道主,倒也公开化、透明化了。
此前制定的对于中国来客的特殊防范制度与当年的马共游击队活动有关。当年确有许多热血青年,团结在马共陈平书记的旗帜之下,意图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赢得革命的胜利。后来,游击队被剿灭,陈平阵亡。为此吉隆坡街头修建了一个类似和平纪念碑的雕塑,是纪念马国对于共产党游击队的战胜。我们看了,也有所感慨。天地沧桑,人间起伏,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天地不仁,万物刍狗。岂止陈平,列宁斯大林和突然在中国红了一两下的切·格瓦拉,在各自国家,最后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束呢?历史是丰富多彩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而个人反而更加显出渺小来了。世上毕竟有比自己的政见与对于政见的记忆更重要的东西,它们是人类的命运,民众的福祉,历史的合力,现实的要求与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
写本书时,我正在翻译印度驻华大使拉奥夫人的诗,她有诗云:“我们都是一些面包碎片,被历史的烘面包片机的不同部位所烘烤。”然也。
我们一起去了槟榔屿、马六甲与新山。在槟榔屿,我们足喝了肉骨茶。在马六甲,我们领略了那里的“娘惹”文化,一种早期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文化混合。在新山,我们参加了华文学校的一个活动,马国华裔人士对于中华文化的热情与苦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山毗邻新加坡,新加坡作家陈美华特意从新赶到,参加我在新山学校的活动。
小憩珠海与烟台
从马来西亚回国后,我应邀先到珠海斗门县白藤湖度假村小事逗留,同行的还有从维熙夫妇、钱钢夫妇,还有一位老编辑夫妇。我们在那里见到一位斗门县的老领导,因故被开除了党籍,改行下海经商。他自己开着一辆“大奔(驰)”,名片上是他任董事长的公司在珠海和澳门的地址。让人深感时代之不同,觉得他就是黑红黄三道说的例证。其时已有此说,黑道指搞学术,因为博士帽儿是黑颜色的吧。红道是指所谓“仕途”。黄道是指经商,金子是黄色的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前途也逐渐多样化了。
十余年后,我突然收到这位朋友寄来的他的讲述中国古典诗词的新作,我心中一动:莫非他不再经商?莫非他经商受挫?不久,见到来自南国的友人,证实了我的想法,他的生意垮了。“文章憎命达”(杜甫),“从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第一,文穷而后工;第二,途穷而后文。当然不是绝对。
白藤湖之行的另一个额外收获是听钱钢的夫人于劲讲她的关于黎锦光的报告文学。传主与黎锦熙、黎锦晖是三兄弟,前者是语言学家,是国语注音符号的发明者。我住的北小街46号的原住户,夏衍之前便是黎锦熙。黎锦晖是作曲家,《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家喻户晓的老曲子便是他作的。黎锦光也作曲,《采槟榔》、《夜来香》等是他的代表作品。
于劲说她到了黎锦光家中,贫穷自不待言,黎的家人的举止穿戴也彻底地底层化劳动化非白领化了。这倒是符合把颠倒了的一切再颠倒过来的理念。那么多美好的振聋发聩的理念,实行起来却发生了与理念背道而驰的效果。而一些说起来美好,实际上却难见美好的理念却老是那样无可奈何地左右着现实。这是多么煞风景却又多么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于劲说黎锦光的命险命苦,改革开放后,上海的一个区落实对他的政策,安排他担任了区政协委员,数月后,他亡故了。大时代的人的命运,形形色色,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从珠海直飞烟台,我与芳到中国文联文艺之家休息并写作《恋爱的季节》去了。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二浴场游泳至少一千米,正逢海蜇活跃的季节,有时脸上手上身上到处撞上海蜇。与这边的作家,原烟台师范学院院长、作家萧平,长篇小说的写作能手张炜,部队作家李存葆、李心田等都有友好交流。原文化局长刘德璞、副局长郝鉴,也都多有照料。烟台市政协主席巴忠鼎,多次设宴招待。中国是一个很讲究人情的国家,只要国家不出大变故,活在中国,其实是一件舒服的事。
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研讨会
8月22日,我应美国一所大学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意大利参加一个研讨会,接着应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邀请到他们那里作三个月的研究访问。可能是由于双程机票才便宜,再加分别结算机票的方便,他们安排的是我与芳先飞抵美国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第二天立即跨越大西洋飞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飞美国波士顿。可这么一飞就累死人了。22日,上午飞机晚点,到上海停留两个半小时(延长了时间)再飞到东京,再停留近二个小时,中间是否还在阿拉斯加停留,记不清了。反正再飞到纽约,早过了预定飞波士顿航班的起飞时间。面临最后一班飞机,航站管理人员说是座位全满了。我们当时真有点筋疲力尽,弹尽粮绝之感。
说明情况后,他们还真是破例为我们腾出了两个备用座位。过了午夜才到达了波士顿,害得接我们的友人刘年玲也是不知等了多长时间。
睡醒一觉,再上机场,乘英航先抵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英航的空中先生极英俊亲切,服务周到。希思罗机场的四号站(国际站)也极宽敞。只是转机等了不少时间,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贝拉吉奥是一个风景区,四面环山,中间是一条更像河流的狭长的科摩湖。山区一处建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研与研讨会中心。这里保留着古老欧洲的传统,每晚要正装集体用餐。这里喝番茄汁的时候要加沙司、盐与胡椒。
我最最中意的是湖。除与大家共乘游艇游湖外,我每天清晨起来先下湖游泳。以至一位美国学者向他人讲他的经历,说是他已经起得够早的了,下湖游泳,忽然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头,把他吓了一跳,却原来是王蒙,起得更早,游得更远。
研讨的主题是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会议中人们对于中俄两国发展变化情状的比较很有兴趣。在人们说到亚洲、东方等概念时,与会的两位俄国学者则强调他们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他们的领土有多少多少万平方公里是在亚洲。他们的论据不由得使我想起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论战,关于苏联是否应该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中国说苏联是欧洲国家,不宜参加亚非会议。苏联说它有多少多少平方公里在亚洲,所以它必须参与亚洲事务。时过境迁,争论性质完全不同,论据不变。俄国学者争的是他们的改革模式,是为了论证他们的改革模式具有跨大洲的普遍意义,论证他们的模式虽然一时效果不佳,但最后,只能是他们笑到最后。这也使我想起中苏论战时期关于“苏联经验”的普遍性问题的争论。何必那么关心自己的道路的普遍适用性问题呢?中国干脆称自己的办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需要也没有冲动去推广自己的经验。
我没有兴趣去比较中国模式与俄国模式的优劣,各国情况不同嘛。只是《大块文章》中提到过的西班牙老大使,他在1989年离华改任驻俄大使,到90年代后期又回北京任驻华大使,他说,他比较了两国的道路,相信中国的路子更成功。
我还有一个体会,公民社会啊,公共空间啊,这些提法都非常有意义,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这些名词毕竟来自欧美社会形态与社会政治观念,有些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在中国,人们用的挂靠呀,对策呀,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呀,保持一致呀,统一思想呀,放宽政策呀,闯红灯(现在不提了)呀,松绑呀,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呀,站得住呀,通得过呀……之类的字眼,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楚的。又是我们不一样,We are different了。
贝拉吉奥的面条实在做得太好了。有些国人总以为天下餐饮笃定中国第一,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也是这样认为并论述的。这恐怕不能说得太绝对:第一,西餐重选材与原色原味,明快清晰,并不意味着加工不足。第二,西餐的乳制品、甜品、冷食以及番茄汁、鲜柠檬与柠檬汁的使用,葡萄酒的品类与质量,种种酒的香气,种种饮料的制作与供应,马铃薯的制作与种种鲜菜生菜的大量食用,直到某些特定的菜肴,如法国鹅肝、俄国黑鱼子、许多种类的牛排(包括肉牛的品种与饲养)大致优于中餐。第三,中餐的爆炒(出了太多的油烟)及大量酱油与食油直到味精的使用,都有可以改进之处。第四,我们的口味当然喜欢中餐,不等于西餐不如中餐。
烹调是我们的强项,但绝不可小觑西餐。例如意大利面条,含面筋比我们多,结实有力,做法也具特色。我吃的一次菜汁荞面条,拌一点洋葱花与橄榄油,足以令人销魂。那天芳想少吃一点,没有去餐厅,结果旅美学者李欧梵一个人吃了两份。当然,他到北京来时,我找他去新疆餐厅用饭,拉面条,他也吃了两碗,他再洋,学问再大,毕竟根在河南,他是河南人也。
研讨会的组织者是本杰明·李,他的夫人是小说家、北大1977届毕业生查建英,查的父亲是原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长、后来的社科院马列所领导人查汝强,查汝强的前妻钟鸿曾与我同在一担石沟劳动,是一个美女右派,文艺工作者。我们与他们的第一、二代人都是,也应该易于成为好朋友。
在美讲学
连来带走五天,我们回到了哈佛所在地波士顿边的康桥大学城,开始在美国讲学的三个月。
这三个月是我们自己租的房子,位于中央广场附近的法耶特街14号。法耶特,即拉法耶,人们熟知的二战时期法国将军。我们租的是一间二层小楼的二层,三室一厅。所谓厅,把客厅、起居室、厨房、饭厅结合、连通在了一起,约有20平方米。三室中大的有12平方米,一个窄窄的双人床,真不知道人高马大的美国双人怎么样在上面睡;其次的大约8平方米,内放一单人床;更小的不过五六平方米,是电脑工作室。原主人是一名女教授,年近50岁,新婚,与先生去欧洲度蜜月,乃出租此房。她是左翼,是当地反对核武器的代表人物,曾去过苏联,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这一处房屋虽然不太大,但很实用。我们除了付房租,还帮她照料室内绿色植物。有趣点之一是,大门,二门(即通二楼的门),每一间房门,都有锁,房东并建议我们出门时所有的锁都要锁上,但全部只有一个钥匙,一楼是另一家,钥匙也一模一样。这就避免了例如听说一位领导分了房,同时掌握了二百多把钥匙——多么麻烦。也避免了瞎黢黢地换一把再换一把,老是找不对钥匙。希望美国人的这个经验能被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适当参考。
只是按中国国情与心理定式,一把钥匙,谁能信得过呢?
阳台是六角形的,也可爱。走廊里是她与亲属的各式照片,如同家庭图片展览。她喜欢收集陶罐陶壶。她的电视机极其一般,尺寸也小。
哈佛燕京的院长时为韩南教授。我们在北京三联书店组织的活动中首次相识。他翻译过中国古典作品《肉蒲团》。
这三个月,我主要是写季节系列第二部《失态的季节》。我在哈佛远东与太平洋研究中心——又称费正清中心作过两次讲演,介绍当代中国文学。我记得我特别以80年代韩蔼丽与90年代洪峰的同名小说《湮没》作了比较,悲情的政治倾诉与一种冷漠的自嘲与荒诞的对比,我也讲到了新写实主义的零点写作与王朔的出现。讲到了《爸爸爸》等作品,还有一些争论,关于文学史分期,关于伪现代派什么的。
我参加过一次中文课,因为该堂课是讲我的《夜的眼》。
我到衣阿华大学、耶鲁大学、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马里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协会(在华盛顿特区)、华美协进社(在纽约)等地发表了讲演。衣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聘我担任他们的顾问,当时中心主任是韩裔的金再温教授,我们交谈得很开心。但是顾问云云,也只是挂名而已。
华盛顿的亚洲协会,听众多是外交官或退下来的外交官。听众中有前驻华大使恒安石等。
在马里兰大学我见到了美国友人李克与夫人李又安,斯时李又安癌症已近晚期,为了对于中国的关切,她是坐着轮椅来的。他们为中国的状况与面临的问题十分担忧,听了我的介绍,他们说是好过了一些。
我必须讲明,斯时的数量可观的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把中国视若地狱的。有的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到地狱里去。美国人的自信带着天真。我看过他们的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是写原东欧的犹太人过着怎样痛苦的生活,剧本的光明的尾巴,是剧中的人物终于获准移民美国了,他们次日就要动身赴美,人们充满了憧憬与希望。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不是偶然的,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去掉了大魔鬼萨达姆,送来了美国式的民主,伊拉克人还能不感恩戴德,载歌载舞?从此一步进入了天堂。这也是从天堂的理念出发,构建出了货真价实的地狱来的一例。
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少谈理念与意识形态,讲中国的实际,讲市场经济与有关争议、日常生活的改变、消费的发展与终被认可、精神面貌的发展、发了财的作家与正在骂娘的作家、自由表达的甜头与限度、言论的宽泛与贬值、首都出租车司机的论政、电视节目的党性与电视广告的覆盖性、畅销书与文学、新的民谣、话剧近况,等等。例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郭启宏的本子《天之骄子》,讲曹植的事:有一个佞臣向曹丕打曹植的小汇报,曹丕不感兴趣,对佞臣说你老汇报他写诗的事,你也写一首诗嘛,佞臣第二天给曹丕朗诵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歌功颂德之作,曹丕听完评说:“三分诗,七分吼……”戏剧演到这里,掌声与笑声混合成一片。但同时上海的一位共同观剧的朋友不理解这样的情节如何能引起掌声,他们说上海人对这种带政治性的对白,早已丧失了兴趣。
我大讲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我讲到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保持连续性的必要,防止大动乱的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髓的必要。我明确告诉听众,要求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只会引起更大的动乱。问题在于怎么样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的是造反有理,而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我不懂得为什么美国人不希望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髓。美国人认为当然的事情,到了中国不见得当然,而可能是当然不行。所以要理解而不是煽情。
会场上不断传来掌声和笑声。他们说,一段时期以来,来讲话的中国人不是痛哭流涕的就是跳脚大骂的,他们已经不能想象介绍中国的时候能赢得掌声和笑声了。当有听者问我对于滞留不归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建议的时候,我从原则上回答说:回去。中国的事只能在中国办。我认为如果以不归为代价定居海外,或者以不出门为代价定居大陆,都是太糟糕了。
有人问我对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的看法,我谈到了据云的匈牙利的经验,他们将过往时代的遗物,集中放到布达佩斯一个“斯大林公园”里,成为一个见证,一批文物,一道风景,一个旅游点。就是说既不必讳莫如深,也不必再煽悲情,引吐苦水。
一位来自祖国大陆的女留学生非要请我们在“水门”公寓附近吃晚饭。她说,我的面孔上有“苦难的痕迹”,而那一位对“公园说”大怒的兄长长着的是一副扑克牌脸。此说有些新意。我回到宾馆特意照了一回镜子,觉得我的脸上的“苦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的盐碱地和代粮食品红薯、近海食品卤虾酱。您就看看鄙同乡张之洞那张倒霉的面孔吧。
从9月到11月底,我们尽情享受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红叶与橡树。其间我到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双子城去看望了在那边读书的二儿子王石。我学会了许多在美国的生活知识,登记了社会安全号码(SSN),从而可以更方便地完成完税、免税、开户等财务手续。置办了信用卡。选择了往中国打电话最便宜的电话局。学会了电话确认机票与购买必需品的办法。我们在剧院听了小泽征尔指挥的马勒的交响乐。我们熟悉了当地的许多中西餐馆。不仅仅是讲学,而且也包括了日常生活,我们对美国社会与各种运作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纽约的皇后区,来自台湾的友人陈宪中先生为我们请来了著名音乐人罗大佑先生与他的姐姐,罗先生一面喝红葡萄酒一面唱歌,我可真有面子!
同时,也在陈先生家里碰到来自大陆的一位女作家,就是她在1986年让陆文夫兄大大地晦气了一回。她请文夫吃完饭让文夫签字好拿到什么机构报销,文夫愤而买单请了她。此次她则声言正在研究破解六合彩的密码,就差一两个数字她就笃定可以得到头等奖了。她获头等奖后,将购买比陈先生家更好的房屋,房子不但要傍山,还一定要靠水。
我顺便发表我的感想,还是回到祖国更舒服,更好。你想有助于国家民族人民的进步发展福祉,当然最好与国家民族人民,与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在一起。如果你因故定居海外,常回来看看。如果你一直在国内,有条件的话出去走走。不要治气,不要较劲,不要想当然地与国家,与故乡,与时代的变迁,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世界或者与太多的地域、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过不去——其实最后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如今,人的心里应该有个广阔的世界。头脑里,文字里,经验里,阅读里,思考里都应该有这个世界。有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才能正确地与有效地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才能正确地与有效地应对来自世界的东南西北风雨。鼠目寸光,夜郎自大,抱残守缺,以封闭愚昧为荣,与唯洋是瞻一样,日子是不好过下去的。
周扬说过,第一,社会发展是不能够跨越阶段而进行的,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
语重心长。
(选自即将出版的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
责任编辑:王文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