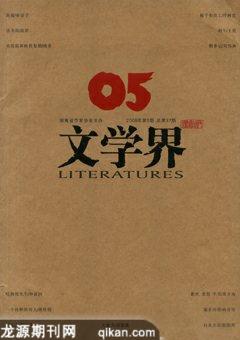栀子街花工
符树忠
花工张确定斩手行动是在子夜时分,无论维持会长冯九怎么劝,他都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逼得冯九居然说,张老板,要么就走,你我都一走了之。花工张不同意,说,你和我一走了之,那栀子街的花工不遭殃?又说,冯会长,你莫劝,劝也是白劝。我这样做既保全你和栀子街不受连累,又成全了杏华恨日本人的心思。冯九说,杏华只是个花工伙计呐!你做老板的还听伙计的怂恿呀?花工张说,如今,伙计老板都是花工,都是中国人呐!冯九哭吧吧地喊声张老板,兄弟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花工张看看酒杯,一口喝尽,手起杯掷,拉起冯九离开店堂走进作坊,在板刀台子前坐好,端端正正地坐好。板刀台是栀子街寿福店专事裁皮纸的工具,功能简单,技术原始。一座大实木台子,两侧竖起两根柱子,柱子内有两道槽沟,卡住上下滑动的裁刀。生铁锻造的裁刀,五寸厚重百斤,刀背上有个耳子,耳子里穿根麻绳连接在板刀台下的绞车上,摇动绞车裁刀便拉起,松手裁刀直落而下。据说,裁刀很是锋利,通常百把斤一垛的皮纸,一刀一次崭齐裁断。花工张要用它斩手,自然轻而易举不留毛边。立秋好久,太阳、月亮两头见天,就是不见风雨。作坊里除了冯九,没有第三个人,原先做花的杏华和两个花工早被花工张打发离开了。作坊里的灯不是很亮,但还是照见了冯九泪流满面,感情真切的面孔。花工张知道,冯九做栀子街的维持会长不容易,那头要讨好日本人板田,这头要监督他做张记的绝活。现在因为他的斩手行动,冯九很可能会受株连,被板田捉住活埋,杀头,吊死。花工张记得板田离开张记店那笑里藏刀的样子,马靴刺碰得好响,立正、鞠躬、拜托!非常感谢!客气得不得了。然而看见他腰上挂的东洋刀,花工张心想,这狗嬲的,不知砍杀了多少中国百姓!
板田也不是什么大官,他只是日本人驻该城宪兵大队的一个普通军曹。但板田懂汉语,听力极好,该城老百姓一些不敢流行的方言,他也略知一二。板田长得很文质、礼貌,那张清癯、干净的脸上总是浮起些和善的笑意。他去冯九家时就是在这个秋季无风无雨的天气里。他一顶军帽揣在右肋下没有汗渍,不凹不皱,硬衬得是个刚出蒸笼的碱水馒头。他来到冯九家的院门外,没有用马靴踢门,更没有直接撞门入室。他是先整理自己的衣着,然而才伸手敲门,等到冯九家老妈子打开门吓得一跳,他仍然彬彬有礼地请老太太通报自己的造访。当然,这时冯九已经走出客厅来到院中迎接他了,因为隔着客厅的雕花大窗,冯九早把院中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进了客厅冯九一如平常,招呼沏茶,上点心,虚与委蛇。冯九知道,这个举止文雅的板田,从来就歧视中国人。那年,栀子街登记良民证时,他认为寿福店是为死人服务的低下行业,与日本涩谷妓女一样卑贱。因此,在良民证职业、姓氏栏里他都不填全称,一律只写花工张、花工李、花工王五麻子。冯九家的客厅不大,两套太师椅就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在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几只横冲直撞的苍蝇,时不时飞徊在板田凝重的脸上。板田告诉冯九,宪兵大队小岛少佐死了。冯九脸色一变,随即浮上悲痛的表情,撩起衣袖去擦本来就潮湿的眼角。板田眯起眼看看冯九,轻描淡写地说,我明白,中国人恨日本人。冯会长,你不会悲伤的,小岛少佐不认识你。冯九说,不见得,那年的报纸都登了,是小岛少佐领起你们从河西杀进城的。板田沉默良久,似乎认可冯九杀进城的说法。说到小岛少佐的死因,板田说,在你们城南,那个小瀛洲。板田伸出手掌,五指并拢,在自己后颈根上砍一下,少佐,死得迅速,没有痛苦。冯九知道,小瀛洲是这个城市妓女一条街,日本人都喜欢去那里消遣。他故意大啊一声,噫呀!婊子也敢杀皇军呀?板田摇摇头说,少佐是被城市里抗日分子谋杀的。又说,宪兵队已经抓到这些抗日分子,一共三十二人,妓女八人,凶手八人,身份可疑人员十六人,统统绞死。冯九不敢再有表情了,他只是看一眼板田那张干净的脸。板田的面孔不再凝重。他说,你们的小瀛洲不存在了,我们放火烧了。接下来,板田向冯九说明了来意。他说宪兵大队的长官,要按照中国的习俗安葬小岛少佐,以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因此请冯会长在栀子街推荐一家寿福店,采购小岛少佐发丧出殡的所需物品。冯九想了想这事不难,轻松容易。他向板田推荐了老井口花工张的张记寿福店,并对该店的产品略加介绍。判官头寿屋,你们日本人没见过吧?冯九说,十二根圆樟靠在一起,榫对榫,方穿方,出殡,气派。龙头扛前八抬后八抬,锣鼓唢呐四套行头才配得起!板田眼睛眯起点着头,像是沉醉于冯九话语中。冯九说得兴致高涨,抖出了张记的花圈绝活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英雄骑虎,二龙戏珠,十二生肖,员外,富贵……直到板田打断他。板田说,冯会长,我们去老井口,请张记花工张为小岛少佐服务。
老井口是处地名,在栀子街的街腰上。这里没有老井,只有株老气横秋的古槐,古槐的树荫里就是张记寿福店。莫看店子是这般营生,门面生意却一点也不比绸缎铺、点心坊示弱。四缝古意浓浓朱漆雕花大门,中门廊柱上有副木刻对子,上联云:阴阳二界人生自古谁无死;下联云:天地六道留取丹心照汉青。这对子把文天祥的名句镶嵌其中,颇有几分匠心。店堂里的柜台上寿服寿被,三铺九盖,用的穿的一样不缺。屋檩子上里三层外三层吊着灵屋子、花圈、招幡,死人要的活人用的应有尽有。冯九领着板田走进张记店堂时,花工张正在招呼生意,他一点也不意外,只是客气地吆喝,冯会长,要什么?我给您拿。这是栀子街招呼客人的规矩,客人进店,不能说您要什么,称呼您就犯忌。省略了您,就模糊了生死的概念,客人心里舒服。客人办齐了东西,要离开店子,不能说您好走,欢迎下次再来、光临之类的客套话,因为这又犯忌,这是明咒人家家里再死人。栀子街口上,刘记寿福店一个花工就犯过禁忌,那客人当场跺脚,吐痰,摔了东西扬长而去。当冯九把板田介绍给花工张说明来意,花工张照例谢谢冯九照顾张记店的生意,但他不知道板田懂汉语,他问冯九,日本人睡棺材埋在哪里?就算有地方埋,将来要回去,是带棺材走还是带骨头走?花工张如是说话,冯九急得不得了。好在板田没有恼火,他告诉花工张自然是用他熟悉的汉语,我们到中国来就不会走,要在中国实现天皇陛下皇道乐土的宏愿。花工张心里有些发毛,他不明白这个日本人,讲的中国话就是中国话。花工张还要开口,冯九就打岔了,忙不迭地向板田介绍张记的东西,纸钱香烛、灵屋子,怎么用,怎么烧,等等等等。板田突然说,请允许他参观张记的作坊,花工张没理由拒绝。
作坊在张记店堂后面。这里除了做作坊外,还是花工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花工张领着板田、冯九走进作坊时,杏华和两个花工正在做花。一堆裁好的皮纸料,一个剪一个拢一个染色,井然有序。栀子街花工做花颇有些讲究。通常一个普通的立式花圈,须大中小花九九八十一朵,里外七层才能把花圈布纸框堆满,真材实料,阔气经看。一叠皮纸顺折九次反折六次,一把剪刀咔嚓不停,一百五十四次才剪出五朵花坯,每朵花坯要点七层桨粘起,才拢得起花型,又经染色晾干后才是作得用的纸花。做花染色是花工最见功夫的手艺,那染缸洗脸盆大小,一指深浅却有三色之分,花工手艺好,那花便一次三色上得均匀,手艺不到家,那花出了染缸便是粪坑纸要好难看就好难看。杏华就是染色的花工,她一双灵动纤巧的手,于虚实之间提起花蒂上的纸筋,交叉掠过染缸,两个来回那花便有了黄蓝紫三色,生动娇艳犹如拍动翅膀的蝴蝶。三个花工将做花的每道工序,做得干净、熟落,行云流水,把板田也看得眼花缭乱。然而当板田竖起大拇指赞口不绝时,花工张注意到杏华只是斜睨这个日本人一眼,这一眼不是得意和骄傲,而是仇恨,像烈火一样燃烧的仇恨。后来,板田问花工张,作坊里怎么看不到判官头棺材和张记的绝活?冯九怕花工张不会回话得罪板田,就抢着说,做那些货场合大,费工费时,没人订寿福店都不做。板田说,我明白。皇军现在就订货,判官头棺材一副,英雄骑虎二十个,二龙戏珠二十个,金童玉女四十个!冯九背心出冷汗,他已知道祸从口出。他连忙对板田说,皇军呀难呀!现在是有材料没师傅,有师傅没时间,这么多货做不出来呐!板田笑容可掬,说,我五天后来取货,皇军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又说,冯会长,栀子街和小瀛洲一样的大,有没有抗日分子?然后马靴刺一磕,立正鞠躬,拜托!非常感谢!
第二天早上,板田派人将五百大洋送到张记,没有其他罗杂和麻纱。但冯九和花工张却面面相觑,一脸痛苦。花工张说,我关板子走人。他还只想起作坊做不出货,板田不会放过张记。冯九说,张老板,你不能走。你走了栀子街就是小瀛洲,会遭火灾,会死人。花工张说,冯会长,这桩生意是你牵进来的,我记你的好。只是张记一家做不出来呐!冯九眼睛盯住那五百大洋,眼睛珠凸起好大一粒。他告诉花工张,判官头寿屋,金童玉女他到栀子街其他寿福店去找,找回来算在张记的名下,价钱照算,张记就只做绝活的货。花工张这才松了口气。心想,冯九到底是维持会长,有心思,有心思的人就不怕做不好的事。只是这五百光洋他不知是让冯九拿走,还是放在张记。冯九那曾做老爷的秉性又现形了,他一举手,袖笼子几扇几扇,吩咐花工张,这钱你先收起,等板田这事了后再计较。后面还有钱来,我估计不会错的。
日过正午,店堂里没有什么生意,花工张就到作坊里来了,他要盘算一下作坊里的材料,能不能做四十个绝活花圈。他一眼望见墙角里一大堆花圈存货,心里生出个主意来。如果把这些花圈改头换面,做成英雄骑虎和二龙戏珠的内容,不是既交了板田的货,赚了钱,又销了张记的存货,一举三得。花工张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花工杏华。杏华是河西布纸码头人。布纸是寿福店专门用于蒙裱花圈下,灵屋的一种纸张,它厚、柔软像布一样富有弹性。杏华家开布纸店时,花工张都是在她家进的货。那年日本人从河西杀进城时,她家破人亡后便投奔了花工张。在花工张的印象中,杏华是位精明能干的姑娘,他有什么事,都愿意和她说,听听她的主意。但这回杏华知道是为日本人做事就变了脸色,不再和言细语。她说,张老板,你跟日本人来往就不怕人家戳背,骂不要脸么?花工张叹气说,杏华,我们做这行已经背到底了,哪还顾得上一张脸呀?杏华一脸憋得通红,好久才咬牙切齿说了六个字,日本人不是人!花工张没有体会到这六个字的份量,他完全照自己的想法把工派了。一个花工拆旧花圈,一个花工裱布纸框。他自己和杏华扎绝活框坯。框坯是用发了水的细篾皮、纸筋做成所需造型,炭火烘干定形后再裱皮纸、上色与布纸框连成一体才是成品,工艺亦讲究、复杂,是张记难得一现的绝活。
一天一晚,张记将板田的货竟然做出了一大半,那些裱好布纸的花圈框依次靠在板刀台下,就像盛白的云堆涌着断头台,精致却阴森煞眼。殊不料到翌日早上,作坊里的情形却把花工张气得要晕。这些布纸框和几件绝活框坯悉数被毁,完好的布纸上被戳穿的洞洞眼眼就是个大罗筛,框坯被撕烂、踩瘪,一大堆丢在作坊墙角。这时,冯九在店堂外敲门要进来。他原本要告诉花工张,判官头寿屋,金童玉女,他都办齐了货,只等花工张这头绝活配齐就交了板田的差。但等杏华开了门,放他走进作坊里,也气得半死。自然他关心的是那五百大洋。他问花工张,作坊里进了贼,把日本人订金偷了?花工张摇摇头说,这不是贼。古往今来,偷钱偷米偷大粪也不会偷到栀子街里来。冯九又问,那是什么人做的?花工张笑笑,这是栀子街行家里手做的,这单生意做得大,怕莫有人眼红。但他安慰冯九说,冯会长,作坊里连我有四个人手,按时交货赶得出来。他把旧花圈改头换面一节省略没说。冯九放下心,临走对花工张说,张老板,再不能生枝节了。不按时交货,你跑不脱我也跑不脱呀。
花工张、杏华和那两个花工又要把前头做的工重复一遍,时间不多不少整整两天。重复劳动令那两个花工意见好大。一个花工说,做一遍又做一遍,不是多做了事么?一个花工说,就是。先头的工白做了。杏华说,你们就是蠢,老板又不是计工算钱,是按月支钱的。硬要怪就怪是跟日本人做事,心里恨起来就痛。这些话,花工张装聋作哑没听见。是夜,各自分头睡觉去了。花工张拣场走后,他哈欠喧天地在自己房里脱衣衫,脱一件抖一件,弄出声音好大。睡到床上他又长吁短叹,辗转反侧把一床干草垫碾得咔吱作响。如此这般一番,他才算睡觉了去。作坊里安静了。月光把板刀台的身影从东边拉到西边。大约在天亮的时候,作坊里闪出一个纤秀的人影,轻车熟路地来到布纸框前,双手一举展开一块大布罩在框上,然后伸出手指隔着布去戳,戳一下那花圈框上裱好的布纸便一个洞。因为隔着布的缘故,布纸框被戮成个大罗筛也没有声音。当这人影下手要麻利、快些时,花工张房里的灯亮了,人影动如脱兔倏忽一闪就不见了。花工张似乎并不急于要抓住这个人影,甚至都不去察看这人影消遁的方向。他打开房门,慢慢悠悠地走到作坊里,拣起地上那人影来不及带走的布,是块青花包被布,是那年月良家妇女的寻常之物。这块布还有些湿润,大约是潮湿更能吸附声音。花工张来到杏华的房门口,把青花布挂在门搭上说话了,他声音很轻,似乎怕惊醒了其他两个花工。他说,杏华,我就知道是你,有哪个贼不偷钱的呢?我不怪你,你有你的情由。栀子街的天已经亮了,听得见街上寿福店开板子、做生意的嘈杂声。当花工张要离开时杏华的房门却静静地打开了,花工张看见杏华从头到脚一丝不挂地倚床站着,褪去的衣衫拢在她的脚踝边上,那皮纸窗朦朦的亮光照着她身体像布纸一样光滑、雪白。稍后,杏华又慢慢侧过身去,花工张的心就像被铁爪子紧紧揪住了。杏华这半边身体是破烂的,乳房上豁然拆裂几道暗红的伤口,愈合不好的肉蕾,弯弯扭扭一直连着腰和大腿,犹如高温下被溶解、流动而突然冷却后凝滞的物质。花工张一扭头,眼眶里甩出两行泪水,说,日本人呀,真不是人!杏华慢慢地穿好衣衫,从容不迫就像她从容不迫脱去衣衫展示苦难和悲愤一样。花工张车转身,把作坊里那些花圈和绝活框坯统统毁了。他用手撕、牙咬、脚跺,做得毫无余地。
当天,花工张早早就把张记的板子关了,把杏华和那两个花工喊到作坊里,每人送了两块大洋,告诉他们张记从此不开张了。花工张说,你们往南边跑,找条生路。遇到有事做,只管讲是栀子街出来的。这世上,有下贱的手艺没有下贱的人。花工张如是说,杏华眼中就有了泪水,她知道张记关板子的原因。她劝花工张,张老板,你也趁早跑吧?花工张说,我不能跑呀!我还要把店子盘出去,弄几个钱回来。他这话说得俨然,那两个花工信以为真。
第二天,冯九悠哉游哉地又到了张记,心里盘算着做板田这单生意,该拿多少回水。但他到作坊一看便捶胸跺脚了,说,张老板,兄弟也!日本人是板刀,说要命就要命。你不交货,栀子街就是小瀛洲呐!花工张一言不发地听冯九说话、咒他。他顺手捞根篾皮在手里,几撇几撕,那篾皮倾刻变成细如麻线的篾丝,又好玩似地几缠几绕,一个蚕豆般精巧的小花圈便立于他大拇指上。这花圈虽小做工却有板有眼,两端提耳左右对称,一副撑脚长短一致。花工张对冯九说,冯会长,你看看,点上花瓣就作得用。叹口气又说,这门手艺到我这里只怕传不下去了。冯九一听,跳起脚就骂,嬲你的二世娭毑,板田拿不到货你我都不知死活,什么家伙都留不住。花工张拉着冯九走到店堂里,把那五百大洋拿出来,说,我一个子都没动。冯会长,我的事牵扯不到你,我横竖给日本人一个交代。栀子街已是暮色苍然,竟起了些风,那风在街头街尾搜掠一遍栀子街便绝少了走动的人影。花工张也不亮灯,摸黑拿出一壶酒与冯九对盏,你一杯来我一杯去,喝得酣畅淋漓。花工张说,日本人是日本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中国人又没有请日本人到家里来,是不是?冯九说,这是国家大事,平头百姓是不懂的。花工张不服气,说,国家大事就是平头百姓的事呀?换过一壶酒后冯九熬不住了,额头泛亮,汗流如雨。花工张把一杯酒一口喝了,杯子一摔,拉起冯九回到作坊里。这次他先亮了灯,然后,在板刀台子前坐好,端端正正地坐好。板刀台巨大的阴影整个地笼罩起他。他伸出右手捋起衣袖对冯九说,冯会长,有劳你把裁刀摇起来。冯九这才明白花工张要做什么,他当然不想做这种事。花工张就说,冯会长,你不动手日本人会动手,栀子街怕是保不住呐!冯九只好摇动绞车,那百把斤的裁刀被缓缓拉起来。板刀台上有几个用木条固定的木槽,是方便裁切不同尺寸的皮纸用的。花工张把自己的手伸过去,平放在一个大的木槽里,还自言自语,我都不知道,我这只手是大花皮纸的尺寸。花工张说这话时冯九刚好把裁刀摇到位,他话没说完便一脚踢在冯九的腰上。冯九被踢到地上时只听得闷闷一响,几滴热血挟风飞溅在他的脸上。这时,午夜的月光从作坊亮瓦上照进来,清清朗朗透澈如泼水。
报纸登了,布告贴了,小岛少佐的丧事,无论如何是该城的一件大事。板田如期到栀子街张记店来拿货,栀子街头一回开进了日本人的军用卡车。那些宪兵先从车上丢下一个麻袋,然后迅速散开把栀子街几个出口封锁住。板田解开麻袋,放出早上准备出城逃命的冯九,也见到了断了右手,坐在店堂里等他的花工张。板田那张脸依然干净,表情没有变化,除了鼻翼两端那两道深刻的阴影。板田先收回在张记订货的五百大洋,然后,指挥宪兵把作坊里的板刀台搬到古槐树下。这时候,栀子街寿福店的所有花工,都被宪兵驱赶过来。他们早就听说花工张要为日本人做绝活花圈但不知个中原由。他们看见几个宪兵将花工张抬到板刀台上,把他按在木槽里要斩头时,板田突然改变了主意,指使宪兵斩他的腿。当宪兵把花工张的左腿压在木槽里时,板田又改变了主意,指使宪兵斩他的右腿。摇绞车的人还是冯九,是板田的东洋刀架在他颈根上逼他做的。花工们还记得,裁刀落下来时声音好大,整个栀子街都震动了。太阳在无云的天上,稠稠的血溢满了板刀台,从一个木槽流向另一个木槽。稍后,古槐树抖落下几片叶子掉在血的上面。
没有了半边手脚的花工张死了。那天板田对他的折磨持续了很久,把栀子街花工们的心,看得一寸一寸地痛得要命。但他的葬礼却很隆重气派,整个城南万人空巷,自发的挽联和祭奠铺天盖地。尤其是他张记店的花圈绝活,都一一展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