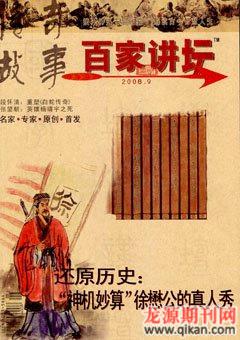疯狂的假面舞会
精彩回放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认定:从公车上书开始,直到戊戌政变,康党一直都在宣传维新变法。但真相却恰恰相反: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启超在湖南执教时务学堂时的讲义,都印证着康有为曾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康有为一边屡屡上书呼吁维新,另一边却积极准备科举考试,无不说明康有为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在戊戌年由革命倒向,维新,上演了一出首鼠两端的大戏。
本期谌旭彬先生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五、从变法到政变(上)
1.烈马选错了骑手
虽然失落,但康有为仍然决定继续留在京城。既然皇帝欣赏自己,折服于自己的维新思想,还愁没有用武之地吗?
康有为决定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
变法开始后的第10天,即康有为面圣后的第3天,御史杨深秀、宋伯鲁上了一道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骥阻挠改革的折子。
折子是康有为写的,他建议皇上罢免许应骙的一切官职,然后选择支持改革的人来接替他的职务。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推荐自己,但康有为说:“总理衙门是朝廷对外交涉的重要机构,在当前这个强敌环伺的时候……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之人,岂能胜任!”
此外,康有为还列举了许应骙两条罪状:
一、见识短浅、妄自尊大,皇上为了培养新型人才,特意在科举考试中开设了“经济特科”,而许应骙竟公然在礼部朝堂上大放厥词,说“经济特科”毫无意义,而且他还曾“腹诽朝旨”。
二、皇上下达的改革新政,许应骙统统反对。康有为在折子中愤愤地说:“皇上日夜苦于经世之才不够用,许应骙却日夜思量着遏制对这些人才的培养,真不知道是何居心!”
康有为之前进呈《彼得变政记》的主要意图是希望皇帝学习彼得大帝,通过对守旧官僚实施铁血政策来推动变法。光绪被康有为说动,自改革伊始,就一直想抓几个“反改革典型”。对许应骙的弹劾,正对上了皇帝的这种心思。
皇帝决定立即将许应骙罢职。军机大臣刚毅出面为之求情,光绪盛怒不许。刚毅又请求让总理衙门彻查,光绪也不同意。最后,刚毅提出给当事人许应骙一个上折子解释的机会。许应骥毕竟是朝廷重臣,面对这样的合理要求,光绪也只好同意。
结果,许应骙的自我辩护让皇帝哑口无言。
许应骥在折子里说:第一,当日开设“经济特科”是我和李鸿章等人一起商议通过,并请求皇上批准的,如果有意见,当时我就可以反对,何必在事后散播流言?第二,说我“腹诽朝旨”,他们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就算我真的诽谤朝廷政策,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不是肆意捏造是什么?第三,说我阻挠所有的新政举措,问题是,除了“经济特科”,其他的新政措施都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如何阻挠?
最致命的是,许应骙在折子里直截了当地把藏在此次弹劾背后的康有为抓了出来,并披露了他和康有为之间的宿怨:“宋伯鲁、杨深秀说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乎指的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康有为与臣是同乡,他初次进京,就终日打着西学的幌子,到处奔走于权贵之门。其中曾经到臣这里求见过三次,臣鄙视他的为人,三次都拒绝相见。后来康有为又在广东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达两百多人(这已经违反了清朝的禁令),臣恐其滋事,又将其取缔。从此,康有为就与臣结下了私怨。”
考之史料,这段康、许结怨的过程,许应骥并没有说谎。
最后,许应骙历数了自己几十年来讲求西学的履历,声明自己对改革的意见只是提倡务求实际,反对虚华而已,如果这样也算反对改革,那么就请皇上罢免自己的职务。
看到许应骙有理有据的自我辩护,此前还盛怒不已的皇帝蒙了。他本来想抓一个反改革典型,杀鸡儆猴,但现在看来,这个典型无疑是抓错了。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让许应骙不必辞职,只是警告他说,今后要更加勤勉,尽职尽责。
表面上看来,康有为的算计是失败了,但实际上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大臣,最后收到警告的却不是弹劾者,而是无罪的被弹劾者,皇帝的偏袒一目了然。
通过这次无中生有的弹劾案,朝廷上下无疑都看出了光绪皇帝存有让康有为主持维新新政的意图。此外,标榜民权的康有为以“腹诽朝旨”这样荒唐的专制社会特有的标志性罪名来弹劾他的政敌(私敌),也可见他从来就没有实现自己思想上的近代化。他维新思想的实质,非常值得怀疑。
改革的烈马选择了这样一名蹩脚的骑手,要想到达目的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把马累死,要么把骑手摔死。而戊戌年那场荒唐的赛马会,累死的是马,破产的是在这匹马上孤注一掷的赌徒光绪,而骑手康有为却溜了。
2.总督和皇帝的区别
就在鼓动宋伯鲁、杨深秀弹劾许应骙的同一天,康有为也在为自己接替许应骙的位子而作准备。
他在擦屁股。
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自己最得意的著作——《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是以商定教案法律(用儒教对抗基督教)、厘正科举文体(改革科举)、请求在全国各乡镇设立文庙、尊师保教等名义进呈此书的。在奏折里,康有为对皇帝说:“外国在中国到处建有教堂,动不动就以教案为借口挑起冲突,然后挟持国力,以兵相迫。结局则是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削割,举国震骇。愚臣我久思补救之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变法。而变法之道,则在于开教会,制订教会法律。”
康有为建议让孔子的嫡系后裔衍圣公做教主(可是这个新孔教的“教义”却是他康有为阐发出来的,所谓“教主”显然只是虚衔),开设孔教会,让所有的王公士庶都入会,各省府、县一律创办分会。然后让孔教会和西方各国的基督教会交涉,共同订立“两教和约”,制订“两教法律”,以后再发生教案,就依照这些规章法律去办,这样就不会再有被逼割地赔款的危害了。
说实话,康有为的办法可真够异想天开的。当然,救国建议的不切实际并不妨碍一个人的爱国情怀,可惜的是,尽管康有为向皇帝罗列了一大堆进呈《孔子改制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仍然无法使人相信他的爱国情怀,无法使人相信他的这些自我解释。
只要把《孔子改制考》的公开刊行本和康有为的进呈本作一个简略的对比就会发现:在康有为的笔下,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孔子、两种孔教。虽然是一本牵强附会、粗制滥造的伪学术作品,但公开刊行本中的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中的孔子却已降格成了君权纲常的维护者。
例如:刊行本中有一篇一千多字的序言,集中论述民权社会的高级形式“大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却将这篇序言删掉,另写了一篇主旨在于“尊圣扶教”的序言。在新序言里,康有为居然肉麻地感叹道:“(孔子道统丢失的后果)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坠将湮,岂不畏哉!”公然拥护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
再比如:在公开刊行本中,康有为极力颂扬民权,提倡人民自主自立。在《孔子为制法之王》篇中,康有为说:“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但到了进呈本中,这种否定君权神圣的句子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君权的极力肯定和鼓吹:“(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
可见,康有为的学术纯粹是一种靠东拼西凑、牵强附会构筑起来的伪学术,康有为本人无疑也只是欺世盗名的伪思想家。因为真正的思想不能出自抄袭,不能出自异想天开的想当然;真正的思想家始于严谨,终于坚持,也绝不会这样肆意糟蹋自己的“思想”。
进呈本与刊行本的巨大差异,与康有为地位、处境的变动是同步的。自从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孔子改制考》就成了令康有为坐立不安的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他已经得到的一切恩宠炸个烟消云散、流水落花。此前,翁同稣之所以对光绪皇帝说康有为居心叵测,就是因为他读到了宣扬民权、贬低君权的刊行本《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当然明白:过去自己不得志,朝廷的言官们自然没兴趣对一个小人物发起攻击,所以刊行本《孔子改制考》也就一直没有给自己惹什么大祸。但如今自己已经得到了皇帝的青睐,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更何况自己马上就要取代许应骙的位置),树大招风,《孔子改制考》的屁股已是非擦不可。
此时距离皇帝召见,康有为得知自己被宠信的6月13日仅仅过去三天,显然康有为是自当天面圣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篡改《孔子改制考》的。这也可见康有为在行动和思想上,对“革命”的背叛是同步的。
康有为果然有先见之明。进呈《孔子改制考》不到一个月,大学士孙家鼐就上奏请求严禁悖逆之书,指责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引导天下人犯上作乱——在此之前,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时,竟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列入必修教材,出于谨慎,孙家鼐于是找来《孔子改制考》一读。
孙家鼐读到的,自然是公开的刊行本。
随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请求皇帝降旨令康有为销毁《孔子改制考》,御史文悌等人也以《孔子改制考》为证据,攻击康有为倡言民权,怀有异心。
但他们统统没能扳倒康有为。
他们哪里知道,皇帝和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同一本书。
遥记当年在南京,张之洞对康有为说:“只要先生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我一定竭力供养。”康有为当时傲然回答:“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区区一个两江总督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总督和皇帝的供养,果然是云泥之别。
3.走投无路,回归制度局
戊戌年正月份,康有为曾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帝在中央开设制度局,作为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下设十二个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则一律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推行新政。黄彰健等史家告诉我们:这是康有为在企图架空国家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行政机构,可谓野心勃勃。但康有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架空原来的中央六部、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各地方督抚衙门,制度局在他的构想里属于“议论”机构,原有政府机构则属于“办事”机构。
康有为的解释真可谓此地无银,狗屁不通。所谓“议论”机构,也就是国家发号施令的脑子;所谓“办事”机构,也就是国家执行具体政策的手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垄断了脑子,手足难道不是傀儡吗?!
何况,康有为根本就没想让现有的中央六部一直到地方督抚衙门在维新这口大锅里分到半勺羹,甚至连傀儡都没想过要让“办事”机构去担当,所以。他建议皇帝:“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康有为还建议让王公大臣担任制度局的总裁,制度局的会议须由皇帝亲临主持,再选一些“天下通才”去制度局值班。至于给自己留的位子,据康有为自己的说法,翁同稣(此刻尚未与康反目)曾经表示愿意推荐他去制度局当值。
这样评价康有为的政治动机,在许多人眼里,恐怕又不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然而,历史的真相总是如此让人失望。
在获悉翁同稣因反对自己而遭受光绪皇帝的严厉斥责后,6月13日,康有为抓住时机,又写了一道自己推荐自己的折子,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给皇帝,于是3天后皇帝亲自召见。
深知自己已经获得皇上青睐的康有为,在替徐致靖写的折子里已经绝口不提制度局的事情了,相反,他得寸进尺,大力建议皇帝任命自己做他的贴身顾问,开始做起“帝师”梦来了。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康有为的一厢情愿发展下去,慈禧太后的干涉,让他与翁同稣罢职后留下的空缺失之交臂;随之他又想挤走许应骙,让其为自己腾地盘,结果也未能如愿。忙活了大半年,他仍然只是个六品工部主事,兼职在总理衙门实习。
于是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康有为,居然又折回到开制度局的建议上来了。
上奏弹劾许应骙、呈递《孔子改制考》的同一天,康有为还给光绪上了他一天之内的第三道折子:“臣以为,皇上若不想变法图强也就罢了,若想变法图强,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开制度局不可。”
对康有为的建议,光绪是一百个赞同。对慈禧的旧班子,皇帝一直心存芥蒂,若能借变法之名,对中央到地方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何乐而不为。
皇帝将康有为的提议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衙门总署动作迟缓。光绪屡次动怒,责令他们限期拿出意见,庆亲王奕勖承受不了皇帝的压力,转而去颐和园求助。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向奕勖交了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拖了一个多月之后,7月2日,总理衙门终于拿出了讨论结果:一份对康有为的建议逐段批驳的冗长报告。
康有为自己也觉察到了巨大的抵制浪潮的存在,他在(《自编年谱》里回忆:
“我请求在京城开设十二局,外省开设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纷,都说我想将内阁六部以及地方督抚、藩臬司道全部废除架空……于是京城震动,外省惊悚,谣言诽谤不可听闻。军机大臣们说:‘开设制度局,是要取代我们军机处,我宁愿抗旨而死,决不能让它开起来。”
康有为的人品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他曾自我解释,为什么一直提倡民权的他反而要在戊戌年极力阻止朝廷开设议会,说是因为满朝都是守旧大臣(这只是康有为的看法),开议院会给变法带来许多的阻力。但是他一直怂恿皇帝开设制度局、十二分局、地方新政局,带给新政的阻力较之开议会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史家们总是一再批判顽固派的自私自利:“这些王公大臣虽已老朽昏庸,但在切身利害面前表现出异常的机智和清醒。他们一语中的,明了开制度局是要废去军机处,夺他们的权。权力就是生命,岂可让人!”(《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