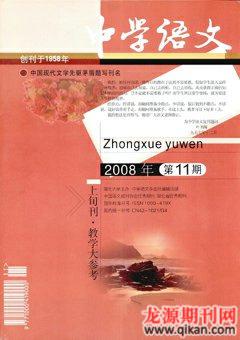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山水游记文源流考
郑晓娟
中学语文教学无论怎样改革,文体教学和学习应该是一个始终不变的观念和思路。但在语文课程改革的今天,语文教材中的文体意识逐渐淡化,学生的话题作文中也经常出现“四不像”的表现形式。从语文教师自身来说,文体意识也并不是特别明确,许多教师对每种具体文体的渊源流变和发展变化了解得不是很清楚,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一种文体的产生、兴起、发展、变化、废止,是有其必然性的。对此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是语文教师必须具备的业务素质。本文就古代山水游记的源流演变作简单的阐释,以期对语文教师的业务学习和能力提高有所帮助。
山水游记,是我国古代以“记”标体名篇的记叙性文体中的一种。
从文体的起源来看,“记”体之文在古代的各种文体中,是出现和使用最早的,而且,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史学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②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也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③这就是说,为了备忘,所以才有了史官;而记言、记事,自一开始就成为古代史官的基本职能,也因此,成了“记”体之文的性质功能。
“原始以表末”,是古代文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记”体之文的起源,有一种说法认为“记”之为体,是起源于《礼记》中的《学记》、《乐记》。这种说法,仅着眼于文体名称的文字表面,尚缺乏对文体名称的意义做更深入的考察和辨析。《学记》、《乐记》中的“记”,并不是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名称,而是一个训诂学中的术语。这正如“春秋三传”中的“传”,这里的“传”,不是文体名称“人物传记”的“传”,而是“传注”、“解释”的意思;《学记》、《乐记》中的“记”,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含义。④我国古代的经学家,把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用以直接注释“经”书的著作称之为“传”,把间接阐发“经”书之义的文章称之为“记”。所以,《学记》、《乐记》中的“记”,实际上是孔子之后的弟子及更后的儒学者研究、阐释《礼》经的文字篇章,而非“记言”、“记事”的记叙性文章。如《学记》,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的教育学论文;《乐记》则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的音乐学理论文章。考察《乐记》中的两段著名文字,问题就更清楚了。“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也者,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⑤第一段文字,阐释了声与政通、解说性的文字,明显地区别于记言、记事的记叙性文字。因此,说“记”体之文源于《学记》、《乐记》,是只看表面文字,不看实质意义的妄断,不能成立。从文体的性质功能来考察“记”体之文,早在《尚书》中就已经出现和使用了。陈懋仁说:“《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但是,《禹贡》、《顾命》虽然具有“记”体之文的性质功能,但毕竟还没有用“记”来正式标体名篇。具有“记”体之文的性质特征,且又用“记”来标体名篇的,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本文要考辨的山水游记,是古代“记”体之文中的一种。这种“记”体文的基本文体特征是:专门用来记游,是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它的记写对象和内容,是山川胜景、自然景观,并通过真实地记写作者旅游中的见闻,来抒发他由此引发的真切感受。依据现能见到的文章,古代的这种山水游记,起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到明清之际,则成为散文中的重要一体。
晋代,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是古代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虽然著名中标体为“诗序”,但同时还题名为“游”,现考其性质内容,实则是一篇游记。文中,作者不仅以生动的笔调,真实地记写了自己寻幽探胜、游览山景的经过,而且细致真切地写下了自己在游览中的愉快喜悦之情,记述游踪,描写山水胜景,抒写心情感受,开后代游记文之先河。
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则标志着古代山水游记的成熟与定型。柳宗元被贬官永州,在这里呆了十年。这十年之中,他曾各处寻游,而且以简洁、生动、形象的语言,记写下所到之处见到的奇特景观和秀丽景色,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真实的心境,并借此含蓄地表达对自己身世遭遇的不平和激愤。如其中的《小石潭记》,写漂水,写岩石,写竹木,写游鱼,着墨不多,却笔笔有神,文采飞扬,使所写景物如在眼前。文中最精彩的文字是写潭中之鱼:“漂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写得真真切切、历历在目、形神毕现,极生动、极逼真。而写潭中鱼又是为了衬托潭水之清澈透亮。结束时写自己的感受、心境:“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周围竹树环绕,不曾被人发现,所以没有人来,因而这里的环境过于幽静、冷清,使人感到神凄骨寒,呆不下去,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以文体发展的角度论,《永州八记》一出,明确确立了山水游记的基本类型,奠定了山水游记的规范体式。
但到了宋代,就像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样,山水游记文也出现了议论化的倾向。这时的游记文作者,往往在文章中借写游踪,写风景来议论说理,于是又开辟了古代山水游记文的另一条路径。如果说唐代的山水游记文是以描写自然风光、表现自然美、富有想象和联想、充满真实感受而见长,宋代的山水游记文则以议论说理、借题发挥、富有理趣、充满哲理思考而见长。这是游记文的一种变化、发展。例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以文题而论,这当属一篇典型的山水游记文,但文章的中心和思想精华,却是作者借记写这次游山,而发挥、阐述的道理。作者与同伴游褒禅山洞,但并未游完全程,因越往里走越难、越险,所以只进入山洞一部分就退了回来。退出之后,作者追悔不已,深刻反思,总结体会,并发议论,写下了这篇游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是就游山而发议论,但其阐述的道理却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他是在谈做事和治学。
文中,作者首先概括了一种普遍现象,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规律。“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没有危险、没有困难、距离近的、不需要付出多大努力的地方,去的人多;而有一定危险和困难,距离又比较远的,需要付出较多努力的地方,去的人就少了;大自然中那些奇特的、美丽的、不平常、不一般的景观,恰恰是在险而远的地方,所以就很少人能够去得了、能达得到,只有有志者,不怕危险和困难、意志坚定不动摇,才能到达那样的地方。人们从事任何一项事业,包括治学在内,要想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境界、一个更远更大的目标,就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坚定不移的决心、毫不动摇的毅力、奋勇向前的精神,这样,才能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全力以赴、永不退缩,才不会半途而废。作者的议论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层次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思考,再深一层探讨:“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如果说:“志”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那是人的主观条件;那么,还必须同时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这就是“力”和“物”。这两者若不具备,最终还是不能达到一种美好的境界,理想的目标。在这个层次的议论中,作者在论“力”和“物”的同时,还两次提到“不随以止”、“不随以怠”。作者虽然没有就此特别阐发,但他注意到了、体会到了、认识到了,所以不忘提到。他要表达和强调的是,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轻易地为别人的意见和想法所左右而改变自己的决定,有了目标追求就不要轻易放弃,那种一味附和与跟随别人,做事没有自己的主见的人也很难有所成就。
以上,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分析论说系统。在完成了这一分析论说之后,作者还没停止自己的思考,继续推进自己的议论说理。接下来,又专门对“志”与“力”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这里讲了两种情况:一是“力足”未能达到,所以自己感到后悔、遗憾,而且还被别人讥笑。为什么呢?是“力足而未尽志”。二是“尽志”未能达到,所以自己不感到后悔,没有什么遗憾,也不会被别人讥笑。为什么呢?是“尽志而力不足”。前者是讲能做而未做,后者是讲尽心尽力争取去做,作者赞扬和肯定的是后一种做事的态度。
我们看这篇山水游记,其写作中心显然是在议论部分,文章中,记游成了发表议论的由头,由记叙引出议论,转为谈感想、讲体会、说道理;而且议论说理步步深入、层层推进,行文展开有很强的逻辑性,思想缜密;虽是借题发挥,议论又处处扣题,不离不弃,引发自然贴切。因此,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成为古代山水游记的别开生面之作。
南宋后期,游记文又出现了一种日记体的新形式。作者因某种原因,要长途旅行,在旅行途中,他把一路上所见到的山水胜景、自然风光,按日期记写下来,于是就成了一种日记体的游记。这种游记,既写行程,又写游踪,内容丰富多彩:写景物、记名胜、叙风俗、作考证、咏历史、抒情怀。因此,既有很强的文学性,文笔优美,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供研究。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夏天,从家乡山阴动身往四川的夔州任所,取道长江,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按日记之,遂成《入蜀记》。范成大则于淳熙四年(1177)由四川成都东归家乡江苏吴县,也是用日记的形式,写沿途风光,一路见闻,故称《吴船录》。这种形式的游记,最著名的当为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徐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徐宏祖是明末一位著名的旅行家,20岁便立志远游,其后三十年的时间内,他徒步旅行,几乎遍游全国的名山大川。他用日记写沿途风光和各地民俗风情,并考察山川地貌,形成了二百多万字的旅游日记,经后人整理,编辑刊行,题名为《徐霞客游记》。这种日记体的游记,合则为一部文集,分则为单篇小品,其基本风格是重在纪实,朴实无华。
以单篇的游记而论,明、清两代,这种山水游记文大量产生,明、清时期很多文人的文集中,都收录有山水游记。因此,山水游记已成为这一时期散文中的重要一体,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山水小品文。而且,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又特别讲究和追求“独抒性灵”,因而,许多游记文,写得题解精美别致、清新动人、富有意境之美。如,袁宏道的《西湖》、《满井游记》和《晚游六桥待月记》;袁中道的《西山十记》;徐宏祖的《游黄山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白洋潮》、《湖心亭看雪》;姚鼐的《登泰山记》等,这些文章都是享誉文坛的游记名篇。我们即以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为例,作简要评析,体味这一时期游记文的风格特点。
张岱虽出身仕官之家,却没有做过官,因而在政治仕途上落拓不羁。由于性喜山水,明亡之后即隐居剡溪山村。他是晚明时期的一位重要散文家,不拘门户,采纳众长,反而使他的作品独具风格。《湖心亭看雪》即写出了一种特别的境界。全文仅有159字,是名副其实的小品文。但文虽小,却以大手笔出之,作者凭借他精深、厚实的文学修养和驾驭文字的功底,在极短的篇幅中,用极准确简练的文字,写出了精美动人、别有情趣、清新灵性的大景观、大气象、大境界。“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段文字,在开头“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这样的交待和铺垫的基础上,集中写“看雪”所见的景物,是全文的中心。“湖心平眺”,原本是西湖一景,湖心亭是一处观景点。往日,若是天气晴好,游人如缕,络绎不绝。而眼下,三日大雪,“湖中人鸟声俱绝”,可作者偏偏要“独往”,而且是在夜晚“更定”之时,这使人想到作者游兴之浓近乎痴,也使人想到作者非同一般人的个性、情趣。自然的,作者笔下写出来的所见也就不同凡响。明明是他坐小船于湖中,而写看雪时的视角、立足点,却跳到湖岸,眺望湖中,这就给人以意料之外,也正是作者写景构思的独到之处。作者让自己跳出画面之外,视野开阔了,才能见到全景,才能写大观。于是作者的笔下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幅西湖雪景图:湖面之上,雾气、水气,弥漫氤氲,交混融合;天上的云、远处的山、湖中的水,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全都是迷蒙蒙、白茫茫、混沌一片,一切皆白;湖中的长堤成了模糊不清的一线,湖心亭成了隐约可见的一点,本来就小的船成了水上漂浮的一根小草,船上的人成了看不清人形的两三颗微粒。在这里,作者运用反衬的表现手法,以微观显宏观,以微小衬阔大,把铺天盖地、阔大壮观的雪景别致而又准确地再现出来。作者这样写,也许在他的心底深处确有这样的感触:在广阔的天地宇宙之间,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个体,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
作为一篇游记,作者虽然紧扣题中“看”字,写自己的所见,但他又突破以游踪为线、移步换景的传统写法,置身于景物画面之外,选择一个固定的立足点来“看”,这是一个创新。另外,这篇游记,也并不是作者游湖看雪的当时之记,而是事后凭回忆写成的。作者之所以要撰写此文,就是要实践独抒性灵的写作主张,把文章写得清新飘逸、洒脱自如、富有情趣韵味。这也正是明、清两代山水游记所追求的一种风格,整体呈现出来的一种时代特点。
————————
注释:
①杨照明:《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2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徐时曾:《文体明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④王凯符:《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⑤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通联:山东德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