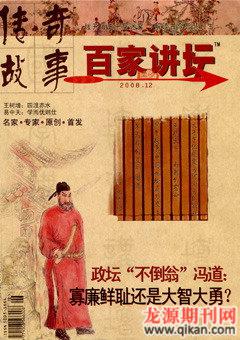朱元璋的反贪困局
黄 波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还有颇好的口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官吏非常严厉,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既然官权受约束,民权自然就能出头,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明中叶的著名清官海瑞就曾经非常仰慕地赞叹,说太祖对鱼肉百姓的官员不惜施以惨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是历史上的“千载一时之盛”。直到1955年,吴晗先生在一篇论文中谈到朱元璋反贪时仍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朱元璋下定决心,随犯随杀,甚至严厉到不分轻重都杀,对贪污的减少是起了作用的,对人民有好处,人民是感谢他,支持他的。”
对上述论断,有几个问题值得一说。朱元璋对待官僚队伍十分苛酷,原因就在于怕这些人上下其手,贪污、害民,而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在挖他王朝大厦的墙角,非痛下辣手不可,所以,洪武一朝,“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反贪最为严厉,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而朱元璋也堪称最恨贪污、处置贪污最不留情的皇帝。
但是,朱元璋反贪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完全都是积极的,还大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朱元璋大力约束官权,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权的扩张,并由此导致百姓的安居乐业?恐怕并不尽然,朱元璋以严刑峻法为后盾的强力控制,不仅是针对官员,也是针对平民的,洪武朝并非只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百姓的盛世。
其次,朱元璋的反贪虽然足够铁腕狠辣,但是否就说从根本上遏制了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其反贪效果不佳,是连他自己也要忍不住大感沮丧的。在朱元璋的反贪风暴中,有很多冤假错案,对那些无辜者,今之论者能否仅仅因为他们是官僚集团的一员,就站在一旁拍手称快?
面对这么多问号,我们对朱元璋的反贪肯定无法单纯给予掌声。作为一个现代人,在道德评判之外,更应该思索的是:朱元璋真心反贪,其手段又如此严厉,为什么最终还是陷入了一个宿命的困局?
教化与刑杀的两手
朱元璋反贪,放在那个时代来说,几乎已穷尽其技。
他可以放低身段,对官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洪武初年,各地府、县的官吏来朝,他对这些手握百姓身家性命的人说:“现在天下新定,老百姓生存维艰,就像鸟儿初飞和树苗刚栽下去一样,你们可不要拔鸟的羽毛和撼动树根啊。”这是诱导官员激发“天良”,希望他们不要逼百姓太狠,以免重蹈元王朝覆灭的命运。
朱元璋并非只会杀人,他一样擅长对官员做思想工作。他曾经打过两个比喻:一日“今汝俸禄,有如力田”,二日“守俸如井泉”。意思是说,国家的俸禄相比贪污得来的横财,当然少了点,可是好在“岁享其利,无有已时”,而贪污所得,一旦事发顷刻立尽。
在廉政教育上,朱元璋也是煞费心机。洪武二十五年,他命户部备录各品级文武官员一定的禄米数,并据稻谷出米率换算成用谷数,又写明田亩的粮食产量和付出劳动的多寡,汇为一书,命名为《醒贪简要录》。官员们从朝廷里领的禄米,费谷多少石,种田的农民又会付出多少劳动,一目了然。太祖希望用这样真实的数据教育官员,诱启他们的惻隐之心。这本《醒贪简要录》很有可能是最早的“廉政教材”。
从这两个比喻和这本“廉政教材”中,颇能看出朱元璋的苦心。
当然,朱元璋最为人熟知的,还是对贪官的残酷打击。当时官吏贪污白银60两以上就要被处死,贪污80贯则处以绞刑。朱元璋在处理贪污案件时,又往往法外用刑,诸如断脚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抽肠、剥皮等很多不载于法律的酷刑。据野史记载,当时各地都特建一庙,专门作为剥皮的场所,谓之“皮场庙”。贪官被押到那里,先砍下脑袋,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往人皮中塞满稻草,成为人形,摆在衙门里作警示之用。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反贪喜欢大搞株连,一个案子事发,常常要因此倒下一大批官员。像有名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一案,牵连其中而丧生的高达数万人,真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据说,长期在恐怖氛围中讨生活的官员们看出了一点朱元璋喜怒的规律,哪天朱元璋的玉带被按在腰下,便是大开杀戒的信号,若这根带子到了胸前,官员们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以刑杀辅助教化,大肆屠戮,无疑会对官僚阶层形成很大的震慑作用,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视人仕如畏途,有的宁愿毁损肢体也不愿为官;其次是其中积累了很多冤案。朱元璋的反贪有时候全凭捕风捉影,而这些风和影,他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照样大开杀戒。所以对那些冤魂,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们是官就一律称赞杀得好。
民拿害民官吏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把“制度建设”四个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作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反腐问题上,“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首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都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和他颁布的其他许多政策一样,仍然具有浓重的朱氏色彩,如:
设登闻鼓。“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这个鼓是专门鼓励百姓击鼓告状的,为了防止走过场,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查看,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由御史带着上奏。
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级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相当于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在各个地方巡视,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禀报,小事则可以径行处理。
设置特务机关。检校、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人员,是皇帝的超级耳目,任何官员都在其侦听、窥伺范围之内。特务机关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图谋叛乱,而掌握其贪污不法的劣迹也自然包含在内。
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数“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大诰》中。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颁布的“严禁官吏下乡”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对“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压良善的贪墨之吏,允许民间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领青壮年将其绑缚,押到京
城,而且谁也不能阻挡,“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官吏下乡常常扰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许官吏下乡,这样一条法令当然是荒唐的。官员是否扰民,关键不在于是否下乡,他不下乡,难道就不会扰民害民了吗?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此就有激烈的抨击,他说:“官员不下乡,则其对辖区内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必然懵懂无知,如何行政?不许官吏下乡,那些喜欢偷懒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乐得以此为借口优哉游哉,而想做事的官员却被活生生束缚了手脚,简直是因噎废食!”
沈家本的批评合情合理,如此一来,随“严禁官吏下乡”命令而来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
首先,这一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个人的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
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显而易见,其风险是非常大的。虽然《大诰》中没有明确表示,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大胆的百姓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所谓“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象,任何一个百姓在遵照圣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谁都明白,所谓“害民”与否,这个界定相当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间常常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皇帝派人查证,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在权威对民间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说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准备拿获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许正是缘于上面一些因素,“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没有结出很好的果实。史载,朱元璋的命令颁布后,真正撞到了枪口上、被“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区区两三例而已。如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肆为非,害民非止一端”,“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壮拿获赴京”,李添奇被斩趾;又有河北某县主簿汪铎等人“设计害民”,“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绑缚赴京”,汪铎被处死。可以看出,就是这区区两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罢了,由此也可证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未能够普遍而有效地实行。
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单靠个人拍拍脑袋就出台政策,哪怕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怕这个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也是一定的。不过,朱元璋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众力量来监督和惩治贪官污吏,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只要想想传统社会官威积重难返的现实,就不应该低估这一制度中蕴含着的深长意义。只是这制度突破的一点星火,限于历史的主客观条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罢了。
奈何朝杀暮犯
朱元璋铁腕反贪,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风,他不断掀起反贪风暴,眼皮底下却闹出了产部侍郎郭桓的贪污大案就是一个证明。越到晚期,朱元璋的反贪手段就越残忍,他对反贪的效果就越悲观。他不止一次地如此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朱元璋的反贪,为什么会陷入困局?
像朱元璋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王朝,其本身就是孕育特权阶层的温床。民众对官僚没有基本的监督和控制权,必生蠹虫,这应该是一个根本的症结。由于民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是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也会渐渐变质。
就拿上面所说的巡按制度为例,朱元璋设置巡按御史,本意是靠他们在地方上厉行监督,使地方官员不敢犯法,所以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但这些御史们并非个个是圣人君子,即握有皇帝授予的大权,难道就不会为了私利,打击正直的地方官员,甚至和贪黩者串通一气,瞒上欺下吗?如此一来,多了一个巡按御史,对正直守法的官员来说多了一层掣肘,而对百姓则更糟糕,饿狼之外又来一虎矣!事实上正是如此,明王朝的巡按御史制度越往后,其弊端也就越多。究其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制度本身。在皇权中心下,任何一个反贪的制度,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局限。
而从“技术”上分析,朱元璋的反贪还有下列缺陷:
他对官员过分苛刻。朱元璋是个小农思想极重的人,史家皆称“明官俸最薄”,他最喜欢看见谷满仓,恨不得手下官员只做事不吃饭。一个四品官员被罢官后因缺乏回家的盘缠,竟不得不将4岁的女儿卖掉凑钱,朱元璋听说后不悲悯也不反思,只觉给圣朝丢了脸,将其处以腐刑,可这有丝毫补益吗?想用最低的成本豢养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又指望这些人天良发现不贪不占,对下爱民,对上尽忠,如何可能呢?
朱元璋的铁腕反贪,很大程度建立在他对官僚集团不信任的基础上。官员动辄得咎是洪武朝的家常便饭。吴人严德珉由御史升任左佥都御史,仅仅因为以疾求归,便引起了朱元璋的疑忌,将其脸上刻字,流放到边远地区。到了明宣宗时代,这人还在,有人见他脸上有字,便问他当年犯了什么法。他回答说:“太祖时国法甚严,做官者很难保全,那顶官帽可不好戴啊。”说罢竟向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这四个字,着实让人感慨无限!
皇帝和官僚集团没有建立起码的信任关系,就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官员们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普遍因循守旧、畏法保位的大势下,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二是因怕官员在一个职位呆久,滋生流弊,所以要频繁变动。这本来也是防贪之一法,可是朱元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史》说,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平均不到一年换一个,刑部尚书也是如此。这可都是正部级的高官,是要思考和策划方针政策的啊,如此频繁地更换,往往自己的计划刚刚实施就挪了地方,又怎么能够指望在这些人中诞生治世之能臣?
朱元璋又过于看重反贪中残酷手段的威力。乱世中起家的朱元璋很迷信暴力,总对人宣扬元王朝丢天下是因为“过宽”,所以他自己要以猛治国,施之于严刑峻法,殊不知刚猛的东西终究是难以持久的,这就像一张拉得满满的弓,如果始终不松懈就一定会绷断一样。
清末沈家本评价朱元璋的反贪,认为他没有找到问题症结,只是一味地依赖暴力,“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无论多么让人畏惧的“威”,终有“竭而不振”的一天。
事实证明,沈家本一语中的。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