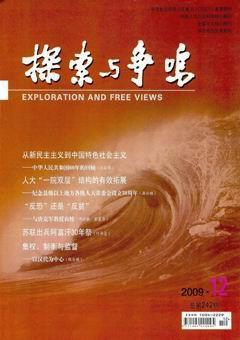劳伦茨·冯·斯泰因的社会—国家思想
徐 健
内容摘要 劳伦茨·冯·斯泰因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整体国家”学说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的社会—国家思想在德国的思想语境中,吸收了19世纪初浪漫主义“有机国家”学说和黑格尔的现代国家观,并通过对工业化时代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德国政治现状的考察,形成一种学理综合。斯泰因的社会—国家思想,尤其是他对政府行政提出的见解,具有鲜明的现代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劳伦茨·冯·斯泰因 社会国家 人格思想 社会行政
作者徐健,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对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古已有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到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经典作家对两者关系时有高论。然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及思想家的谱系中,德国偏向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因不被视为主流而被遮蔽,劳伦茨·冯·斯泰因的名字自然也就被淹没了。
劳伦茨·冯·斯泰因,1815年11月15日出生于当时属于丹麦的什列斯维希公国的艾肯福德,1890年9月28日逝世于奥地利维也纳,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整体国家学说”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运用哲学、历史学、法律、经济学、政治和社会学方法对国家与社会、经济与正义问题进行观察。他的三卷本名著《法国社会运动史》(1850年)不只是描述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而是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深度后人很少能望其项背。该书奠定了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不仅如此,劳伦茨·冯·斯泰因还是杰出的国家学和行政法学家,其先后出版的8卷本《行政学》著作对政府行政提出了许多不朽见解,获得了极高声誉。
一
在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谱系中,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是强调政治自由的孟德斯鸠传统,其政治界定社会、权力制衡的思想为社会和国家分离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二是洛克传统,主张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视社会为一种外在于政治的综合性实体。[1 ]无论是哪一种路向都以社会契约论为出发点,其根本都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这儿是国家,那儿是社会。不仅如此,国家还只是一种社会设备,是由人一步一步按照社会演进的需要发展而来的。社会有如基础,国家即于此基础上发展而为的特殊的权力机构。因此,国家的作用,普遍被认为只是仲裁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工具而已。国家执行最低限度的强制性工作,把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争执限制在和平与法律所必需的最低范围内,而它本身则严守社会组合与阶级纷争所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在劳伦茨·冯·斯泰因的眼中,国家与社会也存在着对立关系。他认为国家是人格化的有机体,通过内在的自律、意志和行为可以充分施展个性。国家是独立的机制,是由思想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个拥有思想的国家的目的是要建立全体的自由。那么,什么是社会呢?社会是自然生命要素中的等级社团,是物质生活的组织,它满足于各自的利益,追求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是依靠财产来保障的,个人在获得财产、取得独立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他人的不自由和依附地位,因此社会就被分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独立者和依附者、自由阶级和不自由阶级。国家和社会就这样始终处于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国家努力克服社会的原则,支持无产者参与国家公益,并通过行政保证其生存,另一方面有产者试图控制国家政权,以便借助权力的保护占有社会财产并维持其社会统治,国家被看成社会权力的工具。”[2 ]
在国家与社会的斗争中,国家是没有光明前景的,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是抽象的存在,在现实中它只能通过人类社会来实践,表现为具体的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沦落为一种工具,国家权力属于有产者,有产者控制国家制度和国家行政。换言之,宪法和行政用以维护社会现状,它是建立在保护有产者统治、无产者依附的基础上的。
显然,斯泰因所理解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不完全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因为斯泰因所定义的“国家”是以思想为原则的,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只是社会的衍生品。它是超越社会的,是最大的政治团体,它本不应该与社会对立,因为它本身就是社会。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没有对峙的关系,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并立,应当是“国家之为社会” [3 ],国家是作为社会的国家而存在的。只不过这个超越社会的国家在现实世界中被社会的利益原则俘虏了。因此,这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会是古典自由主义式的简单否定,它们彼此相互依存,归属于一个更高的原则——人格。国家与社会实际上代表着人性中的两种可能性,前者是道德自由,后者是利益满足。在斯泰因那儿,国家与社会终于找到了契合点。而这个“人格思想”,实际上正是斯泰因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国家。
二
斯泰因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有其思想源流和文化传承,它处于德国的思想语境中,吸收了19世纪初浪漫主义政治思想家亚当·米勒的“有机国家”学说和黑格尔的现代国家观,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学理综合。
德国的现代国家理论形成于1800年左右法国大革命时期。1790—1796年间,仅讨论国家问题的出版物便达到900种之多。德国自由派的思想是分裂的,对国家的态度不一而论。以卡尔·罗泰克和特奥多·韦尔克为代表的南德自由主义者接受启蒙思想,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而其他的自由派人士如弗里德里希·达尔曼等却表现得模棱两可,一方面拒绝把国家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相信国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是超越一切的神圣秩序,另一方面却也承认社会的自由和权力。随着法国革命趋向激进,德国思想的主流越来越怀疑现代国家起源的古典理论——社会契约论,保守的历史“有机国家”理论就在这种环境下悄然诞生了。该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正是亚当·米勒(1779—1829年)。
1804年,米勒出版了《对立学说》,奠定了“有机”理论的基础。该书认为,一切生活建立在自然和精神、社会和政治彼此矛盾的对立和紧张之中,并将通过对立面的“联姻”达成更高级的整体,美好的生活和进步运动将诞生于一个社会有机体中。多样性的统一是对立思想的核心,“整体性包含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整体性的表达”[4 ]。1809年,米勒又出版了另一名著《治国术原理》,建立了浪漫主义的国家学体系。在他看来,国家应该是从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超个人机构,而不是依靠理性在绘图版上创制出来的;国家不再只是形式和秩序,而是鲜活的运动和积极的概念;国家不再局限于实现经济、军事、政治和法律目标,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富有生命的完整的有机体。“国家的整体性”指的是社会中各个自由的、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成分之间,通过力量均衡所达成的有机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说,它是超越社会各个冲突阶级之上的,维护和保障着全体的利益。
斯泰因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首先接受了米勒的“有机”理论,他也承认国家是自土地与血统中生长出来的,充实而有生命的。其次是米勒的对立学说,只不过米勒在他那个时代所看到的对立,更多地存在于传统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而斯泰因所指称的对立则是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以及作为自由原则体现的国家与利益原则表达的社会之间。毕竟在斯泰因生活的时代,工业社会已经到来了。再次,米勒的“整体性”国家在斯泰因理论中也有表达,这就是具有“人格思想”的国家。人格以及人格的自我认定将成为社会自由运动的承担者,消弭社会中的一切对立因素,并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达成整体的自由。最后,斯泰因的国家学说不是静态的,一如米勒所倡导的那样是一种鲜活的运动,把社会不自由导向国家自由的“社会运动”,其任务就是要“把社会秩序和运动纳入国家一切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中”[5 ]。
但是,斯泰因的国家观并没有止步于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而是在此基础上继承了黑格尔的现代国家思想。
德国思想中的国家概念到黑格尔这儿上升到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层面。应该承认,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吸收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研究成果的。他首先承认市民社会对自由的肯定,因为“它坚持个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利,增加了人的需要和满足他们的手段,组织了劳动分工,推动了法治”[6 ]。但他又深刻地认识到,市民社会作为需要满足的体系也会产生自身的危机,一方面社会成为角逐私利的场所,另一方面出现财富分配不均和等级差异。为了克服这个由“孤立原子”组成的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必须由一个代表普遍理性的国家来出面调停。这个能“促进普遍利益”的完善国家,应该不是一种作为暴力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国家机器,而是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基础的伦理与文化共同体,具体的自由和权利只有在这样的理性国家中才能得以实现。
显然,黑格尔的现代国家观已经超越了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有机国家”理论,它是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刻认识和批判的基础上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浪漫主义者如亚当·米勒等虽然也批判劳动分工的堕落倾向,批判兵营式大工厂是伤风败俗的怪物,但卡尔·施密特认为,浪漫主义是从情感—审美角度来批判的,它在根本上是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的。
斯泰因同样也继承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他对自由的认识是辩证的,一方面,他也相信理性主义和进步观念,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个体自由是从未存在过的,它依靠财产来保证每个人的利益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又揭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社会自由的美丽面纱,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营自由、市场自由和劳动契约自由。实际上正是它们导致了财产关系的分裂,造成了社会的不自由。真正的自由,按照斯泰因的理解不是不负责任的、没有联系和约束的。如同黑格尔强调国家是“伦理的整体,是自由的实现”,斯泰因也认为“人格”国家是自由的真正体现者,它承认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但代表的是全体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个体或集团的利益。实际生活中的国家权力的重要任务是使依附阶级获得财产,形成独立意识、具备负责任的能力。
三
斯泰因生活的时代与米勒和黑格尔不同,他处于变动的时代。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后果开始显现。资产阶级社会诞生了,欧洲文艺作品的主题明显围绕着资产阶级社会展开,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阶级分化,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与工业社会相伴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成为时代的政治口号。法国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而斯泰因人生中风华正茂的时期也正是在巴黎度过的。为了撰写法律史论文,他从基尔大学去了巴黎,但从此却改变了专业方向。他密切关注法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状,认真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并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密切交往。他一生中所有重要的著作都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相关。
斯泰因的国家理论并未停留在他的思想理念中。如果说黑格尔对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做了大胆的思想预测的话,那么可以说斯泰因在黑格尔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现实的思考,对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完善。斯泰因国家理论的特点是他把经验和理论、实证科学和精神科学结合起来了。他的社会改革方案正是他社会—国家理论的实践设想。
虽然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中,思想的国家往往屈服于靠利益驱使的社会,而社会也由于财产的分裂而导致阶级差异,有产者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设置种种障碍剥夺无产者获得自由的权利,由此产生了“社会正义”的问题。但“人格化”的国家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斯泰因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于劳动被资本控制。财富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但劳动成果却不归劳动者而归资本所有,这与劳动的本质相违背。因此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建立新秩序,使劳动的本质和意义得以实现。解决19世纪的社会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一个工业社会,使劳动者通过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按一定方式获得财产,使劳动“不再是商品,而成为真正的资本,一切经济和财产关系的基础,物质生活和社会的内在原则”[7 ]。不过,斯泰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理论结果,他不主张通过社会革命而是寄希望于社会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社会改革所依靠的既不是统治阶级也不是被统治阶级,而是第三种中立的社会力量即社会君主制。
其实,斯泰因非常清楚现代国家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遇,它往往会被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所掌控,即使君主制也免不了这种厄运的困扰——君主代表的是抽象的权威,实际的权力被剥夺了,只是作为一具空壳被保存下来。但是,斯泰因仍然乐观地相信会有一种摆脱这类命运的可能性,那就是君主制必须代表纯粹的国家,必须成为社会改革的领导者。斯泰因认为世袭的君主不依赖于任何社会阶级,拥有人民的信任与爱,这是他与生俱来的优势,因此只要他重新宣布自己是最高的立法者和执行机构,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创造自由,特别是把对无产者的保护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自由的国家就不难实现了。
斯泰因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稳固,因此政治学所思考的对象发生了重心转移,权力分割的法治国家思想让位于行政思想。斯泰因的《行政学》著作正体现了他重塑国家制度与行政的理论勇气。斯泰因的国家学说,其作用不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所限定的职责范围,它远远不只是维持社会治安,而是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全体公民都有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可能性,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整体中的一分子,有独立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意识。国家的精神气质应该与个人的精神生活相一致。他为政府的行政管理即所谓的“社会行政”注入了新的基础——“生存关怀”,通过在经济、流通领域,以及教育和培训制度方面的行政工作,关心每个人的基本利益,保障其生存安全。国家要发展经济,它必须是强有力的和富裕的,这样才能促进公民福利的发展。国家更要发展教育事业,斯泰因提倡普通义务教育,让每个孩子、每个公民不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对所有人开放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打通社会的流动性,扩大人们在给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活动空间,打破阶级壁垒,使无产者获得上升的机会,而且还可以“废除社会因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精神隔膜,全面建构人类的精神生活”[8 ]。教育是建设具有“人格思想”国家的社会实践。当然,国家行政的真正任务是要重新确立劳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教育把劳动阶级培养成有教养的、拥有财产的社会阶级,以保证自由的圆满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泰因所理解的国家行政,与西方自由主义在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时倡导的“国家行动能力”,是有区别的,其差异就在于对国家本质的认识。
四
19世纪中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凯歌行进的年代,但斯泰因却在资本主义看似稳定的制度中预见到了工业社会无法避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为他的学术研究打开了未雨绸缪的开阔视野。
斯泰因的国家理论不是孤立的,他通过观察社会的结构、条件和原则来研究国家,因此他的国家学说也是社会学说。他的社会—国家理论与19世纪的大多数相关理论不同,他没有党派观点。他热情地主张将人民从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参加到整体国家中去,但却不是自由民主的推崇者;他想建立与自然秩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却不是把政治诗化的浪漫派;他崇尚国家的行政权力,但却不是国家威权主义者;他提倡社会君主制但不是王政复辟者。斯泰因的社会—国家理论重视公民福利的发展和国家的富裕充足,但这个国家又不是费希特主张建立的“封闭的商业国”,因为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力,而在于通过国家的强大来保证全社会的自由。他的社会—国家理论也不是19世纪末欧洲所推行的简单的“福利国家政策”,他对社会问题、社会正义的关心不仅是要解决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而且是要对社会结构做出质的改变。
但是,君主制还是为斯泰因的社会—国家理论添加了“保守”的色彩。虽然他不喜欢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小德意志道路,但他热爱君主制。他对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斗争的结果可以保持清醒地认识,对君主制国家的利益倾向和弊端却视而不见。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他对君主制抱有幻想。19世纪末,这个帝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体制,其思想渊源便来自于包括斯泰因在内的德国思想家的国家理论,认为君主制国家有责任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1890年上台的威廉二世皇帝更是推行社会政策的“新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袒护资本家的阶级立场,对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采取中立态度,以至于赢得了“工人皇帝”的称号。但“新路线”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1918年德国君主制在一次大战的炮声中覆灭,乃是资产阶级和社会革命力量联合行动的结果。斯泰因所倾心的君主的“高贵的道德勇气”,亦未能如他所愿建立起具有“人格思想”的自由国家。
事实证明,斯泰因的社会—国家理论以及他所传承的德国思想中的整体国家观,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只能是另一个乌托邦。现代国家不可能是黑格尔“具体自由的实现”,也不可能是斯泰因的“人格化”自由国家。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作为“整体”的国家“沦为一种更加有限、更加非个人化的行政区域”[9 ],政府的职能是向私有者提供保护。国家不可能是纯粹的思想的体现者和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它不可避免地要为强势集团所支配。
不过,斯泰因的社会—国家理论对我们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第一,现代社会需要有一个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理性力量来规范和制约。第二,国家不应该只是理性的工具,它在看重效用的同时,也应当关注目的理性。国家行政的基本理念在物质性的生存关怀之外,应该具有更多的精神关怀。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周嘉昕. 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 南京大学学报,2009(2).
[2][4][7]Ernst R. Huber. National staatund Verfassun-gsstaa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Staatsidee. Stuttgart:W. Kohlhammer Verlag, 1965 :132 、52 、143 . [3][5]桑巴特,杨树人译. 德意志社会主义.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41、239.
[6]张汝伦. 莱茵哲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
[8]Gundela Lahmer. Lorenz von Stein: Zur Konstitution des buergerlichen Bildungswesens. Frankfurt/M: Campus Verlag, 1982:131.
[9]汉娜·阿伦特.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97.
编辑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