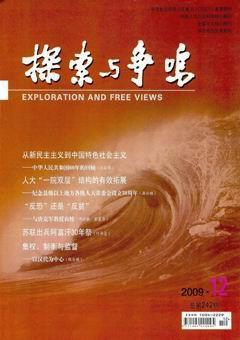论新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意识的变化
内容摘要 从“新时期”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形式语言到文化语言的实验过程。在形式语言阶段,作家作品强调文学语言的形式意味,突现文学语言在文学叙述中的功能和作用。但从199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文学开始尝试文化语言的写作实践。作家作品的一个基本的努力方向,就是将汉语写作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创作出更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新世纪”以来,“方言写作”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在本土文化经验方面,又作了更为自觉的理论提炼和创作尝试,其基本特点是注重中国文化生命特色,本土经验不再是落后、愚昧的表现,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展示其困境与开掘的不懈努力。
关 键 词 先锋派 语言本位 当代文学 形式语言 文化语言 方言写作
作 者 龚海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上海:200062)
“新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通过批评和创作实践,逐渐确立起语言在文学本体建构中的历史地位。所谓本体,在理论上的理解可能有分歧,但就其指向文学最根本或是最重要的问题的理解而言,显示了近似或相似的价值立场。对文学语言问题的定位,是一个既区别于思想观念、生活经验等“内容”范畴,又不同于方法、叙事等抽象形式范畴的独特问题,它是一头联系着生活,一头连接着作家精神世界的审美中介物。这种中介物所建构的文学审美空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示着一个阶段文学审美的历史进度。
一
“新时期”文学语言的思想自觉,是与形式主义批评、叙事理论、结构主义方法以及文艺创作中的实验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划分,罗兰·巴特、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热奈特的叙事理论,都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理论助推器和文学实践的进展标志。文学创作中,马原、苏童、余华、孙甘露等“先锋派”作家,一改以往文学创作探索着力于思想观念等“内容”方面的做法,转向文学形式实验。这种文学探索的转向,给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开辟出一个巨大的实验空间。其中,文学语言问题是支撑这一新的探索空间的重要支柱。
对“新时期”作家、批评家而言,文学语言问题并不是开天辟地的新发现、新问题。但长久以来,文学语言与文学表现“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于工具与表现两大范畴的。很多作家、批评家都强调思想、情感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他们虽然同时也强调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他们对于文学语言的认识,大都局限于工具论范围,以为文学语言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就是通过作家精湛的艺术技巧,将常人难以表达的思想情感,以语言文字的形式传递出来,但这样的意识,在“新时期”后期开始受到普遍的质疑。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但文学语言还有超越工具之外的另一面,即审美层面的问题。从审美层面看,文学语言未必都是出于交流、传达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审美的完整部分。它不需要传递什么,它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
在“新时期”后期,也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包括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在内的一批作家作品,显示了另一种文学实验的方向。这就是被很多人视为形式主义的文学实验。他们创作的最根本之处,在于把语言形式抬高到文学存在的最重要问题。换句话说,语言包容了他们文学实验的全部内容。他们认为文学审美的变化不是表现为叙述内容方面,而是叙述形式上。讲什么是受到怎么讲的叙述程式的规定和制约。而在怎么讲的问题上,语言又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不是作者选择语言来讲述,而是语言驱使着作家在讲述故事。就像马原小说中时常出现的那个叙述者——汉人马原,汉语的叙述习惯规定了汉人马原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风格。所以,汪曾祺在这一时期论及语言问题时一再强调,语言就是内容本身。[1 ]语言不是披挂在文学表达之外的形式,而是文学存在本身。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文学语言论述,常常被一些批评家命名为文学本体论。以语言为基本问题的文学本体论研究,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作形式主义,一方面固然受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偏向于语言形式,尤其是将语言形式抬高到文学的核心问题来进行论述有关。在此之前,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审美探索,一直注重于思想内容,尤其是当代政治生活。事实上,相比于同时代“右派作家”、“知青作家”浓厚的政治情结,“先锋派”作家普遍对现实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作家,不太愿意直接在自己的创作中涉及现实政治,像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艺术上近似于颓靡。“先锋派”作家着迷的是文学语言的叙述实验。他们的作品题材大多远离现代生活,或表现边疆生活,或描写民国生活,他们的这种艺术选择不完全是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其中主要还是源于他们想用自己的笔墨来做一番文学实验,看看那些曾被写滥的边疆生活和民国生活,是不是可以通过叙述语言的实验而获得非同寻常的审美效果。的确,同类题材的陌生化效果在他们的文本阅读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语言实验的成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通过语言修辞方式的变更,可以达到文学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或许是实践和理论的互文效果。
总之,在文学语言问题上,“先锋派”作品的语言实验和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叙述理论在内的一些偏重于形式的批评理论的相互支撑,大大改变了“新时期”后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作家、批评家从原先的注重社会生活内容,转向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
二
文学语言问题的讨论和审美实验,一度被研究者认为到“先锋派”为止。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一种文学实践在语言问题上能够超越“先锋派”的文学实验了,再也没有一种批评像形式主义批评那样注重语言的本体价值了。所以,在一些研究者眼里,“新时期”后期的形式主义批评以及“先锋文学”的语言实验,抵达一种形式扩张的顶端,而1990年代随着“先锋派”作家作品的淡出,似乎表明当代文学的语言探索就此结束。但事实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对照“新时期”“先锋派”作家作品的语言实验,与1990年代中国作家作品在语言问题上的认识进展,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先锋派”语言实验的特点以及局限,也因此映衬出1990年代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在文学语言问题上新的探索和实验。
“先锋派”之所以被一些批评家归类于形式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的形式主义是指在文学问题的理解上,“先锋派”作家较多地偏重于从文学形式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喜欢以怎么写的问题来替代写什么的问题。语言问题——作为如何写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受到“先锋派”作家、批评家的青睐。他们从语言的形式感、语义的表现效果、语言叙事结构对小说故事的改写功能等诸多方面,扩张了文学语言的表现力。让文学语言从一种简单的工具论牢笼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存在物。但这样的文学语言探索,无论从语言观还是审美实践方面来讲,都存在简单化的倾向。从语言观反思“先锋派”的语言实验,他们仅仅是把文学语言理解成一种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形式。“先锋派”作家信奉艺术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不错的,但有意味的形式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借助语言来不断改变自己的?这一系列问题不是简单地说:文学语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就可以全部概括的。
从西方语言学对语言的认识看,很多研究者意识到形式语言学的局限性,转而走上文化语言的研究道路。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就认为,语言问题应该是与人类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孤立、封闭地抽取出几条语法规则和语言统计数据,是无法说明语言生成过程中的复杂原因和复杂现象的。他注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研究,认为:“语言的特性主要是在文学时期以及此前的准备时期发展而成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语言更多地超越了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上升到纯思想的阐发和自由表述的高度。”[2 ]文学语言一方面是作家个体的感受和生命体验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又具有普遍的意义,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的体现。与“新时期”“先锋派”作家作品的形式主义文学语言探索相比,1990年代初一些中国当代作家、批评家有了较为自觉的新的探索。譬如鲁枢元在《超越语言》一书的后记中就表达了自己对结构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不满足,认为这些理论过分拘泥于现有的语言规则,而忽略了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和突破性。王蒙和韩少功等作家也认为文学语言是在规则与破除规则之间徘徊,永远也不可能固定在既定的语言规则之内。[3 ]
在创作实践上,摆脱形式主义语言规范的影响,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阎连科的《耙耧天歌》等创作中,一些更具本土性的语言内涵被挖掘出来。这些作家作品一改“先锋派”作家作品炫耀语言形式的炫技派做派,努力挖掘语言之于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在《马桥词典》收录的词语解释中,感受到的不是韩少功在炫耀地方语言的形式美感,而是作家对一种地方生活经验的独特感受。词语的揭秘,不是将词语的形式美感从叙述内容中剥离出来,进而将整部作品的关注焦点拉入到叙述技巧轨道上。韩少功的写作兴趣不只是停留在语言形式上,而在于马桥地方生活,所以,马桥地方语言的呈现承载着马桥地方生活经验的独特性,作者是希望将读者的注意力从词语形式的层面,提高到对地方生活经验独特性的关注上。同样,在阎连科《耙耧天歌》中,对河南耙耧山区的风土人情的揭示,是与其地方语言的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阎连科对地方语言的思考还不及同时期的韩少功来得自觉,但阎连科在耙耧地方系列作品中对这一地方生活的高度关注,无意间让自己的语言文字开始脱离“先锋派”作家的形式主义表达方式,进入到一种文化语言的境地。
三
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整整10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实验一直是在一种无名状态中进行的。所谓无名,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一些有价值的文学语言探索,还没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它们依然是被1980年代的形式主义理论误读和遮蔽的。另一方面文化语言的文学意识远没有像“新时期”后期作家、批评家对形式主义文学语言那么自觉地揭示和热烈追求。前一个方面像韩少功等人的语言实验,在绝大多数同时期的批评家眼里,不过是照搬国外某部作家作品的格式,而这样的借鉴模式在“先锋派”作家作品中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事实上,我们阅读“先锋派”的作品都会有一种鲜明的感受,与其说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一个中国人在说话,还不如说更像是一些中国作家们在模仿着卡夫卡小说的中译本或者拉美作家的某个中译本的语句、语气在说话。语言的洋腔洋调和外来特征,在“先锋派”作品中几乎是一眼便能窥出。但1990年代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尽管还没有完全脱离“知青腔”,但那种“先锋派”作品的怪里怪气的叙述语言已经不再存在了。一种平实的更接近于中国人叙述习惯的语言方式,以较为贴切的方式蛰伏于作家笔下。至此,我们可以说当代文学走出了实验期,开始以汉语母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够像韩少功那样在1990年代初期就对自己的文学尝试有一种充分的自信。文化语言的写作意识在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笔下,并不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语词。一些作家只是本能地感觉到形式主义的探索似乎越来越苍白,甚至“先锋派”作家自己都在调整着原有的笔墨。像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被一些评论家视为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其实,对余华而言,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许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写作时的感觉对不对头。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似乎不再拥有形式主义的阅读市场,人们需要一种更为持久而深入的东西,文学需要呈现出作家对生活的质朴感受,而不是华丽的形式外衣。这一时期走向中国当代文学前台的,是莫言、贾平凹这样的本色作家。他们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方式,描写着乡土世界发生的变化。莫言的《檀香刑》、《丰乳肥臀》,贾平凹的《病相报告》、《怀念狼》等作品,尽管在文字形式上,已经做了非常大胆的实验,但在一般读者及批评家眼中,这些语言实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些小说呈现的乡土中国。似乎从这时开始,中国小说才有点真正的中国面目。在以往,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作家想象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似乎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神明世界。但1990年代之后,像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了与中国文化地位相匹配的大国作家拥有的从容气度和精神状态。这样的文学面貌,是世纪末最后30年间,中国语言文学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一些敏感的研究者以“民族主义”来概括这样的文学、文化现象。但从文学语言变化角度看,应该是更趋成熟的一种表现。
对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形式探索经验的理论提炼,应该是新世纪以来的所谓“方言写作”的概括。在2005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活动中,有评论家总结“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经验差异。随后,李锐等作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继续探讨网络时代的“方言写作”问题。像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太平风物》,贾平凹的《秦腔》、王小鹰的《长街行》、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等,基本上都是非常本色地表现着中国地方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大量渗入了方言。这种不断蔓延的“方言写作”潮流,已经超越了形式革命的文学范畴,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所谓浓厚的文化意味,是指作家们普遍自觉意识到语言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同构关系,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存在形式等问题,已经不再是作家考虑的主要问题。从作家写作的角度考虑,地方性经验,以及与这种经验相关的方言形式,似乎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
围绕“方言写作”的文学探讨,是新世纪文学语言观的重要进展之一。普通话推广之后,对很多非北方话方言区的作家而言,当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地方经验时,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方言习惯,以普通话的语言方式来重新叙述自己的地方性经验。这种双重改写的语言写作方式,改变了方言与地方性经验的直接性,所有的文学语言都以一种标准、规范的普通话形式呈现自己。文学语言所需要的崎岖不平和充分变异的语境、语调和语言气象,被一种统一的、规范的、平面化的程式所逐渐控制,文学语言的审美险峰也因此被一种平淡无奇的单调语言所替代。从这一角度来反省新文学以来的文学语言传统,普通话推广对汉语言文学的语言创造能力的限制,应该说是负面的影响胜于积极的作用。[4 ]事实上,以“方言写作”为开端的对现代汉语写作传统的反思,强调现代汉语危机,注重文化语言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新世纪以来文学语言探索的新途径。
反省现代汉语研究传统与反思现代汉语文学写作的语言工具,几乎开始于新世纪同一时期。这种反省文学现象与语言研究现象的思潮的重叠出现,似乎在提醒人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文学语言,包括与其相关的语言问题研究,是应该有一种新的归宿了,这种归宿的具体方式,或许各有不同,但基本面貌应该是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更加接近。而这种接近不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体的生命魅力的展现。
参考文献:
[1]汪曾祺. 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晚翠文谈新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7.
[2]洪堡特,姚小平译.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鲁枢元. 超越语言·跋. 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刍议.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陈佳. 茅盾文学奖颁奖 文学界反思长篇创作. 东方早报,2005. 7. 28. [5]杨扬.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三个三十年. 上海文学,2008(6).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