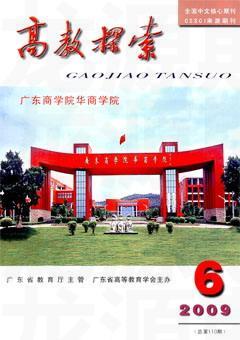当代教育的技术化活动方式及其调整
刘同舫
摘 要:当代教育无论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手段运用上,都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方式。其技术化特征包括:统一化、简约化、工具化与二元化等。积极反思教育的技术化活动方式对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具有紧迫性。在技术时代,当教育的发展正表现出受技术发展目标控制的时候,应保持教育系统自身的独立地位,并按自身的目标发展,不因外界力量的冲击而偏离自身的价值认同与发展轨道。
关键词:当代教育;技术化;超越
随着社会的发展,崇尚技术、追求效率成为时代的精神之一。当代技术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性与自在性从而按自身逻辑发展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对象世界和自身世界的各个方面,使人类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形成了一种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性标准的技术化的活动方式。“在试图达到目的的人类事务那里,它是为人类的历史经验所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手段。因此,它最终倾向于取代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模式。”[1]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学校教育也遵循技术理性,沿用了无所不能的技术化逻辑,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实践活动。
一、“工具理性”与技术化之特征
技术在为当代世界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却也逐渐显露出其“工具理性”实质的局限性。人文精神被挤压、“价值理性”主导人类的生活被幻化,背后的深刻根源,就在于对工具(手段)的有用性的绝对确认,即对“工具理性”的沉醉。符合“技术理性”的生活方式都被认定为一种合理性的生存。技术理性的生存方式有两种表征形式,其一是“工具”,即技术的物质形态;其二是“规则”,即贯穿“工具理性”的技术化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可以说,这两种方式对人类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尤其是现今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采取现代技术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一种时尚标志;各种新兴的技术知识、原理、手段对课堂的全面渗透,使得当代教育无论在教育目的抑或教学安排上都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方式。
1. 统一化特征
目的理性的活动按照工具理性的规则,也即是依照技术自身的逻辑规则来进行,无疑是技术化的最重要特征。当代教育作为一种目的性极强的培养、塑造活动,自然是一种“目的理性的活动”,却由于依照技术规则运作,成为一种标准化和统一化的活动,是“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2]。其活动过程是“用合理性的东西把合法行为的感情和传统的模式作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从生活中加以取代的过程”,“理性是它自身的必要性的立法者”[3]。如此一来,此类代表着“工具理性”的技术逻辑规则具体化到当代教育中,造成了两方面的恶劣影响。其一是详细划分学科,形成各自为阵的学科领域,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知识支离破碎;其二是按照量化的技术规则,将学习者“捏造”成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却缺乏主体性的个体。由此可见,统一化的当代教育造就的只能是一种工具人,秉具严谨的技术理性精神,却空乏细腻的人文精神。最终,教育只能成为一种功利主义的输入-输出式的催化剂。教育把受教育者以组织化的模式纳入学校教育的生产过程,用统一的教育技术、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育工艺流程,把学习者制造成标准化的“教育商品”;把学习者放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而加工制作,把学习者整体精神的发展仅仅变成行为功能的增加,是呆板的机械性变化,抑制了个体的全面发展,剥夺了学习者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学习者完全沦为学校和教育的附属品。可见,当代教育以统一性压制了具体性,以群体性压制了个体性,以依赖性和被动性压制了主体性,其实质是以技术理性压制了人的价值性与情感性。
2. 简约化特征
当代教育的简约化是统一化的延伸。简约化指的是将高级的、复杂的整体性事物通过严密的技术理性拆解为低级的、简单的部分性元素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局部代替整体,将整体化约为局部的过程,其本质乃是一种机械的认识论。简约化对当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于影响人们认识教育的目的与本质。教育仅仅被看成是实现人类知识再生产的手段的教育本质观,由此导致教育对象的物质化、非人性化倾向。更是由于其机械的认识论,使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划一性的过程,结果流于形式化和表浅性,教育越来越远离学习者的生活世界,窄化了教育的职能和内涵。教育发展只是如何设计一套完整的标准化的手段,把学习者培养成一个具有“工具理性”的符合技术理想的缺乏主体性的个体,使教育丧失了其本应承担的在管理、传递、储存知识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感。学校教育的根本意韵被祛除,具有丰富意义和无穷生机的教育只是成为传授学科知识材料的保守僵化的过程。
3. 工具化特征
传统的语境下,教育首先是一种人文教育,是对人的心灵的培育过程,注重的是人的内在精神、思想、气质与责任感的培养,关注的是人性的卓越,维护的是人性的尊严。在这种教育下,尤其注重经典文献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能思想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实施的是一种全面的教育。[4]然而,在当代性语境下,由于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浪漫理性的精神逐渐为一种更适合于现代世界的生存、竞争与发展的“工具理性”精神所替代。正因如此,人文教育对人的卓越性的培育让位给了技术理性教育对人的竞争性的塑造,教育实践成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传授和训练过程,从而导致其深厚的人文蕴含消解,人所生来俱有的一些非工具性精神活动(如形而上的沉思、信仰及艺术情感等)也因不能带来其实际利益而渐被拒斥在外。通过技术理性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以及现实功利性的强迫性作用,受教育者被“培养”成一个个工具性极强的实体。教育本身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渗透了工具化的技术性特征。
4. 二元化特征
技术化逻辑规则对当代教育的渗透促成了一种二元化思维的教育。这种“二元化”教育往往割断事物内部要素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相互抵制与相互对立。其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在教育主体上,强调课程专家、学科专家的作用,忽视教师、学生的地位,教育发展就成为与学习者自身价值与意义无涉的机械的工具性行动。在教育目标上,强调控制,忽视发展;强调训练,忽视生长;强调精确、具体、统一,忽视多样、差异、创造。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强调学科,忽视学生的经验和社会生活;强调知识、技能,忽视精神、情感;强调分科,忽视综合;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忽视社会和人文知识。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强调权威,忽视主体性;强调划一,忽视多样;固守封闭,拒斥开放。在教育发展的评价中,强调结果,忽视过程;强调目标达成,忽视个体创造。这种二元化的认识定势恰恰正是“工具理性”非此即彼的狭隘教育思维的结果。
二、“人文精神”与技术化方式之反思
以培养智慧的人、高尚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过程,需要在较高的层次上,即在人文文化、人文精神的层面上来进行。但是,现实教育活动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技术化方式,将这种具有科学意义、人文意义、哲学意义、心理意义的教育工作,当作一种简单化的技术性工作来对待,形成了教育过程中的技术化活动方式。以“人文精神”为指南,积极反思教育的技术化活动方式对于中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具有紧迫性。
教育技术化活动方式呈现在教育的理论层面上,是教育目的的单一化、片面化,教育功能引导的社会经济化,以及教育理论研究的教条化。与此相应,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强调学生的技术性能力训练,轻视学生的精神涵养,品德锤炼,使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健全地发展;在教育的功能发挥上,过分膨胀经济性功能,从而失却了教育引导社会、创造文化的发展性功能,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堕落为经济的工具。另外,在教育的理论研究中,往往注意探索教育过程的技术性规律、技术性方法和手段,如较多地研究教师如何去教,学生如何去学,而不是研究和探讨教师应该教什么,学生应该学什么。在对教师的要求上,往往只要求教师如何当个教书匠,当好教书匠,而不是如何当个“人师”,当好“人师”。在对学生的学习上,只研究学生如何跟教师学,而很少研究学生如何独立地学、创造性地学、自主性地学,以及建构鼓励教师成为“人师”,鼓励学生自主、独立、创造学习的机制。
教育技术化活动方式呈现在教育的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将教育复杂的、认知的、价值的教化过程,简单化地理解成技术性的知识授受过程,一些学校将培养人格健全的发展型人才简单化地理解成未来应用型人才,技术性能力的学习和养成代替了人的个性充分发展和素质的培养。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专业方向和专业学习成为技术性学习的充分理由,所用教材缺乏必要的知识交错、学科相融和文理贯通;授课教师缺乏必须的人格引导、仪表示范、感情交流、价值观念提升等教育意识和精神;教育方法缺乏焕发学生聪明才智的主体性积极学习内蕴,而是权威式的教师单向授受方式,使教育过程缺乏教育本质上应该具备的科学意义、人文意义和熏陶意义,成为只重视单纯技术能力培养的过程。其中,教师的教育价值与意义没有充分地开掘出来,学校陶冶、更新、洗礼学生灵魂和精神的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学习、探索创造性学习的意义和习惯也没有培养起来,使技术化教育成为一种时代性潮流。
当代教育发展的技术化路径否定人的自主自觉性,缺失“人文精神”的浸润,使教育成为“输入-产出”式的控制模式,教育成为知识的输灌和技能训练,而不是促发生命的生长、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使教育发展目标缺乏整体性和情感性,出现了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和差异性的丧失,使教育内容过于单一和僵化;也使教育评价线性化,教育评价过于注重控制而不是发展。评价由于客观化、划一化和封闭化的标准而成为实施操纵的手段。在教育实践中,技术化教育发展固有的保守性、封闭性、狭隘性,使教育推广政策往往不顾及教育内容和教育背后的价值观的适切性,教育推广政策由此丧失了“政策理性”,教育缺乏民主性和开放性而陷入专制。
渗透着“工具理性”的技术化教育排斥了精神教化,教育过程仅仅是固定化的操作过程,因此,现实的教育不需要教育思想,不需要教育理念,只需要操作指导,这样的教育必然带来精神教化的终结,带来教育理想的终结。
教育技术化倾向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使教育活动出现方向性偏失。技术化的教育过程,使教育本来应该处于知识、人格、意义、精神、价值、观念层次的塑造和熏陶活动,堕落到只论教知识,不用教人;只论教技能,不用培养素质的技术性追求层次,使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因失去具体教育过程的基础而变得虚无甚至失落。教育的方向则变成事实上的职业培训和实用技能培养,只具有实用性的技术意义。教育也相应地变得简单和容易,求优、求雅、求洁的信念渐渐失落,实惠、实用、实利成为教育思想中的主要倾向。
对教育技术化倾向进一步深入反思可知:第一,技术化的教育淡化了教育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强化把教育仅仅当作人类承继文化知识、促进文明发展的工具。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卷的第一句话所指出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种求知本性源于人内心深处对真理的一种渴望和追求,人们正是通过教育实现这一精神渴求。通过具体的教育活动,人与人的精神相交流、相契合,从而领悟生命的内涵,规范自己的行为,获得精神成长。因此,教育其实担当着两大功能:形而下的知识传授与形而上的精神铸造功能。而当代教育尤其是具体的教育过程单方面注重和发展了教授形而下的知识,即“技术理性”的传承功能,忽略了其形而上的精神铸造功能。当代教育中实用功利课程的设置、整齐划一的考试命题和标准答案不仅严重限制了学生求知的自由扩展,更将求知本身引向实用性的世俗追求,导致今天的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学生都急功近利,缺少诗意和理想,缺少激情和牺牲精神。这种急功近利不仅表现在学生对专业和课程的选择上,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关心终极意义和绝对真理,普遍地丧失了批判与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境界和能力,因而根本就无法与这个充满了诱惑力的物欲世界相抗衡,甚至利用所学知识追逐物欲而导致犯罪。第二,由于教育的技术化活动方式带来的功利性教育思想导致受教育者想象力与创造力严重退化乃至丧失。科技理性强调实证,将世界还原为“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沉死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动的世界”[5]。这样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神灵的世界激不起人的任何想象和诗意;想象与诗意的衰退与丧失,又愈发使得人不可能进入文学艺术的世界。文学艺术教育成了对文本结构、写作技巧等进行解构分析的技术操作。想象力的丧失亦意味着人的创造力的退化。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对于个人来说,教育的指向决定了其未来的存在方式。技术化的当代教育将人制造成最有用的工具,是专业知识与技能堆积成的,而不是营造一个深厚的“人文精神”氛围来培育具有完整精神生活的本真的人。今天,人之生命的物化,工具理性泛滥,都与教育迷失了自身的本质,沦为技术生产体系的一个功能性要素密切相关,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
三、“自我意识”与技术化方式之调整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教育深层次的问题域是教育在现代技术的渗透下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方式。因此,探讨当代教育技术化的解决途径必须从教育体系的整体视野来思考。
技术化的教育使教育不能造就现代人的独立的精神品格,不能培植主体性。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时代建构新的教育体系。新的教育体系,即主体的教育体系,就是树立个人主体性原则、以个体为主体、培植个人主体性的教育体系。培植个人现代的主体性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基本内涵,也是时代精神对时代的人的基本要求。社会的发展必然地包括人的主体性发展,同时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起点与条件,两者呈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发展总是建立在每一时代的人成为现实实践的主体之上的。每一代人经过主体化而成为实践主体,以社会目标为取向实现主体价值。每一代人的主体化都是通过教育的积极培养而实现的,教育通过培养新的社会主体,建构新的文化精神与理想,实现对现实社会的变革。每一代人在教育的主体化培养下,超越现实、追求进步,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在的精神与能力,从而成长为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创造的主体。
具体而言,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应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活动本身把发展人的主体精神、培养新时代的个人主体作为教育实践的时代目标。而要培养新时代的个人主体性,就必须有意识地引导个体对自我意识、对个性的积极建构。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外在的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中,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内在的对自己的个性、对自我的精神的有意识的改造中。每个人通过发展自己的内在潜能,塑造自己内在精神,培养自己的新人格,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即通过不断地改造自我,而提升主体内在的能力与价值,从而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地实现文化创新和改造现实的任务。同时必须把个人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自我意识是个人独立、自主、自由与发展的基础。只有在自我意识充分发展的过程中,个体才能获得主体性,个体的主体性是以自我意识为根本的,主体性和精神的超越性只有透过自我意识才是可能的。自我意识不仅使个体在世界中站立起来,建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以自己能动的主体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且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从而超越自我、改造自我。因此,自我意识决定了个体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不断地反观自己、审视自己与确定自身的未来形象,不断在价值实践中实现改造自己精神人格的任务,这是作为主体的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
教育只有把发展个体的自我意识作为首要使命,才能培养新时代的新人,才能引导个体不断地提升自我、发展主体性。发展个体的自我意识,就是使个体在已有的自我基础上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的嬗变中,形成精神的超越,不断形成“人格”理想与追求,从而成为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实现主体价值的“新人”。
我们必须在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整体范围内把培植个人主体性、发展个体的自我意识、发展个性作为根本性的任务,对教育进行整体的变革,使教育真正成为受教育者在精神变革的关键时期的生命活动的价值表现,成为受教育者实现精神力量、获得人格精神整体建构的积极方式。必须从人的生活境遇、时代精神出发,引导受教育者对“生活世界”的价值领悟,建构受教育者的精神人格,形成受教育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并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
从某种角度上讲,教育问题源于人的生存困境,源于人的精神在现代性处境下的困境。技术化导致人精神异化与分裂,形成重“技术理性”、轻人文精神的局面。教育的改革首先必须关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生成这样带本质性的问题。培养一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处境、具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的人文意识。这种意识提醒人们在追求现代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目标,遏制这个过程中可能对世界产生的种种负效应和可能出现的危险。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教育技术化活动方式的讨论,目的并不是要批判教育和当代技术之间这种紧密关系,因为类似的批判——包括反科学主义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出现——不仅没有现实可能性,而且没有理论上的依据。在当代社会,教育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自身最大可能的支持,乃是当代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是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和其它系统正常交往的应有之举。而评价教育技术化活动方式的关键点并不在此,在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破坏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状态与运行机制,它促使教育的目标向现实社会的发展方面靠拢,因而也就阻碍了教育自身功能的实现。正是这样,这种活动方式越是明显,它对教育作为一个系统的破坏性就越大,教育也就越不能按自身的功能目标独立自主地运行发展。在这样的状态下,真正的“人”的发展,真正的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难实现的。[6]因此,在技术时代,当教育的发展正表现出受技术发展目标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愈应保持教育系统自身的独立地位,按自身的功能、目标发展,不因外界力量的冲击而偏离自身的价值认同和发展轨道。只有这样,当代技术在它扩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才有可能得以预防与避免。
参考文献:
[1][3][英]唐·麦克雷.世界热潮的中心人物[M].赵立航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8,109.
[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9.
[4][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3.
[5][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49.
[6][法]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M].程洪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