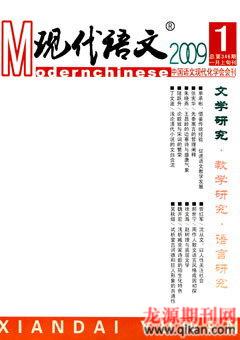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故事理论
涂 昊
摘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发展历程中,“故事”这个小说最高要素走了一条从倍受青睐到遭冷遇再到被注目的螺旋形道路。中国小说创作故事理论从横向和纵向不断拓展,自主性和自足性不断增强,从现代形态向当代形态不断转变。
关键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故事理论当代形态
1992年徐岱在《小说形态学》绪论中,认为对小说创作过程作出审视,主要有两个角度,即从动态的建构方面把、握和从静态的建构方面来剖析,前者当然非叙事学莫属,后者则归形态学所拥有。而本文的故事理论是从静态方面来讲的,而后一节的叙事理论则是从动态方面来分析的。
英国现代杰出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提到“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因素。”在世纪末20年的小说发展历程中,“故事”这个小说最高要素走了一条从倍受青睐到遭冷遇再到被注目的螺旋形道路。其中意味深长的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提升。就在“故事”荣辱变迁的过程中,故事理论在对传统故事讲究时间的延续和因果关系历史特征的质疑与突破中不断地推陈出新,内涵不断丰富。
一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被称为“故事小说”,当时故事小说“只限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给人以离奇的刺激的低级审美感受”。故事理论稍显稚嫩,美学意蕴处于一个单薄的阶段,这是因为小说创作实践表面上重视故事而实际上“故事意识”并不强。
8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仍然延续了70年代末小说对故事的关注。《人到中年》、《沉重的翅膀》、《祸起萧墙》、《人生》、《绿化树》……这些80年代初期轰动一时的作品几乎都充斥着波涛云涌的矛盾和喷薄欲发的冲突,这时期的小说家在竭尽心智地编故事,故事性在小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但实际上,作家们关心的并不是故事本身。
8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追求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在新长征路上熠熠发光,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启示,也给人以力量!”刘心武也反省自己:“我当时是以非文学的情绪进入文学领域的,当时还顾不到‘美文,使用的是相当粗糙、笨重的文本。……总之,是把社会政治诉求寄托在小说的躯壳中。”可以说,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是当时一种和谐的最强音,与其说作家在关心故事,不如说关心的是通过故事说明什么反映什么的激情,于是在故事中带有很强的情绪化和观念化特点,预期中的故事所要诠释的观念像一个“强大的专横的暴君逼着去提供故事情节”。这样,对故事所要揭示的哲理、观念的刻意追求使创作浸染着刻骨的浮躁。
随着整个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故事是所有小说创作都具有的最高因素”这一观念遇到了挑战。一方面,受罗伯·格里叶为代表的法国“视觉派”小说和以维·伍尔芙为代表的英美“意识派”小说明确提出小说的“非故事化”影响。,中国作家也开始有意地淡化故事。“意识流小说”完全打破故事的时空,可以取故事的任何一个环节作为切入点,通过自由联想前后跳跃,时空交错地对待整个故事。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说“情节是创作原始的结构手法……近代小说不再满足于故事”。冯骥才也以契诃夫的名作《草原》为例提出“不要认定小说必须有一个故事或中心事件、或矛盾冲突吧!”另一方面,像老作家汪曾祺,也有类似的想法:“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不太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这是从传统创作中汲取营养对故事要素进行的探索。两股潮流殊途同归共同对故事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在1985年之前都是局部的,没有对故事为中心的小说创作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也没就故事产生激烈的学理论争。
二
1985年前后,中国文学进入到一个空前活跃的新阶段。小说创作打破了传统封闭型故事的一体化局面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心理结构、意向结构、自然空间结构、文化空间结构等小说新样式层出不穷,小说的诗化、散文化、抒情化、情节淡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现代化”小说渐成气候,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搅得文坛沸沸扬扬,马原、刘索拉、徐星、残雪、莫言、阿城等一大批年轻的小说家以全新的手法冲击着小说创作界。在这样一种摧枯拉朽的小说艺术革新中,故事这一小说的基本层面首当其冲,新一代的作家完全抛弃有头有尾的传统故事套路。虽然表面上看小说创作对故事不屑一顾,但新的创作潮流正是以对传统故事否定的方式开始了对故事始无前例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故事理论才走出单薄肤浅的层次,开始了故事理论多层次多样化的理论构建。
徐岱在1985年发表的《小说与故事》在理论上梳理小说与故事关系的基础上,对故事的涵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他借用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给故事下的定义:“故事是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这种定义认为故事必须遵循时间的逻辑,而且是一种线性逻辑,偶尔的中断、反复也都是有迹可寻的,故事的舞台被严格限定在一个空间结构里,人物的出现、.情节的发展,均受空间的约束。故事到底要不要遵循这套时空的逻辑?现代派小说,诗化小说的创作甚至对要不要故事提出了挑战。徐岱借用福斯特“时间生活”(客观世界的外部事实)“价值生活”(人的主体的“情感”生活)的概念,认为价值生活归根到底是包裹在时间生活之内,价值生活只有在时间生活的波峰浪谷之中不断推进才能保持新鲜活力。由此认为传统小说的故事以物理时间为组织者,现代小说的故事以心理时间为枢纽,故事始终在小说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并明确提出,对小说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要不要故事,而是怎样正确使用它,所有的小说创作技巧都表现在这里,这是一条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谁要是轻蔑它,到头来都会受到它的惩罚。徐岱对故事内涵的理论建构,既支持了以“故事”为核心的小说创作实践的深入,又从客观上扩展深化了“故事”的理论内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还有一批作家和理论家建立起的是自觉的与故事对立的意识,标榜“小说什么都写,就是不写故事”。对他们来说,形式是消解故事的,但实际上是以否定的“反故事”的方式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内涵。1985年,马原谈到故事的运行“首先是生活的构成方法”,既然生活并不总是提供所谓“完整性”,故事也未必得遵守完整性原则。马原还多次使用“弹性”故事的概念,“弹性”故事就是没有规律性,有多种可能性的故事。马原声称故事虚假并作出解构时,实际上强化了对故事的注意。事实上,“先锋派”一直在关注历史故事,只不过形式的探索压制了对历史故事的注意。
新写实小说则是在“还原生活”的情况下加入了“反故事”的阵营。它是以对“故事虚假性”反拔的先锋姿态出现的。刘震云曾在那篇堪称是新写实小说家宣言的《磨损与丧失》中谈到,“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有过宏伟的理想,但那是幼
稚不成熟的。一切还是从买豆腐白菜开始吧。”新写实小说写的是个人日常生活琐事的小“故事”,这是叙述了另一种“故事”,但无章法无节制的故事越来越凸现其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其实,延伸“故事”也好,反“故事”也好,强调“真实”也好,强调“虚构”也好,都很少写出经典的故事。
1989年,谭学纯、唐跃发表《故事与反故事》勾勒了故事作为小说的母体、本体、载体三个发展阶段,立足于风格互补的语言效果,较全面地论述了“反故事”的理论内涵。并认为尽管在终极的意义上,反故事可能是不彻底的,它可能会是重建故事的先兆。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反故事,就绝对不会跃上更高层次的故事。事实上,经过“反故事”的环节,故事很快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三
1989年以来,小说创作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巨变,形势探索的势头明显减弱,以《褐色鸟群》名满文坛的格非写出了《敌人》(1990),写过《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的苏童写出了《米》,写过《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余华推出了《活着》,以《烦恼人生》独占鳌头的池莉写出了《预谋杀人》(1992)……对照他们的前后作品,差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他们以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征服了文学界,也征服了读者。随着创作实践领域的巨大变化,在理论界则又对故事投注了更多的兴趣。
文学对故事的理论重认,是从马原开始的。马原在文学界普遍轻视可读性时,却提出“可读性是小说价值中的第一要义”。1989年,上海的《文学角》开辟“故事和讲故事的专栏”,由一些批评家和小说家自由发表对故事的看法,如王安忆极其重视“小说构成意义上的故事”,这类故事强调的是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以区别于对经验的直接抒写的“经验传说性故事”;莫言在1991年明确表示:“我一直在思考所谓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出路。”池莉也强调“名著的标准之一就是不仅仅专家读,关键在于最广大读者经久不衰的热爱”。1992年《文学评论》发表军旅作家周大新的《漫说“故事”》则代表一个时代的小说创作者对故事的反思:
故事的质量是衡量小说品位、等级的一个标准,寻找质量好的故事成了小说家的任务之一,作为一个小说家,既要有选择故事的能力,还要具备讲故事的高超技巧和本领?
这反映了在西方叙事学理论、文学艺术上的工艺主义、操作主义、原现代主义的解构欲望以及顺应了商业化社会心理等诸种因素的文化背景下,创作界和理论界对故事创作的重新回归。
1992年,徐岱出版《小说形态学》,其中提出了叙事/故事概念的区分,认为在现代小说学领域,两者内涵并不相同,叙事等于“叙述”加“故事”,叙述是从动态角度,故事是从静态角度来把握。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首先也在于如何处理“叙述”与“故事”的关系。从形态学角度来看,小说的文本内涵也就是故事,小说形态学对小说文本的探讨主要也就围绕故事构成的开端,中间和结尾三大部分,各部分有不同的艺术要求。1985年徐岱是从纵向的角度丰富了故事的内涵,1992年徐岱可以说是从横向的角度拓展“故事”的研究对象,过去“叙事”与“故事”混为一溃的研究状况得到了理论上的澄清。
对故事理论建构推动的还有创作界和理论界对“虚构”概念的深入阐释。马原在1989年就谈到布莱希特的间离说强调艺术创作的虚拟性质(非真实)有很多的意义,王安忆也认为讲故事的人总是摆脱不了虚拟世界的吸引,她在《纪实与虚构》中缠绕她的就是如何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寻找故事的可能性。余华则更理论化地思考“虚构”,他赞成罗布一格里耶认为“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就在于真实性概念的不断改变”,他感受到自己的作品十分真实,而这种真实不是对存在的本样的复述,反而是通过“虚伪”的形式获得的。
同时他们还区分了“经历”。与“经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经历而来的经验是远远大于经历的,作家不是对经验作原始运用,而是无限地去施展它,利用它,在相同的经验下,却呈现无数的由他们杜撰的“经历”事实,也创造前人们不可能创造出的“虚构的作品”。
而作为作家和理论家并重的学者格非在19g4年发表的《故事的内核和走向》提出了“开放式的故事走向”和“故事内核”两个重要概念。这是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对故事创作进程和故事创作意图而对故事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明确的理论阐释。
“开放式的故事走向”指作家在讲述故事时,不再依赖时间上的延续和因果承接关系,而依据一种心理逻辑,这种逻辑乔伊斯称为“感觉上的和谐一致”,普鲁斯特称为“活跃的,无可确定的记忆”,格非称为“感觉中的世界”,这是对古典文论中“得意志言”的进一步发展,对传统叙述结构的一种调整,在“开放式的故事走向”下,作家的创作自由就极为广阔。
“故事的内核”指的是最早出现于作家意识中的“初始画面”,这个画面是作家虚构故事的切入点。它与整个故事之间至少存在“演绎关系”“象征关系”“隐喻式关系”,并认为存在于故事中的某些内核一直在作品中时隐时现,对自己的超越仅仅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重复”。这也揭示了创作中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责任,有其需要表达的最根本的意图,也从中透露出作家对生活的世界(包括历史)所表明的态度以及其它丰富的意思。格非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把故事还原为一堆生活片断的同时,又从中提炼一个“故事的内核”,它是故事情节的高度浓缩物,带有多种意义指向和多种发展的可能,格非称其为“中心意象”,那些生活片断称之为“并置事件”。
在“故事”理论的支撑下,故事不再执着于再现现实的意图,而更多侧重于表现感觉的真实。故事靠自身的生命和逻辑显示出勃勃生机,这时,故事秉赋了自主性和自足性在更高意义上位于小说创作的中心位置。
四
1990年曲金良在《故事文化略论》一文中提到,在我们至今的文艺学那里,找不到“故事”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将“故事”作为专门种类的,只有民间文艺学这里。1994年,刘守华的“比较故事学”研究的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其实,在民间文艺学那里“故事”已远远不是今天的“故事”概念。曲金良有意对“故事”作全面系统研究,提出“故事文化学”,分析了故事本体可以有口头语言、形体语言、书面语言、绘画语言、雕塑语言等多种呈现形态,并与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心理文化、民俗文化等构成一个大文化合体,意在把握“故事”作为故事文化的整合性和主体性,达到对故事的全方位的认知。这种对“故事”的理解确实扩大了故事的内涵,也有利于对故事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更是启发了人们从整个社会文化战略的转移,从小说创作边缘化的大文化背景下思考“故事”的走向与前途问题。
历史上,故事的传播方式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推进发生了多次变化和转移,但故事始终与人相伴,这种既有益于心智又对族群的生活模式、行为规范等知识系统具有传承功能的文学模式不会消失。行吟说唱的衰落,小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小说便出现和繁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文学生产,印刷传播和阅读消费为主的故事形式,因新的媒介形式出现而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影视剧等视觉文化成了“故事”传播的主要形式,那么在小说创作理论研究视野中“故事”又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也成了未来故事理论建构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