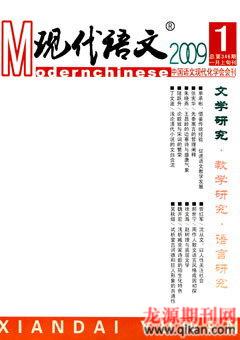未完成的启蒙
巫 丹
摘要:在动态的阅读过程中,文本的空白与未定性召唤着读者。为了意义的探寻,读者进入文本。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将文革时期命名为“启蒙时代”的话语模式引起了读者的阅读阐释。本文从接受反应文论的视角,对《启蒙时代》带来的阅读影响进行意义阐释。
关键词:《启蒙时代》接受反应话语阐释启蒙
文学文本是一种意义的表达,只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可能成为“现实的存在”。阅读是读者在文本中对意义的探寻,通过意义的阐释使文本得以长久的存在。意义的阐释就是对文学的批评,“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作为缺席的在场被谈论。”所以,意义的追寻与阐释便成为读者阅读接受的动力,新的本文唤起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意义的诱惑召唤着读者阅读活动的深入。《启蒙时代》的出现,给了学界一个新的阐释对象,不仅因为王安忆一直是一个受人关注、颇有分量的作家,还由于小说中将文革时期命名为“启蒙时代”的话语模式引起了学界的思考。本文拟从接受反应文论的角度,对小说《启蒙时代》的接受过程进行分析。
一、文本的空白、召唤结构
接受美学的“双子星座”之一伊瑟尔,在他的《本文的召唤结构》中,认为文学文本采用形象的艺术来表现人们生活的世界与重构的世界,作家在创作时,对所构建的事件留有空白与暗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对于文本构成一种召唤结构,召唤读者介入文本所叙述的事件中去,“读者必须靠自己去发现本文潜在的密码,这也就是发现意义”。
(一)《启蒙时代》的专栏讨论及获奖
在文本的产生和读者个人接受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等,这些社会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取舍。《启蒙时代》发表于《收获》2007年第2期,随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权威期刊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发表了陈思和、张旭东、王尧、罗岗等学者的评论文章。2008年4月,《启蒙时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的在权威期刊上的专栏讨论及获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接受,召唤着读者进行阅读,填补本文的空白,寻找本文的意义。
(二)《启蒙时代》命名的召唤与暗示
启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思想界、知识界一个绕不开的话语关键词,作为小说的书名直接出现还是第一次。在这个文本题目的召唤之下,读者对文本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预期。“启蒙时代”指的是什么时期,为什么命名为“启蒙时代”,谁“启”谁的“蒙”,如何“启蒙”,本文又是通过怎样一个故事结构小说。这就给接受主体留下了意义空白,这些疑惑引导着读者深入文本去解码。
二、作品对读者期待视域的融合
由于召唤结构的吸引,读者开始进入文本,其先在的阅读经验为文本的接受提供了一定的期待视野。正如姚斯所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最新发表的作品,也不是信息真空里出现的绝对的新事物。”《启蒙时代》讲述的是发生在文革前期的故事,对于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不同读者因不同的知识结构有着不同的情感期待,形成接受者潜在的有差异的接受基础。
王安忆对于上海弄堂生活的谙熟,构成了她写作的一个重要特质。同时,作品还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深刻与思考的深度,一种接近于性别中性化的理性。感性体验与理性追问,这看似相对的两面却很好地融合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构成了读者对王安忆作品的期待视域。
(一)上海弄堂的女孩世界
王安忆对于上海弄堂中女孩的细腻心理的把握有着独到的贴切。不管是《桃之天天》中的充满生命力的郁晓秋,还是《富萍》中的女子中学窃窃私语的女学生,都是生活在上海弄堂中有着琐细而曲折心理的女孩子。
在《启蒙时代》中,越过第一、二章故事背景的全景图式的叙述,在第三章读者的期待视野在舒拉、舒娅姐妹、珠珠等上海弄堂的女孩的身上找到了融合。这是读者所熟悉的,也是作者多次在其作品中展现的。这一群小女儿,喜欢买滚了甘草,用桔梗还是萝卜条制成的零食吃,到小照相馆拍半寸的“咪咪照”,用玻璃丝编织成的小金鱼,牵牛花样的小物件。在市井社会中,这一群小女儿有着微妙的心思,正从小孩子变成少女。
(二)关注个体生存的思考
尽管有舒娅、珠珠等女孩子在调节着小说中粗粝的阳刚的男性空间,文本仍然是以一个叫南昌的男孩子展开的,他的周围承担启蒙者的大都是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男性角色。在文革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们大谈布尔什维克,大段地背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狂热地迷恋马克思的艰深著作,并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生活中、社会中的一切问题。这是一个僵硬的教条时代,有的是硬邦邦的革命理论,诸如南昌等青年人,被时代所启蒙,有着极大的革命冲动。生存困惑被置于思想的交锋与深度的拷问中,南昌们经受着艰难而痛苦的认同,他们教条的思想在市民社会中接受涤洗与重构。这种思想的困惑带来的焦虑,延续了王安忆作品中关注人的生存思考的意义主题。历史与现实带给作者理性思索的意义之笔,书写着人生存的困惑。
三、期待视野的超越
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对超出原有期待视野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姚斯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和文学演变论影响,一直将新颖性看作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在《启蒙时代》中,读者找到了与期待视野融合的阅读体验,但更多的是对原有审美视域的超越。超出期待视野的作品给人“陌生化”的审美新鲜感,也是读者接受本文的价值所在。《启蒙时代》被进行多种意义阐释,也正是因为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域,留给读者新的意义阐释空间。
(一)思想事件的精神气质
文本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小说充溢着各种思辨话语的交锋,这是一个关于思想修辞的事件。父辈们的军装、辩论、聚众演讲、托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充斥于时代的生活细节之中。如南昌的红卫兵小将们,沉醉在一种以奇异的“革命理论”和激进政治建构的“当代宗教”中,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用言语的互动消除现实狂飙的困惑,填补精神信仰带来的迷惘。文革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使易于接受社会影响的年轻人陷入了一种精神亢奋之中,生成了一个充满激烈话语的时代。
在南昌与陈卓然充满时代贵族气质的辩论中,有着沉重而冷峻的思想姿态。陈卓然可以把当下的革命运动置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之下,马克思原著中的欧式从句结构带来了陈卓然理论的华丽。南昌祟拜陈卓然,他愿意与陈卓然交谈、辩论,在这个时代,陈卓然是南昌的精神之父,南昌“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
南昌、小兔子一帮人凭着时代赋予他们的革命正传的身份,夜访资产者顾老先生,为得是让顾老先生承认他的资产阶级剥削本质,从而验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剩余价值
的理论。交谈中小将们发现,顾老先生不仅形象与他们印象中的资本家剥削阶级相去甚远,而且创业史中饱含的是乡土中国农民式的血泪,其剥削本质充满了东方气质的温和和隐忍。小将们书本上学到的教条、僵化的理论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中受到了质疑,使他们对奉为圣经的抽象革命理论产生怀疑,进而是作为革命正传身份的痛苦否认。
(二)革命者与市民社会
王安忆在本文中隐含了对市民社会的认同,“启蒙”还是对革命者市民意识的启蒙。在这个粗砺、追求宏大的泛政治化时代,隐匿的、琐细的生活细节被摒弃,“小市民”被挤压在社会边缘。“小市民”在革命小将们看来是消极的,是社会改造的对象。作为南下干部子女,在上海这个市民社会中,他们对精致生活是疏离的,感受不到与老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生活是黑白的,由此也产生了失落感。在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潜意识中,对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充满好奇和希冀的。
当他们接触到国外回来的敏敏的奢华生活时,对舒娅和珠珠的热情立刻就发生了转移。嘉宝的中产阶级趣味也吸引着他们,小老大的生活态度,何向明的思维方式都对革命小将们产生了启蒙。小老大从小跟外婆过着精致的生活,家中的沙龙是时代中各式闲散年轻人的去处,包括革命低潮时期的“落难的天使”南昌等人。小老大不谈政治意识形态、不谈国际局势,南昌们僵硬的革命信条在此被搁置,却被其细腻、阴郁、颓废的生活态度所吸引。出身于上海小市民阶级的何向明,属于上海的本土,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在时代的浪潮中虽处于边缘,但受影响也不大。何向明温和,对事物的理解没有那么明朗,但可以将宏大的、抽象的事物化解为易于理解的关系。何向明介入南昌的生活,正是市民阶层对南下干部子弟缺失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启蒙。
南昌生活在一个抽象的革命者身份的自我荣耀之中,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文革初期,这些南下的干部子女,活跃于革命的舞台,随着他们父母在革命中所受冲击,革命成了革自己家的命,他们成为孤儿,成为社会的零余者,从而对自己的“革命的正统”身份产生了怀疑。这个时候接触到的市民社会冲击并启蒙着南昌们的思想逻辑,令他们鄙夷并反抗的小资情调,却给了他们另类的启蒙。
(三)身体的启蒙
《启蒙时代》可以看成是一部成长小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接受启蒙。文本中故事跨度仅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文革前期,即1968年前后。文本主体的这一群年轻人在这一年中正处于身体和精神的发育期,启蒙也包括身体的启蒙。这些特殊时期的革命正传,也是有着微妙心思的少男少女,让他们对异性不免生出懵懂的缠绵。嘈杂的时代,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失,使得刚刚步入成年的他们,极早地成为时代承担的主体,无论是参与革命,还是个人成长的困惑,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南昌在混乱的现实和迷惘的前途中感到无措而消沉,在身体的诱惑中跟资产阶级的小姐嘉宝发生了关系。这对于革命小将来说,是无力承担后果的。他们是社会的正面人物,是时代的核心,在这个阳刚气质十足的革命时代,堕胎带给他的启蒙不仅仅是嘉宝的疼痛,更有着精神上的痛苦。
整个文本不是一个情节很紧凑的故事,而是一部心灵史,一部精神的对话录,大段的辩论、思索,在言语的密林中交锋思想,这也正是那个时空中理想激昂、心灵迷惘的映照。本文中启蒙无处不在,启蒙从未中止,启蒙不仅是作品中人物接受的启蒙,也是读者在文本中接受的启蒙。启蒙意义的诱惑,使更多的读者参与到“未完成的启蒙”的阐释活动中,填补“未完成的启蒙”中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