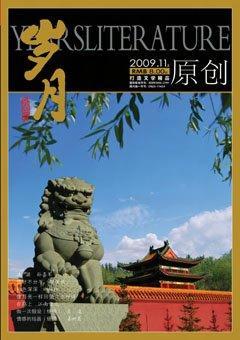卡尔维诺的承诺
刘 飞
阅读就像在丛林中前进,这是卡尔维诺对读者做出的承诺。阅读卡尔维诺的小说确实有这种感觉。作者将你领入丛林,然后趁你一不留神就溜走了,剩下你自己面对巨木和杂乱的灌木愁叹。然而,你发现作者并不是没有良心——他在树干上、路旁的石头上刻了记号。只要你足够听话,按着作者的指示循序前进,最终会走出丛林,仿佛获得了新生。这时候作者又从一棵树后跳了出来,做几句总结性的发言,一部小说就结束了。你在心有余悸的同时禁不住向人倾诉你的伟大,怎样独自走出了丛林,其实,不过是卡尔维诺的游戏罢了。做游戏的同时,你会感觉到自己想象力的地壳一点一点裂开了,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思维岩浆迸射出来,蔚为壮观。喜欢卡尔维诺的小说,更钦佩卡尔维诺的人格。大师终其一生,开掘小说叙述的无限可能;竭尽全力,兑现着自己对读者做的一个又一个承诺。
世世代代的文学中可以说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要把语言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像云彩一样漂浮于各种东西之上,或者说像细微的尘埃,像磁场中向外辐射的磁力线;另一种倾向则要赋予语言以重量和厚度,使之与各种事物,物体或感觉一样具体。
我支持轻,并不是说我忽视重,而是说我认为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说明。
——摘自《美国讲稿》
在看《美国讲稿》之前,我一直以为卡尔维诺推崇厚重的语言,以至于看到《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关于重量的论述颇为惊讶。但仔细一想,卡尔维诺的语言确实不算沉重,压根就不是《静静的顿河》中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风格。在卡尔维诺的语言世界里,更多的是轻灵与美好。所有植物的色彩是那么鲜艳与活泼,更多人物的对话如孩童般天真与快乐。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轻飘的如磁力般的语言,创作出厚重的、令人深思的故事。故事本身是厚重的:像《不存在的骑士》中,那种强大的欧洲骑士文明的背景,是厚重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中,那种关于善与恶的哲学思考,是深刻的。如作者所说,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说明。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故弄玄虚只会表述不明。卡尔维诺运用“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说明”的语言写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故事,给故事本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涂上一层玄幻的色彩。真正神秘的不是老卡讲的故事,而是他叙述的语言。轻飘的是语言,厚重的是故事,这或许是卡尔维诺创作的原则。这一点与徐志摩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之处是二者都使用轻的语言。卡尔维诺轻得轻灵,徐志摩轻得朦胧。不同的是卡尔维诺以轻的语言讲述重的内容,而徐志摩从语言到内容都是轻的。也许有人要说,徐志摩的诗歌有很多描写的是离别时伤感惆怅的情绪,给人深沉悲伤的感觉。但徐志摩的诗歌中缺少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泰戈尔的诗我读得不多,但我觉得里面蕴藏着作者的宗教情怀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些在徐志摩的诗中表现得不多。徐诗更多的是抒发个人的情感。卡尔维诺的小说《不存在的骑士》以骑士文化为背景,《分成两半的子爵》探求善恶的终极问题,比起抒发个人情感的小文章要厚重得多。我想,这就是才子与大师的区别。
爱人阅读彼此的身体不同于阅读写下来的书页,它可以从任何一点出发,跳跃,重复,持久。从身体的阅读中可以辨认出一个方向,一条通向终端的路径。
——摘自《寒冬夜行人》
我把这段话当作卡尔维诺就“灵与肉”的命题给读者做出的承诺。说实话,我觉得卡尔维诺的小说中关于“灵与肉”的描写并不成功。回想看过的他的小说,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画面,一个是《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的小男孩儿趁姐姐与纳粹军官做爱,偷取军官的手枪;一个是《寒冬夜行人》中的“我”,最终与女主人公上床;再有就是《帕洛马尔》中,帕洛马尔先生看乌龟交媾的场面了。这正是我所失望的。卡尔维诺不是一个描写爱情的高手,他在小说中并没有发掘爱情的美好与可贵,没有发现爱情是来源于内心深处对美的冲动,只是停留在了肉的层面。爱情在他的小说中,并不是主要的素材,只是一个道具,是他开发小说叙述的无限可能的一把铁锹。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做得要成功得多。一提起翠翠,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梳着油亮的大辫子,闪着黑眼睛的清纯小姑娘。翠翠说的每一句话,仿佛抓着我的心坎儿,挠得我心里痒痒的。沈从文描写的爱情,已经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上升到人性普遍的爱。天保与傩送对翠翠的感情,也不单单是爱情,还有愿意为其付出生命的终极关怀。《边城》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因爱而美丽,而伟大,最终也因为爱而陷入无法挽救的悲哀。爱情是误事的,或许这样,超理性的卡尔维诺为了避免被爱情冲昏头脑而不敢涉猎爱情。或许是这样吧,但小说又不是现实,来一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爱情又有何不可呢?关于“灵与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开始下一段。
书册和誓言,比不上一个人既有的价值。人可以进行书写,只不过灵魂可能早就已经落失。
——摘自《不存在的骑士》
卡尔维诺是“不存在的骑士”,鲁迅是“真的猛士”。我一直幻想着让二人进行一场角斗,或是在残破的古罗马斗兽场里,杀个昏天暗地;或是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个城砖横飞。或许有人不解:二者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意大利,八竿子打不着,杀个什么劲?其实,鲁迅与卡尔维诺,正好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善与恶。卡尔维诺代表善,鲁迅代表恶。我先解释鲁迅,不然肯定有人反对。首先,在文学创作上,善与恶没有好坏之分。托尔斯泰是善,卡夫卡是恶,但都不影响他们在文学领域的泰斗地位。在文学创作中,善与恶就像是纸和笔,是用来写作的工具。文学作品可以弘扬真善美,更有必要挖掘人性的假恶丑,以警示人类。鲁迅,就是用恶写作的。他尖酸刻薄地批判国人的奴性心理,挖掘人性中已经沤烂变质的心态,以起疗救之效。鲁迅以恶写作,目的是挽救国民,他人性的本质是善的。身在欧洲的卡尔维诺就幸运得多了。鲁迅面对的是两千年的“酱缸文化”沤出来的臭透了的现实,要改变现状只有做个混世魔王,将一切都搅碎了重新安排。卡尔维诺大可不必那样,他不用承担颠倒乾坤的责任,他要做的就是选择正义的一方,支持,支持,再支持。所以他写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大力赞扬共产党。相比之下,我为鲁迅感到可怜。中国人,需要面临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里,大多是灾难,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怪不得鲁迅的语言是沉重的,而卡尔维诺的语言是轻飘的。
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摘自任何一本
卡尔维诺小说的书皮
我把这句话当作卡尔维诺关于创作态度的承诺。我一直把握不好创作的态度。是像诗人一样感性,把写东西当作情感的宣泄;还是做一个理性的神,俯瞰世间的一切,把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无可否认,卡尔维诺具有男性特有的理性,他是超理性的大师。在他的小说里,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自己智商的有限,被大师牵着鼻子走还不亦乐乎。我有时痛恨他理性得近乎没有人性。然而,当我绕到卡尔维诺的背后,望着大师的背影,才发现,脑海中刚强的卡尔维诺的外壳一点点被海水洗掉,露出了感性的肌肤。正是卡尔维诺对文学巨大的热情,促使其追求小说创作一生而未悔。他对文学的热爱是感性的,感性得像个女人,为爱抛弃一切,抛弃现实。也许,卡尔维诺自己才是其小说中最美的女主人公,卡尔维诺的一生才是其创作的最玄幻、最后现代的小说。相比之下,我国的戏剧泰斗曹禺的创作,是感性的。《雷雨》中的繁漪就是女性的典型,感性的典型,是那种为了爱可以抛弃一切的女人。但当我们绕到曹禺的背后窥视他的创作动机时,难免失望地发现曹老的创作动机是理性的。《雷雨》中“周冲”这个人物的设置,剧本对易卜生、奥尼尔戏剧的模仿,给曹禺本人增添了太多的理性色彩。曹禺在理性的支配下创作出了感性的作品,卡尔维诺则是在感性的涌动下创作出了理性的作品。相比之下,后者高超得多,也更值得我们尊敬。
以上是卡尔维诺就“轻与重”、“灵与肉”、“善与恶”、“理性与感性”四方面做出的承诺。本人将卡尔维诺与中国现代作家进行比较,无意分出孰优孰劣,只是一种借鉴,一种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各位先驱所做的贡献,后人有目共睹,我更是无比尊敬。没有他们,便没有中国文学的今天。
我喜欢小说,胜过诗歌。可能是因为性别的缘故,我更喜欢那种包含隐忍姿态的文章。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都是我喜欢的作家。相比之下,博尔赫斯是神,他飘在高远的天边,使我望而生畏;卡尔维诺是人,他仿佛就在邻家隔壁,是我儿时的玩伴。博尔赫斯是水,无论是语言还是为人,都充满了女性的柔情;卡尔维诺是火,燃烧自己点亮作品,张扬着男子的理性。博尔赫斯供我景仰,卡尔维诺供我效仿。我一直坚信卡尔维诺对我做出的终极承诺。
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给予我们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