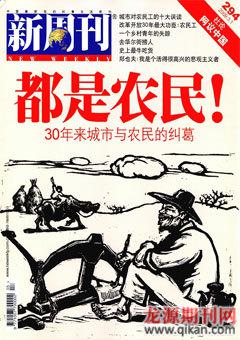春晚:开涮农民20年
陈 旧
尽管农民还占据这个国度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尽管央视屡被视为北方农民台,但在春晚——这个农业社会一年—度欢庆丰收的大日子里,这个举国文艺界最大的形象工程上,农民还是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农民当然是央视收视人群的主流,否则你难以解释毕福剑的走红,给他一块白毛巾,他比阿宝更像农民歌手。类似的还有李咏,他是村子里牙尖嘴利的小坏蛋,《幸运52》一直颇有打土豪、分田地之气息,而最新的《咏乐汇》更是先进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大串门。
没有什么比央视春晚更能展示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所指。春晚上,农民角色从来都不缺:2008年六个湖南浏阳农民步行千余里进京自荐,被央视婉拒,还好曾做过建筑工的王宝强最终在春晚高歌一曲,但不知当时他身后那群农民工可否因经济萧条而失业?今年奶农也站到了春晚的最高舞台上。至于农民形象:至今活跃的一线小品演员如赵本山、黄宏、郭达和潘长江都因演农村角色而走红。
尽管农民还占据这个国度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尽管央视屡被视为北方农民台,但在春晚——这个农业社会一年一度欢庆丰收的大日子里,这个举国文艺界最大的形象工程上,农民还是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春晚小品套路批判
多年来,我们习惯中的春晚小品笑点主要来源有二:服装和语言上拼命表现农民的土气、寒酸、艳俗,穿着过时、行动土气的演员一上场,大家已经发笑,及至开口,更是笑声一片。我们这样嘲笑过赵本山宋丹丹的东北话、赵丽蓉的唐山话、郭达魏积安的陕西话、严顺开郭冬临的江浙普通话与俗称“鸟语”的广东普通话。并不巧合,他们都扮演农民。
还有一个笑点是来自角色们对城市文明与消费主义自觉不自觉的抵触:1995年的《打工奇遇》与1996年的《如此包装》中的赵丽蓉也因切中要害而成为前赵本山时代最受人爱戴的笑星。赵本山在新世纪初的《卖拐》系列则进一步展示了消费主义对农村的侵蚀,2003年的小品《心病》里,农民已经开始变得亦耕亦商,还开始买彩票中奖。

第一种笑点是城里人笑话乡下人,满足了城里人的猎奇感与优越感,第二种笑点则是乡下人对城里人的报复,类似于《卖拐》系列中的奸诈农民成功地忽悠了城里人。当然,在《卖拐》系列的终结篇2005年的《功夫》中,范伟聪明了一次,让赵本山的“忽悠”落了空。城乡握手言和。
春晚农民形象批判
春晚上的农民形象有两种,但都不是真农民。一种是翻身致富新农民,2003年春晚有一对新人合说的相声《今非昔比》,像“陈老舅”这样的平时腰里系根电线,吃饭靠救济的赤贫农民现在家里住着两层楼房,墙上挂着背投电视,开着宝马车,用着笔记本电脑。原因当然是党的正确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光荣正确。
还有一种农民形象,以赵本山为代表:没太大出息,但也并不是毫无出息;谈不上好人,更不是坏人:有中国农民式的狡黠与小聪明,爱占小便宜,但最终又良心发现;对城市生活与现代文明既抗拒又羡慕的农村小人物。这些小品因内容上暗讽时弊和语言上幽默尖酸而成为春晚每年的最大亮点。
第一种农民形象很好地贯彻了央视的国家主义立场与春晚的宣教功能但却大多被人遗忘,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农村形象却又常常陷入类型化与雷同化。就如最新春晚赵本山作品《不差钱》中农村小妹丫蛋儿一身红袄绿裤,发表“获奖感言”时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乡赤水沟子的。”装束笑料与十数年前毫无二致。既不真实,又不好笑,更显春晚内容之苍白乏力。
春晚小品命题批判
当春晚形象固定化、手段套路化,春晚小品的直接命题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再承担部分宣教功能,小品想真好看起来,还真难。
最初赵本山、黄宏、郭达都演过农民,但最近几年三人形象都已基本固定:赵演“蔫坏”东北农民,黄演城市无产者,郭则是木讷知识分子,各擅笑场。发展到最后,为控制语言类节目取向,事先须经导演组授意,谁演什么方向早已事先规定好。一年一度的春晚成了“命题作文”。
2008年春晚赵本山与宋丹丹合作的《火炬手》就因为无创意、无包袱、无笑果而当选为网民心目中“2008春晚最烂节目评选”前三甲。即使今年的《不差钱》中,丫头土里土气地令大家发笑后,赵本山还得用台词说:“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
事实上,这是所有农村题材小品的共同两难境地:服装和语言要尽量土气和艳俗,以博观众一笑;而为了赞美改革开放,他的农民角色又需要炫耀自己的富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小品越来越不真实。
最后一个农民:赵本山
要读懂中国农民,要从读懂赵本山开始。
春晚舞台上,有过三代“小品王”:陈佩斯、赵丽蓉与赵本山。1985、1986年春晚小品《拍电影》、《卖羊肉串》中,陈佩斯是城市里的小混混,为了混口饭吃,而常做出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朱时茂则代表了体制的力量,其凛然正气的形象得自于其背后坚不可摧的国家伦理。1990年代中期的赵丽蓉系列小品则是朴素道德观念在混乱市场经济面前的不适应。

一部本山春晚史,也是一部中国农民进化史。他也曾是春晚的闭门客,三次攻门而不入,如今却成为春晚的定海神针。
本山春晚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相亲》、1991年《小九老乐》和1992年《我想有个家》直面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婚姻、家庭问题,是赵本山的本色演出;1995年《牛大叔“提干”》、1996年《三鞭子》、1998年《拜年》则加入了更多社会因素,因针砭时弊尖刻有力,而成为赵本山讽刺小品的高峰之作。到了2001年《卖拐》、2002年《卖车》、2003年《心病》、2005年《功夫》、2007年的《策划》等小品中,他的矛头开始向下,直指下层社会种种可笑又可冷的不良行径。
或许嘲笑地位财富高过自己的人才叫讽刺,否则只能沦为刻薄。但此时的本山大叔早已是央视都不能小觑的大腕、坐拥亿万身家的娱乐巨头,值得他和他能够讽刺的人已经不多了。
都是农民
歌舞不愉悦,相声不讽刺,小品不幽默,春晚的衰落并不奇怪。
永远忘不了春晚开场歌舞,永远的满园春色,永远的一片大好,永远的歌功颂德。1995年春晚开场歌舞叫《咱们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解小东带着一群半大的孩子,没头脑似地一路高歌“咱们老百姓啊,今个真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个要高兴”,至于为啥,不说。
外人看起来,不正如同我们看、丫蛋儿么?穿着精心缝制的礼服,可劲造,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是来自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中国的。”
还是王朔狠,他说:“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多次啊!吐了好几年不能再看了。那还不如东北农民过年呢!大红大绿多土啊!他们真的特别
可笑,以为大红大绿是中国人。满清来时才这样,明朝是那样吗?宋朝是那样吗?人家都水墨,不带挂色儿的,挂这么怯的色儿。现在穿着被面就上去了。你看春节晚会一开始,金光闪闪,那帮女的都跟姨太太似的。”
反正大家都是农民,谁也别笑话谁。
《远在北京的家》中的22个女孩
陈晓卿
我拍《远在北京的家》时只有26岁,特希望能拍出一个“真情故事”,用现在的话叫和谐社会。但在我跟踪的22个女孩中,没有一个和谐的。
1992年,我开始拍《远在北京的家》,拍了22个外来女工在北京的生活。片子里,我用大量的镜头描述16岁的张菊芳第一天上班在雇主家里手足无措的样子。三天后,她因不熟悉家务劳动被辞退。此后的一年中,她先后当过保姆,卖过菜,端过盘子。她说:“反正我们就看命运呗,命运好就找到好工作,命运不好就做田了。”
2003年,当我再次见到她时,把自己交付给命运的张菊芳已经结婚生子,在上海崇明岛上依靠种田生活。这个后续采访中,我遇到了一件现在想来还是非常吃惊的事:在采访到一半时,张菊芳停止了,折腾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她说:你要给点钱。最后,我还是自己给了两千块钱。
跟张菊芳一起出来的老乡刘红春离开北京后嫁给了一个上海人。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上海人了,告诉我们坐出租车要坐某两大公司的,小公司的不要坐,他们不给开空调的。
22个女孩中,唯一一个还留在北京的叫谢淑平。她不喜欢把自己交付给命运,在去年的时候,她还在合计和别人办一个武术学校。她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两个孩子免除学费。她也是唯一一个要求看片的,看完了没有跟我们说再见,哭着就走了。
我开始拍这个片时只有26岁,对这个社会还是有幻想的,特希望能有一个“真情故事”,用现在的话叫和谐社会。但在我跟踪的22个女孩中,没有一个和谐的。我拍过的一个小保姆,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给某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当助理,自己还学了外语。但因户籍问题无法结婚而不得不回老家。回到家之后,她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她父母刻薄地说,我养你这么多年,你连打个水都不愿意。她不愿意这么晒,她说会得皮肤癌。她在家里听英语,我说你听英语,将来干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们拍的这二十多个人,大部分都成为了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不管她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边缘人。这些女孩子都是在青春最绽放的时候来到城市,她们很快地学习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已经是城里人。但她们的思维还是农村的。回到村里,她们的肉身接受不了。留在城里,他们的思想接受不了。这个是很痛苦的。北京是一个居住地,不是归属地。绝大部分人都回到老家,开一家跟北京有关系的店。他们有一句话叫,熟人就是生产力。在北京有熟人了,有什么活,就可以利用家里便宜的劳动力,在家里做厂。新富豪一批又一批。如鱼得水。但这些成功的人里,我没有看到一个女性的身影。
(采访/邝新华)
我不想一直当助理
陈黎
在四川绵阳平武县古城镇,他叫陈黎。在广州的苏豪发廊、他叫Daniel。一年前,陈黎高中毕业,在广州当发型师的表哥把他从古城镇带到了广州。现在是苏豪发廊的发型师助理。“初中时,表哥来广州学发型师,就一直比较关注这个。后来看日剧的发型师男主角耍剪刀,很帅,就很想干这一行。”陈黎每天早上8点从洛溪的出租屋出发,到天河北的店里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最近刚换了手机,闹铃不熟悉就醒不过来,有一次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按公司规定迟到1分钟就扣1块钱,就这样损失了近60块钱。让他心疼了半天。
虽然有时会迟到被罚钱,但是他还是喜欢上早班。这样就不会洗不成头了。上早班的发型师助理一般9点半到店里,先把店里的卫生搞完,开始洗头,拾掇自己。“我们算是时尚行业,要注意一点外形。尤其头发,我们都喜欢自己弄。自己吹的,用发泥定好型。打卡之前要把自己收拾好。”陈黎特意强调他的头发不是别人烫出来的,而是自己吹出来的。一年多前,他还在路边小店里花三块钱理发,也从来没有衣服搭配的概念。
陈黎的手有点糙,因为他每天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给客人洗头,“冬天特别干,手上都裂口了。现在好很多了。”他们每月是有绩效工资的,洗头多一点,钱会多一点,但是陈黎还是宁愿少洗几个头,多点时间跟技师学一下电发。“我不想一直当助理啊。”他将来是想做发型师的,像日剧里的发型师男主角。来广州之前,表哥曾说如果不习惯就回成都帮他忙,他已经回成都开了一家发廊。“但是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大城市,目前的公司也挺不错的,在这里学东西学出来都是挺厉害的。”至于最终的去留问题,陈黎还是稍微有点摇摆,从心里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四川。不过,这边如果发展比较好,还是想留在广州。
一年前,陈黎来广州的时候是坐火车,硬座,20多个小时,这次春节回家他是坐飞机回去,路费父母出一半,自己再出一半。他买了初一飞成都的机票,折扣高,打了5折。除了机票之外,这次回家还把用了两年的手机弄丢了,买手机“让我妈支援了500,向她又借了500”。支援的是不用还的,借的是要还的。
陈黎每月一千多的收入差不多能应付在广州的生活。父母在家乡开了一家杂货铺,目前也不要求他寄钱回家,只希望他在广州好好学手艺。过春节见到了很多以前的同学,上学的,打工的都有,他们都过得还不错,除了“头发没有我弄得好”。
(图—阿灿/新周刊采访/金雯)
我时常恍惚自己的身份
王军民
2000年是王军民生意的一个低谷时期,他亏掉了200万。妻子在医院待产,他拿不出一分钱,就让朋友救急快递来5000元。朋友很诧异,而一直衣食无忧的王军民也只有苦笑的份。他回老家探亲,看到家里的乡亲们在树下打麻将,闲散而无忧无虑的样子,那瞬间他也希望自己还能变回一个没有心事天天耕种的农民而一旦资金周转顺畅了,赋闲务农的想法就被抛在脑后了,王军民还是喜欢自己运筹帷幄的生活,他说在农村哪里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做事情啊。王军民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当了一个汽车兵,转业在粤财厅下的家信托公司做司机然后升职管汽车队、业余炒更做生意、2003年正式下海折腾到如今是广州中晟物流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也是广州物流界颇有声誉的人物了。
王军民15岁之前在农村生活,父辈代代务农。他没种过地,可是知道农民的苦,他记得小时候总是吃不饱,没油水天天做梦都想吃白馍馍;夏天去田里送饭,看见收割麦子的乡亲、手上被麦子刺得密密麻麻的的血印,觉得真疼,当兵的日子在广州看到了霓虹灯广告牌,看到了城里的松下电视机,他羡慕城里的好生活,千方百计托关系想留在城里,最后是一个老乡帮了他的忙。
对当年在广州一无所有的王军民来说,他最初一切的人脉关系发端都是老乡和战友,而同样很多年来,王军民也是老家乡亲们的靠山和顶梁柱。他帮村里修了路,安装了电力设备……最近村里又打电话来说,让他出50万解决全村的自来水问题,他犹豫了。他说虽然惦记着老家方圆百里水质不好,碱性水喝了得食道癌的特别多,可是他说给钱也一定不能太爽气。
1997年,王军民进城15年了,那年他头一回春节有假所以回老家过年了,而他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了,他不喜欢每天喝那么多酒、喝得晕乎难受,他也不喜欢每天和发小们在一起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描述谁家盖房子、谁家生孩子的事情。他觉得农村的生活太平静了,而这又是农民的生活局限决定的,农村生活特别程式化特别按部就班,没有奔头。他记得第一次过年回老家、老家人看到电视里广东人爱吃宵夜,就问:城里人每天吃几顿饭啊?
在城里多年,有时王军民也会恍惚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广东人还是河南人?他有一双儿女,他说女儿没所谓,他很坚决地认为儿子一定要明白自己河南人的身份。因为儿子是根,故乡也是根,儿子是不能不记得祖宗的。
(图—阿灿/新周刊采访/朱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