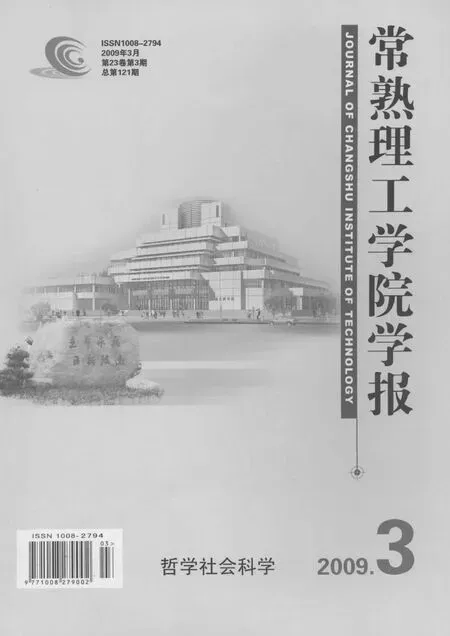汉初藩王文学观念的变迁和藩国文学创作
张春生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汉初藩王文学观念的变迁和藩国文学创作
张春生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藩国的文学多为藩国君臣所作,藩王的文学审美观念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初藩国文体最早为楚歌,大赋继兴,纵横文逐渐消歇。藩国君臣之间的文学探讨,不断变化的朝藩形势,日益发展的求奢心理,都对藩王的文学审美取向产生影响,继而引领着藩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汉初;藩王;文学观念;文学创作
汉初藩王作为藩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不惟支配自已的创作,还对藩国文士的创作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1]现在流传下来的藩国作品,没有布衣之曲,纯粹是藩国君臣之咏吟。汉初藩国的文学流变无疑打上了藩王的文学审美烙印。
一
汉初诸藩王深谙楚韵,在审美接受上也以楚歌为主。
汉高后吕雉七年春正月,吕后因吕王后谗言,招赵王刘友入京,幽刘友于王邸,刘友死前作楚歌以申悲怨: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2]1988
同年六月,继任赵王的刘恢亦因吕王后擅权、爱姬被鸩而悲苦自杀,死前作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
同年,济北王刘章(刘邦孙),在一次入侍吕后燕饮中进歌舞,并高唱一曲《耕田歌》(时刘章20岁,为朱虚侯):
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2]1992
观是年刘氏三歌,刘友歌先唱吕刘之争的大背景,再唱自已遭诬囚禁的经过,卒章写自已无奈、悲苦、怨恨的心情,艺术上简俗质直,少形象寄托。刘章歌通篇用比,用耕田间苗喻吕后对刘氏宗室的迫害,虽然感情上不如刘友歌浓郁,但在表现手法上属婉讽之作,艺术技巧似又更胜一筹。后世诸藩与帝矛盾时表达感情多所借用。据称魏陈思王曹子建作“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3],以对曹丕。唐雍王李贤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4],以讽武则天。可见刘章歌影响之大。
汉初藩王在创作上的这种特色,主要是受汉帝刘邦影响。刘邦家本楚地,故善楚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2]1沛,楚地也。同时由于刘邦起自民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2]79,“帝起细微”[2]80,能多接触原汁原味的楚地民乐,创作出布在众口的作品。刘邦虽“不修文学”[2]80,但多才多艺,对楚歌的应用十分娴熟。曾作楚歌二章,一是《大风歌》,一是《鸿鹄歌》。刘邦在吟唱《鸿鹄歌》时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2]2036汉初楚歌响彻宫廷,不惟刘邦吟唱,戚夫人吟唱,更有120名沛中少儿定期习吹相和《大风歌》,甚至唐山夫人用四言楚歌写《安世房中乐》。汉史评曰:“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2]1043诸藩王在年少时是和刘邦生活在一起的,浓郁的楚文化氛围对他们影响至为深远。李泽厚这样概括汉文化:“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5]未免有些夸张,但形容刘邦时代的文学实不为妄。西京初建时,整个文坛确是楚声独步,就藩的诸王也深受影响。
由于藩王和汉帝在文学审美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一些非楚地籍的作家在藩创作中也呈现出明显的楚地特色。如汉文帝刘恒前元三年,贾谊因朝臣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的反对,被文帝徙为长沙王太傅。由京入藩,称为左迁。贾谊意不自得,渡湘水而作《吊屈原赋》。文中用了屈原式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受排挤、遭打击的愤慨。此赋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式的长句。刘勰评价其文特色:“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6]157点明其善于抒情的骚体特色。三年后,有鵩飞入贾生舍,“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7]249,《鵩鸟赋》纯粹是自慰之作,作品中人物情感和作者情感并不完全一致。作品中宣扬的是道家齐生死的豁达,而现实中贾谊却是一个敏感的人,以长沙卑湿而伤悼,后又自伤为梁王傅无状,哭泣抑郁至死,寿仅三十三。在文体特征上,《鵩鸟赋》可看作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经减少;在文法上,以假设自己与鵩鸟的问答展开,隐然开汉赋问答体之先河。刘勰评价汉初赋与楚声的关系时云:“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6]108
二
逮及景帝之世,文体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诗赋方面。
四言诗用于叙庙堂之事,虽有文繁意少之弊,但是由于藩王的熟悉和喜爱,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楚元王交字游,……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2]1922楚傅韦孟四言诗创作的动机,也是考虑到楚王对诗的深厚造诣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共鸣,我们推测韦孟当时的四言诗应该有一定数量,只是与核心政治关系不大,故史书不载。元王死,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汉景帝刘启前元二年(前155),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徒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云:“如何我王,不思守保”,“邦事是废,逸游是娱”,“所弘非德,所亲非俊,唯囿是恢,唯谀是信”。[2]3101《在邹诗》云:“我即迁逝,心存我旧”,“洋洋仲尼,视我遗烈。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我虽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2]3105刘勰高度评价两诗艺术特色:“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6]82,其实这两篇呆板古奥,完全没有《诗经》那种民歌天籁风韵,也不如刘邦父子四言体通俗浅显(除“兮”字)。这种作品,不但刘戊不屑一顾,社会上也并不认可,不能传唱于井水处。班固撰《汉书》时这两首诗的著作权已经模糊,为慎重起见,也指明“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2]3107在文学史上韦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汉初梁国为赋的重镇,汉赋至此初成体制和梁王的文学审美观念息息相关。梁王对赋家多招徕和奖掖,“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2]2208,游士中就有后来名满天下的邹阳、枚乘。后来被称为汉赋四大家之一的司马相如,也为好文的梁王吸引来到梁国。《西京杂记》还记载忘忧馆中梁王和文士们咏吟奖罚的场景:“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7]191《忘忧馆七赋》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特征,显示出梁国君臣对赋体的探索。在内容上,不写贤人失志,而写喜遇明主。写作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先咏所咏之物,再言藩王之美。如枚乘作《柳赋》,先言柳之嫋嫋情态,再言“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路乔如作《鹤赋》,先言鹤之优雅,亦言“吾王之广爱”。公孙诡作《文鹿赋》先言鹿之美,再写梁王知遇之恩,“逢梁王于一时。”邹阳作《酒赋》,先言旨酒之美,再写梁王与宾客之乐,“哲王临国,……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代作的《几赋》:“君王凭之,圣德日跻”。公孙乘《月赋》则有“君有礼乐”之词。羊胜《屏风赋》则有“藩后宜之,寿考无疆”(详见《西京杂记》178-191页)。这种模式可用“咏物+颂圣”来概括,虽然单调乏味,以致王世贞有“梁王兔园诸公,无一佳者”[8]86之讥,但考之于史,也不失为一种创造。
而枚乘的《七发》更体现了梁国对赋这种文体探索的实绩。文中写楚太子疾甚,针石无效,于是吴客尝试治疗,诊断其病因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于是吴客用音乐、美味、车马、游观、打猎、观涛六事来启发太子,结果作用不明显,于是最后吴客用“妙言要道”来治疗,太子一听浑身充满力量,“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病亦霍然而愈。《七发》在内容上劝谏藩国未来藩王不要太过奢靡,这是针对此次诊视的病因而言,但吴客所开的药方“妙言要道”,却似乎功效不遽于是,“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筭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9]。这几味药,老子、庄周、杨朱主张节欲保真,墨翟倡俭,詹何、便蜎以智者称,魏牟关心国家大事,留下了“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名言,孔子、孟子更是积极用世的代言人,其持论多及国家大的根本方面,节欲去奢是其小者。枚乘写《七发》让人不解处在于,对前六个没用的药方,记录甚详,有声有色,惟恐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对于一下子治好楚太子病的药方,却寥寥数语就结束了,给人一种本末倒置之感,由于其不明确性,同时也给人一种感觉,吴客不单矫正了楚太子不良的生活习惯,还对其以后的生活起一定指引作用。刘跃进进一步认为:“枚乘所讲的‘要言妙道’,其实质就是孝悌之道,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劝诫当时等吴楚大国不要忘记这根本的大道,维护汉帝国的统一。”[10]如是,藩国文士用大赋对藩王的介入就更为深远。关于这篇文章的艺术形式,将贾赋中人鸟对答发展为主客问答,并有浓重的策士纵横游说之风,体制更大,辅叙更为华丽,所以刘勰有“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膄辞云构,夸丽风骇”之评[6]161。鲁迅也点明该文在文学流变中的定位:“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11]39。由于善为新声,后人摹拟者众,鲁迅言及这一盛事时云:“汉傅毅有《七激》,刘广有《七兴》,崔骃有《七依》,……谢灵运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梁又有《七林》三十卷,……今俱佚;唯乘《七发》及曹植《七启》,张协《七命》,在《文选》中。”[11]40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体,名“七体”。值得注意的是,《七发》引起人们对赋的文体再认识。刘勰著《文心雕龙》,开“明诗”、“诠赋”章,但却将《七发》归入“杂文”类。萧统《文选》开卷即赋,一直到第十九卷;继而叙诗,从第十九卷第三十一卷,但是虽然选诗赋众多,却没将《七发》选入,而是单列为《七》体,在第三十四卷列为“七上”,可见,《七发》确实有着与众多诗赋迥异之处。
司马相如《子虚赋》也是为迎合梁王文学审美需求而作,“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2]2529现见于《文选》第七卷,或以为此篇和《文选》第八卷的《上林赋》实为一篇,为司马相如为武帝所写的《天子游猎赋》。但不管怎样,在梁《子虚赋》和在京《天子游猎赋》二者必然有很大相似性,只不过后者体制更为宏大,夸饰更为震骇而已。因为司马相如被武帝看上,就是因为《子虚赋》夸饰的特点,司马相如不能不考虑武帝的喜好,进一步演进这一手法。关于这种行文风格,千人一辞,历无疑议。如“《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8]91,“相如之辞赋,淫靡浮艳,堆叠成堆,专为献媚帝王,完全无描写自身心情个性之作品,不过侈丽闳衍,词藻典雅而已。”[12]以此观之,梁王的文学审美观应是追求新奇、华丽、夸张的艺术境界,极尽耳目之欲、视听之娱。他对新兴大赋气势宏阔、铺陈渲染、华美辞藻的特点的肯定从而规定了汉赋发展的方向,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与汉大赋兴于藩国、流布海内相对比的,是藩国纵横文的再变。
纵横文的存在基础就在于各种势力的争竞,一旦这种平衡打破,局势出现一边倒之势,纵横文必然产生变异,直至消失。七国乱平,藩国势力大减,虽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还高唱“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用五霸和三王的业绩来激发梁王,但观其全文,实际只是导泄悲愤而已。董浔阳评:“情至窘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13]352-347至于中山靖王的《闻乐对》,虽也有纵横特色,但在格调上更为卑下,几近哀吊之文。“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不知涕泣之横集也……潸然出涕……臣窃自悲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2]2422
三
汉初藩国的这种文风的转变,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来自藩国君臣对文学特质的探索。汉初藩国招徕文士,组织文学活动,对文士文学创作进行品评和奖惩,应该有一定的标准。邹阳、严忌、枚乘等俱仕在吴,“皆以文辩著名”[2]2338。这个评价应该是和其他文士横向对比,突出三人创作的文学性。枚乘从汉廷回到梁国,“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2]2365。枚乘在辞赋创作上水平更高,非有一定的评判标准莫办。而在和枚乘相较文技的,还有一个司马相如,“乘尤高”的结论,证明了司马相如在辞赋的创作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司马相如后来的成功,也应和这一段文技的切磋分不开。冷卫国、踪凡在《西汉帝王的汉赋观》中云:“大量的辞赋创作以及品高论低、奖优罚劣的活动,势必造成一阵汉赋批评的热潮”[14]。武帝初立,淮南王刘安朝见时,由于共同喜好,两人多次谈诗论赋,兴致盎然。“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2]2145由于谈论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他们的文论观点很可能被身边文人洞悉并影响创作,这一点是肯定的。司马相如在答如何作赋的时候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7]93这种“丽”的特征,后来也被宣帝所承认,“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2]2829。
藩王对文学的审美需求,直接诱导了文学特质的发现。武帝时期作家司马迁论述学术时,多用“文学”一词,如“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孝武本记》),“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同上),“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晁错传》)。在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意义时,多用“文辞”或“文章”,如“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伯夷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传》)“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儒林外传》)这种区分对于原先文史哲不分的文学观念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是与藩王对吴楚之乱后的形势的理性认定有关。汉朝建立之后,封功臣和宗室藩卫汉廷,这和周时的分封制在政治形式上十分相似。异姓藩王被铲除之后,同姓藩王还将自已定位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招纳游士,巩固自已的地盘。淮南王刘长招揽游士“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2]2341,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2]2338,梁王也招延四方豪桀,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2]2145。但是言纵横于藩国,就要受忌于汉廷。七国乱后,反抗汉廷的藩王遭到歼灭,犹疑不决的藩王受到震慑,政治格局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纵横文的衰落就成为必然。虽有藩王喜爱纵横之术,迷恋纵横之文,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敬谢不敏。景帝之子、汉武帝异母兄长中山靖王刘胜就是一例,他被称为“汉之英藩”[15]2099,作品《闻乐对》,艺术水平极高。司马贞在索引中称其:“其言甚雄壮,词切而理文。”[15]2099蔡虚斋评其“愁肠盈襟,悲思满纸,读之一字一泪”[13]352-388。林次崖云:“此对事情激切,识亦该博。佳言美句迭出如贯珠,皆自胸中流出,不见斧凿痕。”[13]352-388唐顺之指出该文对后世的影响:“亦六朝之滥觞也。”[13]352-388就是这样一个对文学有着深刻理解的藩王,却乐酒好内,他理想中的藩王生活为“当日听音乐,御声色”[2]2426。刘胜不喜宾客,独善其身,治中山国42年,也没有形成一个文学中心。但他那种对文学的审美趋向也应该受到注意。所以,对于纵横文的再振,藩王非不愿也,实不敢也。
三是与藩王求奢求美的生活作风互为表里。汉初,虽然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景二帝也以节俭著称,但一些藩王还是凭着权势和财富过着淫靡的生活。一些爱好文学的藩王加入到奢侈的行列,在文学观念上必然会弃质实而求华艳,而藩国文士为了迎合特定读者的口味,也会竭力创造出奢丽的作品来。班固在总结汉初藩国赋家的创作特色时,云:“汉兴,枚乘,司马相如,……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2]2208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梁王,他对赋有着偏爱,自身也尚奢靡。史载其派头之大:“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2]1756坊间也有对梁王的描写,可与《汉书》对照:“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7]114《汉书》还记述了梁孝王“罍樽”故事。梁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他告诫平王大母李太后说:“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2]2214罍樽,应当是商末周初制作的青铜器。“西周时商周铜器,出土至少,值千金亦可以知当时之市价。”[16]梁王不但活着骄奢淫逸,他的丧葬也辅张浪费。据说曹操曾经发掘梁孝王陵墓,“收金宝数万斤”[17]。河南永城发现汉代大型洞室墓。据考古工作者推定,墓主应当是梁孝王刘武和他的王后,以及其子梁共王刘买。陵墓设计施工体现出建筑艺术的成熟。墓室壁画笔调生动,色彩华美。对于这样的藩王,讽喻的内容自然引不起兴趣,汉赋在梁国形成的“劝百讽一”的传统,确实有其现实基础。
汉初七十年,财富的大量增加带动了全社会的奢靡心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2]1136也许,汉初藩王开启了“诗赋欲丽”的文风,更普遍的汉代骄奢习俗才是这种风格得以广泛接受的真正原因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书店,1984:[卷六百“思疾”].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一六];3385.
[5]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1:9 4.
[6]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7]葛洪.西京杂记[M].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8]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9]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三十四];478-484.
[10]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5.
[1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2]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中国大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18.
[13]冯有翼.秦汉文钞[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冷卫国,踪凡.西汉帝王的汉赋观[M]//赵敏俐,佐藤利行.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80.
[1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陈直.史记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1.
[17]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唐宋编子部:卷八三].
Literary Creation in Vassal States of Early Han Dynasty and Changes in their Owners′Literary Ideas
ZHANG Chun-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Literary works in vassal states were mostly created by their owners and their officials,and literary and esthetic ideas of vassal state owners provided huge impetus to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the form of literature is the Songs of Chu,followed by descriptive prose interspersed with verse. Many factors exerted influences on literary and esthetic ideas of the owners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vassal states,such as literary discussion between the owners and their officials,the constantly changing situation, and the desire for a magnificent style.
early years in the Han Dynasty;vassal state owners;literary ideas;literary creation
I206.2=341
A
1008-2794(2009)03-0069-05
2008-09-09
张春生(1971—),男,河南南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