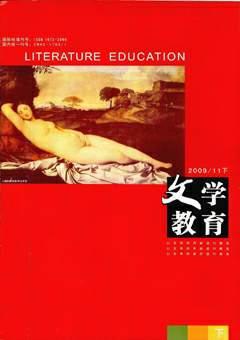中国现代女性的婚恋困境例析
黄 玫
小说《伤逝》发表于1925 年,作为鲁迅唯一一部反映青年男女婚恋的小说《伤逝》,子君和涓生为了爱情毅然挣脱一切束缚走向婚姻,不可谓不勇敢。然而在政治斗争尖锐民族命运飘摇不定的大环境下小资产阶级个人性质的解放成果朝不保夕也是可信的,正所谓“中国的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社会过于黑暗,在广大的社会群众实现广泛的理想是不可能的”。[1]鲁迅自己也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些固然可以看作他们举步维艰,婚姻为之消磨殆尽不可逾越的客观原因。但是任何社会形势之于个人都如海底之于海面,《伤逝》那个年代遥远的社会党争根本不可能有直接左右个人爱恨悲喜的能力。因此《伤逝》的悲剧毋宁说是社会造成的不如说是作为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涓生和子君对于爱情和婚姻不同的价值认同的结果。
一.谋杀婚姻的男性爱情观
作为直接践行分离绝言的叙述者“我”在同子君相爱了一年以后做出“已不再爱”的结论,其心理逻辑过程是这样的:起先“我”和她(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她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2]让“我”觉得找到了能理解自己的人,渴望日日能不停的见到她,“日日对她讲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3]而她恰也是褪了旧思想的新式女性,穿着高跟鞋径直地来我的会所见“我”。对于她的胞叔阻止她与“我”交往,她的回应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这句话震动了我的灵魂,而且说不出的狂喜”,[5]意思是我有的思想她也有,因此“我”等她——竟至于连最爱的书也不能卒读,只要迟来一会,“我”就担心莫非她撞了车,而要立即去找她了。为了把这纯真的热烈的爱示于她,“我”曾“仔细排列过措词的先后,可是临用时却慌乱地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6]
可是婚后,她并不给“我”买的花浇水而只爱小动物,和官太太暗斗却不把这事倾诉与“我”,常常没有一点颜色地“大嚼起来”而因此打断“我”的构思。“我”被局里解聘了,她虽鼓励可是听来也只是浮浮的,透着软弱,而不是从前恋爱时“冷静地、坚决的”子君了。因此“我”渐渐地意识到“我”是不再爱了。
首先,涓生以忏悔之名来澄清自己不爱的理由,不难发现,主要集中在女性难以逃避的厨房四周。把女性的生活常态当作恋爱的对立面给以放大,按照自我需要来定义爱与不爱的标准,然后无情地给出了不爱的结论。无怪乎帕特里克·哈南说“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兼主人公在反思爱情问题时,尽管满心悔恨,却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7]这无疑是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其次,价值判断上,涓生显然是把日常生活完全置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对立面,把摒弃日常生活的“我”确认为树立价值标准的权威,把沉入日常生活的子君判断为价值否定对象。按照女权主义者的解释就是“女人从没有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的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因为他理所当然的被看成是社会生产者。女人则在疲于生殖和家务的奔波中无法保障她获得同等的尊严”。[8]男性作为社会生产者,传统承袭的优越感让他们常常把女性舒展人性的自在的生活常态视为庸俗,而不反思自己是否在婚姻生活中整合进日常生活内涵,这样的思维内隐着可憎的男权意识。
二.“花木兰”式双重标准下的男性婚姻观
无独有偶,时隔大半个世纪,王海鸰的畅销小说《中国式离婚》努力还原了社会上的某种“真实”——真实的观念、现实和无奈。如果这种真实是男女双方在婚姻生活中不断地自审、对话、调整来面对婚姻的失衡,不夸大一方的缺失,不偏袒另一方的疏忽,那么这是一种可喜的警示、反思,无疑是可喜的。可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小说中有一个给读者印象很深的情节,林小枫在穷途末路时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听信娟子的高论尝试买了一件与娟子一样的带“三朵花”的性感内衣,作者详尽描绘了回家之后这个中年妇女怎样笨拙地扮妖娆主动示爱,可笑的是宋建平不仅毫无反应,之后还把这一“遭遇”当作谈资说给别人听,宋建平“跟他(刘东北)说自己的心事,从那天的‘三朵花开始说起,不料刚说了个开头,刘东北就笑得不可收拾”。[9]读者在这样无限夸张的场景面前采用宋建平的心理逻辑认为这样一个平庸、恶俗、中性、保姆般的女性给不了她爱情纯属合情合理。
这无疑是集体陷落到把婚姻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呈现的生活常态对立为女性美的丧失和被爱的权利的剥夺,其实,小说中即便是让林小枫显得可厌鄙俗可憎的种种猜疑,也不过是具有丰富的生命欲求的主体舒展自在人性的正常的反应而已,并非由于林小枫天生独具女人猜疑好事的性格而搥着宋建平的衣角使其陷落到无休止的家庭纷争中。既然你连“诚实”二字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林小枫不愠不怒,是否现代婚姻中女性还应该装聋作哑扮傻以践行作者为女性量身定做的“贤妻”(林母)?同样都有错误而隐含的作者却带着异样的眼光审视和旁观女性出离了理性的疯狂,不过是为男性卸责寻求理解而已。
如果按照作者在访谈中所表示的意在还原社会的主流心态,而如今的主流话语还可以认为是男性的,那么小说中采取的第三人称视角实际上依然是宋建平之流的视角,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读者所产生的一边倒的想法实际上正是男性自我脱责自我掩护的男权话语作用的结果。男性视角下宋健平让读者饱览林小枫的歇斯底里,为自己精神出轨寻求理解,与涓生得出“人必须生活着,爱才能附丽”的逻辑是同质的。不同就在于涓生的年代社会历史的原因等的确是女性获取幸福的障碍,那么历史推进了百年,女性接受了教育,有独立的经济产出能力,却依然摆脱不了为男权话语所排斥和纠正的命运。其原因何在?那就是社会给了女性就业生存的半边天,同时也就给了本身就没有放弃男性覇权的男性另一支指挥棒——从双重的标准要求女性既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又希望她能够像职业妇女一样自立有开阔的视野,希望女性“既要对镜贴花黄做一个标准幸福的女人,又要在一种化妆下建功立业”。[10]只要其任何一重期望得不到满足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夸大自己的感受,无限放大女性的缺失。女性在这样两向倒的标准下处境相当困难。要避开这种处境标准的缺失又是个现实。女性应该何去何从的确值得深思。
三.何去何从的饮食男女
涓生的年代还存在女性没有职业、社会尚未解放等客观原因。而当代社会解放毋庸置疑,女性也并非无业者,而男性又往往采取两向倒的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置女性在现实人生层面上舒展人性、争取爱与自由的努力为日常生活的庸俗态予以嘲讽和压制。女性自从觉醒以来,从子君到林小枫她们争取的权利越来越多,身上背负的压力却在扩大,女性的生存和快乐完全置于男性需不需要和需要多少的逻辑之下。这样单方面地为婚姻和爱情配置上越来越多的指挥棒,而把女性关在幸福的大门之外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尼采曾说“同样的激情在两性身上有不同的节奏”。因此两性之间的和谐不是现成的,它需要一个彼此接受、理解、适应的过程。只要我们承认婚姻,就不能否认婚姻中必包含日常生活部分,这不仅是女性而且是男性应当乐于与女性分享的生活的一部分。把婚姻与日常生活对立,进而与女性的价值对立势必走入婚姻虚无的死胡同。只要一天男性不能正视婚姻生活真正的内涵,不能整合异性生命逻辑,那么婚姻危机就可能随时被引爆。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3.
[2][3][4][5][6] 鲁迅.鲁迅小说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51-355.
[7]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24.
[8]西蒙娜·德·波夫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0:404.
[9]王海鸰.中国式离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63.
[10]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0.
黄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