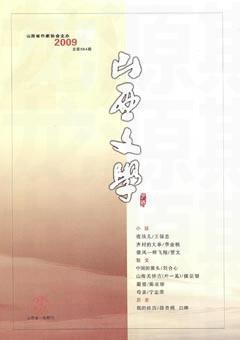凝望
陈亚珍
一
十九岁的母亲安静地定格在古典的相框里,窈窕的身段,穿着一件袖领镶边的连衣裙,白净的脸庞,碎碎的皓齿,两根粗长的辫子垂在胸前,姿态颇有些肃穆,是那种严格规范下的女孩儿。但清纯的气息依然无法掩盖。由于母系是朝鲜族人,母亲有朝鲜族女子端庄与娴静的别致。
我想,父亲就是被母亲这种姿态吸引的吗?
据父亲说:他在营地集训时,一个姑娘从他身边走过,回头向他一瞥,他就记住了这个女孩儿。父亲说,志愿军抗美援朝归国后,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多少姑娘迎面走来都会主动示好,送来甜美的微笑,而母亲只送给他一瞥,这一瞥仿佛是命中注定。
从这点上看,父亲是爱母亲的,可母亲爱父亲吗?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母亲,一直没问出口。母亲很沉静,她的表情看不出悲也看不出喜,母亲到底装了多少心事谁也不知道。母亲十九岁从东北平原跟随着父亲,到这个鸟飞都有些困难的太行山下的偏城,人生地不熟,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几乎磨掉了她所有的美丽。
父亲转业回到地方,常年外出搞农田建设,扎根乡下。领导干部一年288天劳动雷打不动,据说这个决策,得到中央认可,且在全国纷纷效仿。父亲成了“革命”的代名词,如果有人问,你爸呢?我们会脱口而出:“革命去了。”
母亲是一名服装裁剪师,除去饭时,我们几乎也见不到母亲。母亲长时间无法入乡随俗,常为捅火做饭这件事焦头烂额,比如和煤泥就成了无法攻破的难关,红土掺多了黏得搅不动,煤多了,抱不成块,火焰噎住上不来气。因此吃饭就成了问题。有天中午,大热天,火虽没灭,但死活熬不了锅,母亲用斧头劈柴,决定片柴引火,结果小弟从煤池墙上掉下来,母亲一走神,斧刃啪叽劈在自己的虎口上,殷红的血哗然而出……
我们叽溜一下躲到墙根下,像几条大小不等的小狗畏缩在一起,都被吓傻了。眼睁睁看着母亲承受疼痛,却谁也不知道上前救助,只怕谁挨近母亲会赶巧吃一个巴掌。母亲五官扭曲着,眼里噙满了泪……我以为她会号啕大哭,结果没有,母亲只是把眼泪甩掉,找了块白布勒住。
母亲说,早知山西是这种火,死也不来这破地方,真想一跺脚走人!
这话说过之后也不见母亲有什么具体行动。其实我们也很向往东北平原,假如母亲带我们离开山西,抛弃父亲,用不着跺脚,估计集体同意。听母亲说,东北的灶火很方便,几把白草,几片干牛粪,就可做一顿饭,绝不会让谁挨一顿饿。可母亲是个口头革命派,多次说话不算数。有时候我们淘气,她也会说:“听话啊,不听话把你们扔下,我一个人回东北去了,什么破地方……”我们一听此话竟有些凄哀!带我们走,没问题同意,一个人走,留我们咋办呀?尽管有一顿没一顿的,但保证不被饿死还得全靠母亲。
二
母亲从二十岁生孩子,到二十七岁,五个孩子全部到齐,加上夭折的,几乎一年一个。五个孩子出生时,父亲都没有守在身边。母亲说她一个人备好所用,一个人住院。有时候羊水破了,先见红了,母亲在疼痛难忍中一个人往医院里走……
我们姐弟五个,没一个对自己的出生觉得有多么了不起,因为母亲常把我们比做烂柴火,甚至还说把我们一个一个都瘟死。多么可怕,每当母亲生气发火,我们都觉得有可能被瘟死。我们常觉得自己可怜,把我们比做烂柴火还不如是小猫小狗呢,小猫小狗有腿啊,随便找个小窝都可以躲起来……我们对母亲的凶恶胆战心惊!谁也不知道谁会遭到瘟死的下场。
那一年三妹发烧,一烧就是七八天,最后抽风昏迷,水米不进。大人们进进出出,说有可能是“伤寒”。天一直不停地下雨,母亲望着灰蒙蒙的天六神无主。我们怀疑三妹会不会被母亲瘟死呢?我们围着三妹吓得哇哇大哭,母亲烦了说:“悄悄!都不想活了?”哭声戛然而止。母亲用雨布包住三妹冒雨走了。谁也不知道母亲包着三妹哪里去了。大约半个月后疲惫的母亲和瘦骨嶙峋的三妹回来了。这才知道母亲是到阳泉402医院求医,说是半个月没眨一下眼,回来后蒙头睡了整整两天。母亲说,三妹体虚得输液都扎不进针去了,扎了四五针也没扎住,母亲找到医生大吵了一顿,后来护士长一针就扎进去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英雄似的,哼,拿一个要死的孩子学手艺,和他们好吵……
多么奇怪,既然母亲时不时想要瘟死我们,可三妹都快要不行了,母亲还费劲救她做什么呢?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困惑。
面对大小不等嗷嗷待哺的几个孩子,母亲曾对父亲发火说:“看看,你看看,日常营生顾不上做,往肚里扔崽儿倒一点不误事。庄稼不是种上就没事了,还得锄刨浇水。”父亲说:“我咋不锄刨浇水了,我一肩挑俩孩到处找奶妈,这不是浇水锄刨是干甚?找不到奶水能活到现在?”母亲曾经提出辞职养孩子,还说把孩子奶出去都奶黑奶丑了。父亲说这是后进思想,他要母亲走出锅台,为解放妇女做表率。
三
那年,父亲这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无缘无故走了“资”,彻底与家庭断开,一年回一次家。只有两天时间用来“过年”。我们几乎不指望父亲的出现,出现也帮不了什么忙,只会帮助我们吃一年都难得逮见的饺子。我只记得,我们五个孩子的冬暖夏凉,都由母亲在茶余饭后完成。母亲美丽的脸常常很憔悴,很疲惫。母亲没有休息时间,除去上班,班余时间受父亲株连挨审批。在这个“革命”的时刻,有许多家庭夫妻裂变,父子成仇。但母亲没有任何行动,母亲只是拼命挣钱养我们,买粮、挑水、拉煤、备炭,都由母亲挑大梁。有一次买粮,母亲拉着大板车,我意外地发现绳子勒在母亲的肩上,两根青筋凸暴,肌肤磨得血红、最终变成了紫……前腿弓后腿绷,额头上的汗水乒乒乓乓甩了一地。一个美丽的女人变成了一头力大无比的牛!
三十岁的母亲依然是美丽的,走在大街上仍如一个硕大的蜘蛛,扯起的目光如同层层蛛丝,但母亲从不为之所动。母亲的警惕性很高,不接受任何人的恩赐,也不许我们无故受恩。那时候最时兴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母亲让我们有困难靠自己解决,她自己也不例外。她老说一个男人不着调,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有一次拉煤,一个叔叔样的男人前来帮忙,母亲不用,但男人还是执意要帮,母亲无奈,共同把煤拉回家中。母亲的手沾满了黑,男人适时递过自己的手绢关照母亲擦手,这应该是一种温暖,可母亲看一眼男人的目光,接过手绢就扔在地下。
男人从此不敢接近母亲。
母亲与父亲聚少离多长达十二年,可母亲却无丝毫求助他人的意思。我们少不更事时,所有的呵护都由母亲承担。
然而我们与母亲的感情并不怎么贴近,我们曾经不念母亲有多少好,更过分的时候还集体私下咒骂。我们只记得不停地做家务,不停地挨训。挨打是需要时间的,感谢上天没给母亲这样的机会。我们每一天都被训练洗衣、做饭、和煤泥、生火、拉煤、挑水……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呵斥,无穷无尽的活计,没有消停的训斥。母亲给我们的笑
脸很少,但促成母亲忍俊不禁的一次笑,是因为我不慎做坏了一顿饭:玉米面和软了,用火又过长,一锅饭成了面糊糊。
母亲回来揭开锅一看,说,谁做的饭?
我神气活现地说,我。
母亲说这是饭?这是猪食!“咣”一声盖住锅,说你都给我吃了去!
我本以为母亲会表扬我,结果挨了训。那天中午我不敢吃母亲重新做的饭,大家好像对我吃不吃也没太在意。等到母亲上班后,我开始消受我的“作品”。一丝不苟地吃,除了往肚里填,居然不知道用别的办法处理掉。
到了晚上,母亲要姐姐把我做坏的饭蒸了窝窝头。
姐姐说,二丫早吃了。
母亲一愣怔,说全吃了?那么老多,她是怎么吃的?
姐姐说,吃了屙、屙了吃……
母亲吃惊之后,“噗嗤”一声笑了。
而我的泪却汩汩地涌了上来。
母亲说你傻呀?要你吃你就真吃?撑坏咋办呀?
那时候我很茫然,我怎么咋做咋不对呢?母亲的笑让我觉得很屈辱,这一笑让我一记就是多少年。
四
许多年之后我懂得了母亲的悲哀。
十六岁时,母亲向往参军,外祖母为了给家庭留个劳动帮手力拒女儿的要求,后来到部队的被服厂当了女工。
十九岁时,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住满了全城。母亲走在大街小巷,遇到三三两两的军人总会招来满身的目光。“最可爱的人”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最可爱的人”每一天都要接收若干部门前来慰问的光荣。
父亲也是这份光荣的受益者。
当时部队给地方下了一道旨令,一定要给大龄军人找到配偶,如果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可以解除婚姻,追求自由恋爱。于是,各团组织了不同规模的舞会与茶话会,为大龄军人开辟配偶的土壤,用来迅速繁殖婚姻。结果父亲那个团百十多个大龄男人,都先后找到了伴侣,只有老实的父亲不会跳舞,不懂喝茶,让他上台演讲英雄故事,他总是泣不成声。父亲搞不出英雄气概,又无风流倜傥的身姿,因此,合适人选姗姗来迟。
团首长为父亲的木讷着急上火,并挑选了几个恋爱得法者轮番给父亲“上课”。他们的要领有的是“猛、准、狠”,说和打仗一样,瞄准了目标,猛追不放,追到手要狠,容不得她反应过来,生米就做成了熟饭。
另有人说,这样教不对,应是“亲、和、力”,和打仗完全是两回事,说打仗面对的是敌人,恋爱面对的是爱人,“猛、准、狠”非完蛋不可。团里急着要举行集体婚礼,父亲成了拦路虎。因此首长每天都催逼父亲加油,打胜这一仗。
首长看“自主制”不行,就只好“集中制”,说只要你看准,一切交给党安排!父亲在被服厂“视察工作”时,若干如花似玉的女孩儿给父亲送花,而且厂领导不让一哄而上,要有秩序,一个一个上。意思很明了,让父亲的眼睛做到最大程度的努力。女孩儿上一个,有关人员都要认真观察父亲的表情,可父亲的表情千篇一律,看不出对哪个女孩儿有特别的意向,让陪同人员大失所望。就在“视察”结束时,父亲在西南角发现了一个女工,旁若无人,对他的“视察”好像一点不感兴趣,只顾低头做活。厂领导发现父亲目光的落脚点,喊了一声:小秦,“最可爱的人”要走了,别只顾做活,送送咱们的志愿军啊。
这个小秦就是我的母亲。据说母亲当时一脸尴尬地站起来,说,我怕完不成任务……
父亲站住了,与母亲的目光进行了一次短兵相接。父亲后来说,他就是在这一瞬间找到了心中“那一瞥”。可惜,还没来得及仔细端详,对方就又低下头干活去了。父亲说他就看准母亲爱做活。
回到团部,首长问父亲,说仗打胜了没有?
父亲说,“俘虏”了一个,不知人家愿不愿意“缴枪”。
首长说愿不愿都让她缴,告诉她,缴枪的不杀!
母亲就这样成了父亲的“俘虏”,没有商量的余地。而最本质的是外祖母看准了父亲优厚的薪金待遇,可为全家的生活提供帮助。当时父亲三十四岁,母亲十九岁。
五
母亲一生平静如水,其中是痛苦还是快乐呢?
有一次,因为工作问题,父亲不闻不问,还要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不准挑肥拣瘦。我们对父亲的态度表示不满,并且对父亲坚持“大公无私”有所嘲讽。而母亲决然捍卫父亲的神圣,大动干戈,让我们超出了想象的程度。
父亲在临终前夕,曾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母亲,他说母亲不在身边,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要母亲为他照明,为他引路。他总是攥着母亲的手,说大老远把你带到山西,我走了,留你在世上怎么办?我一个人走了不放心……
其实,自从母亲:“被俘”后,哪一天不是独自面对世界?独自撑着一片天空?父亲的扶助是能数得出来的。可是母亲没有对父亲盘点,只要求父亲和她一同上天堂,永不转世。
也许这个约定,被冥冥中的主宰者听到,准许了他们的心愿,并最终促成了“天堂”之行:
父亲和母亲在四十天之内相继而逝。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