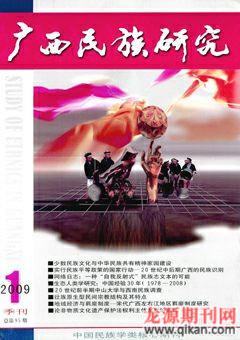作为民族志的个人叙述
张丽梅 胡鸿保
【摘 要】从《尼萨》这部民族志出发,本文探讨了民族志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真实性、代表性、田野伦理和口述史资料整理等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关键词】个人叙述;访谈法;生活史
【作 者】张丽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30-005
An individual narration viewed as an Ethnography
——a sample on the life history of a Queensland woman
Zhang Limei,Hu Hongbao
Abstract:Based on an Ethnography called Nisa,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writing methods about Ethnography as well as some other issues refer to ethnographic writing,such as authenticity,representation,ethics on field and reorganization of material of oral history,and so on. These items are all involved in the theory and approach of anthropology.
Key Words:individual narration;interview;African women;life history
人类学田野工作既是科学的“实验室”,又是个人的“成年礼”,这里既暗含了当代人类学试图融合客体/主体实践的理想,也隐藏有学科内部科学性与个人性之间的颉颃。就具体的融合实践看,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和客观描述之间的关系便很值得重视。民族志著述中对两者关系的处理,既有马凌诺斯基式的随意切换、为凸显客观与科学而对个人叙述着墨较少并使其时隐时现的方式,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0),也有专门叙述个人田野经历和反思的实验性文本,如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8)。
尽管个人叙述在民族志的写作中不可或缺,但个人叙述的主观性和民族志描述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真正解决。个人叙述往往主要是人类学家的声音。然而肖斯塔克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诉说》①(后文简称《尼萨》)则不同,它以主要报道人尼萨的个人叙述为主体,同时注意呈现作者肖斯塔克自己的个人叙述以及民族志概括和评论,通过三种声音的并置,较成功地调和了客观化的民族志表述和田野工作中的主观性经历,并尝试建立个人叙述在民族志表述中的权威。
一、《尼萨》:个人叙述用作民族志
《尼萨》是美国女人类学家肖斯塔克的田野民族志著作,是作者在1969-1971、1975年对喀拉哈里沙漠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进行田野工作的产物。在共计25个月的调查中,肖斯塔克对昆人妇女进行了大量的生活史访谈,而最终翻译、编辑和出版的主要是老年妇女尼萨的个人故事。这好几百页的个人叙述交织着人生的甜酸苦辣、充满戏剧性。尼萨清楚而生动地讲述了她生命中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被抛弃,与其他小孩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母亲和几位丈夫的亡故,以及对变老的感受等等。此外,尼萨还坦率地讲述性行为和女性高潮的细节,受新情人吸引的方式和原因等诸多隐私。尼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讲故事的天分,让读者领略了昆人个体的交流方式以及社会的组织方式,了解到许多昆人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经验的新材料。
显然,尼萨的个人叙述是全书的主体部分,通过对访谈录音的翻译和编辑,她的生活史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得以展现,并按照生命周期的顺序排成从“早期记忆”到“渐渐变老”的15章。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声音”值得注意。一种是属于人类学家的,具体就是每一章前面的民族志概括和评论,它有助于我们在更全面、更开阔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尼萨的个人叙述。另一种声音则是属于作为正在体验异文化的年轻美国女子的肖斯塔克的,它集中体现在《尼萨》一书的导言和结语部分:这主要是肖斯塔克的个人叙述,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作者两次田野经历的背景和过程,在田野中的兴趣、感受和想法,尼萨故事的收集过程和表述框架的形成等。肖斯塔克把三种声音并置,在一种人性化的框架内实现了三者的相对平衡,较成功地调和了个人叙述和民族志描述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认为,《尼萨》堪称将个人叙述用作民族志的成功范例。
二、个人叙述如何用作民族志:相关方法论和伦理问题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跨文化背景中,个人叙述是否能够用作民族志?如果可以,又该如何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和主客体实践的矛盾?对此,肖斯塔克曾以《尼萨》为例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并着重提出了5个方法论和伦理问题:
(1)个人叙述能用作民族志吗?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代表作为整体的文化,那么,该如何处理报道人的个人偏见以及个人叙述与统计学规范之间的差距呢?(2)一个讲述个人故事的人,其个人叙述能被看作是他的真实报告吗?个人叙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访谈关系?(3)个人故事能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在我们的作品中随意使用吗?个人故事的收集和出版在给研究者带来好处的同时,是对报道人不加掩饰的欺诈和剽窃吗?我们最终的责任何在?(4)编辑和翻译过程是如何影响个人叙述的使用方式的?在翻译、编辑与呈现已收集的个人叙述的时候,哪些因素是我们必须考虑的?(5)个人叙述可以用来反观或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吗?②
下面我们将就她这些问题结合其他评论谈谈学习体会。
1. 访谈关系与主体建构性
肖斯塔克明确告诉我们,“个人叙述不能脱离收集个人叙述所涉及的合作过程而独立存在”,“访谈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一个人,回答由另一个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人所提的一组特殊的问题”。③报道人的个人叙述的真实性,也必须放在特定的访谈关系中才能得到较好的辨别和理解。至于“主体构建”,至少有两重,首先是,被研究者构建了一下自己的世界,而后,研究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再次构建被访者的这种构建。在意识到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影响或者研究的主观性的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尊重被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生活、行为等等的构建与意义的赋予,而不是无意识地扩大研究者这个主体,把对象物化,从而导致忽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两重意义上的“主观”性。④
具体就《尼萨》来说,一方面,访问者肖斯塔克作为一名24岁、新婚的美国女性,最感兴趣的是与她自身所处的生命阶段和文化环境相关(美国妇女运动)的问题:“在一个如此迥异于我自身所处文化的文化中,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如果存在普同性的话,它们是什么?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它们?”⑤;另一方面,尼萨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更年期的艰难调适的昆人妇女,她所陈述的生活故事必定是经过某种过滤机制的选择性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真实的、修饰的、想象的,或者三者兼有,但肯定服务于她当下的自我定义。因此,尼萨的个人叙述仅仅反映了“50岁的尼萨和24岁的肖斯塔克之间的暂时性协作”,“任何其他的组合,都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⑥
2. 口述材料的加工整理
肖斯塔克是尼萨生活故事的访问者、记录者、转译者和整理呈现者,她是如何将21次访谈所得的30小时的录音带变成《尼萨》这本条理分明、引人入胜的著作的呢?
首先,翻译是十分枯燥和耗时的工作,而且涉及一些难于处理的问题。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于“重复表达法”的使用。昆人社会有着强烈的口述传统,经常大量使用重复语,尼萨就经常说“我们生活,生活,生活”(通常重复更多次),这在英语中是行不通的。肖斯塔克通常将其翻为“时光流逝”或“我们继续生活”等,但这种译法不能有效地传达出昆人语言蕴含的独特的时间感;于是采取折衷的方案:依然保留一部分重复表达法,只是削减重复的次数。另外,翻译时不能仅仅就尼萨的话翻译尼萨的话,还得参考其他昆人是怎么表达同样的意思的,从而敲定译文是采用标准化的日常表达还是某些更诗意、更书面的表达方式。
翻译之后,大量的译文片段还需按话题进行分门别类,按时序予以大致排列,并进行更为精细的编辑和校定(插入时间用语,去掉确认和澄清性问题,合并重复性叙述,排除无关故事片段,等等)。在此基础上,将尼萨的故事以一种编年体的方式组织并呈现出来。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个人叙述的材料取舍问题上,作者往往怀有隐蔽或不甚隐蔽的偏见,编辑过程绝不可能做到全然客观。Kay B. Warren就认为,《尼萨》一书在涉及性的问题上存在许多跳跃性提问以及模糊或不甚相关的回答,由此可见研究者的选择性和修饰性作用。⑦另外,研究者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和解释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知识体系的影响。《尼萨》成书于1981年,此前学界倾向于强调昆人社会的“与世隔绝”,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肖斯塔克对叙述材料的选择。而在2000年(肖斯塔克逝于1995年)出版的《重访尼萨》一书中,肖斯塔克对《尼萨》中的一些观点做了修正,其中之一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博茨瓦纳(Botswana)与外界有着更多的文化接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狩猎——采集社会。⑧
3. 典型性VS代表性
现代民族志承担着描述整体社会和文化的任务,如果要把某个报道人的个人叙述用作民族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报道人的代表性问题。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作为整体的文化,但肖斯塔克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将个人叙述用作民族志的范例。她的做法是一方面忠实地呈现尼萨个性化的经验和情感,另一方面以所访谈的其他昆人妇女的经历及其他田野工作者的材料与尼萨的经历进行比较,以求达到一种个性和共性的相对平衡,让读者可以将尼萨那些寻常或不寻常的经历放置在全面、开阔的背景中来理解:
和其他妇女的访谈证明了尼萨和她周围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似的。她异常健谈,承受了超出平均水平的更深重的苦难,但以大多数其他重要方面而论,她是一个典型的昆人妇女。⑨
当尼萨说她的初婚发生在9岁,我便从一本出版物中查找女孩初婚的年龄曲线,从另一本中查找婚姻仪式,再从一本中查找相关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比方说,我发现,虽然女孩们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6岁左右,也有一些人早在9岁便结婚了,尤其在尼萨这一代。⑩
肖斯塔克毫不讳言,历尽沧桑、性格开放的尼萨并不具有理想的代表性。然而,社会科学研究中“个案所要求具备的,不是代表性,而是典型性”,“典型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而是个案集中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11]。与代表性所偏向的统计意义不同,典型性主要看重分析和理解的优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Nancy Howell就认为Richard Lee和Irven DeVore等专家在组织化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昆人生活的描述过于简化、缺乏血肉,而肖斯塔克和尼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性化的框架,在此框架内,昆人生活的深描得以呈现,量化的研究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尼萨关于婚姻、小孩抚育和死亡的阐述,也为其人口学研究提供了例证,并使它们显得更为生动。[12]
那么,肖斯塔克的处理是否无懈可击?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有的评论者曾给出委婉的建言:如果采用多个交叉的个人叙述这一替换性方式,是否可能给出一种对高度互依、互惠的昆人社会的更适宜的描述呢?[13]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问题的答案以及相关的困难和质疑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4. 田野伦理
人类学的伦理问题一直以来存在颇多争议。肖斯塔克的回应确有其独到之处。她认为应该超越金钱上的施与受,强调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强调报道人的知情同意,并重点关注双方在情感甚至社会性贡献方面的双赢。
肖斯塔克强调自己的调查、翻译、出版工作主要是兴趣和责任感所致,在个人专著中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尼萨的故事征得了她本人的同意,“尼萨”这个化名也是两人共同议定的,“肖斯塔克的工作,尼萨的故事”正是两人的共识。另外,虽然《尼萨》一书的出版确实让她获利匪浅,但作者在从调查到出版的漫长过程中着实付出了超乎寻常的艰辛。
尼萨的收获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尼萨从肖斯塔克那里获得礼物以及事先议定的报酬,成了变迁中的昆人社会里具有财富和地位的人之一;肖斯塔克还付出了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尼萨所居住的社区。其二,访谈作为一种宣泄途径和自我表达方式,对尼萨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对自身生活经历的回顾和讲述,把作女人的诀窍和生活的“真谛”“教授”给肖斯塔克这个来自远方的“侄女”,尼萨真切地体会到自豪感。第三,对于访谈本身,她也有自己的理解,并乐于通过访谈录音将自己的声音和经验留存下来,使它们不至于随风飘逝。
那么,人类学家对报道人的最终责任何在?这个问题本身是可以商榷的。一方面,如此提问似乎暗含这样的意思:人类学家会对报道人产生某些值得注意的影响,因此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关注和帮助。这种考虑是必要的,也具有合理性,但似有以施恩者自居而凌驾于报道人之上的嫌疑。肖斯塔克就认为,自己在尼萨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小而积极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相反的可能性。比如,在《尼萨》出版后,肖斯塔克曾于1989年重访昆人社会,当时她身患乳腺癌,试图故地重游,重拾友谊,寻求内心的平静,但尼萨和其他人主要以一种功利的方式对待她,并在信息和服务的金钱报酬上不依不饶,令她感到十分失望、沮丧。[14]由此可见,在研究者和报道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避免简单化倾向。
三、结语
传统的功能主义民族志往往强调对作为集体的被研究者的观察和评论,以求客观、科学地认识社会活动的全貌。《尼萨》继承了这一现实主义的传统,致力于呈现一个遥远的狩猎——采集部落的文化经验,并在实质上保留了民族志作者对文化解释和整体文本的单方控制权。然而,与马凌诺斯基式的科学民族志相比,《尼萨》更具内省精神,更强调被研究者的文化表述,作者本人的自我意识也更为突出。
以此而论,《尼萨》可谓主流传统中的民族志实验,在民族志范式上则介乎“文化科学”与“文化解释”之间。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影响。值得称道的一方面是:不曾固守某种范式立场,有利于作者大胆采用个人叙述来写民族志,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相关的方法论和伦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科学性和个人性之间的矛盾。令人遗憾的一方面则是:“主流传统中的民族志实验”也使《尼萨》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综观全书中并置的三种声音,尼萨的声音占据绝大部分的篇幅,可是尼萨自己的解释却付诸阙如,而为尼萨的故事提供民族志背景的“正式”人类学家的声音却倾向于把持单方面的解释权;读者还往往倾向于跳过民族志提要直接进入尼萨富有吸引力的个人故事;作者为了突出尼萨的典型性甚至代表性,又时不时地拿那些很可能被读者跳过的“对其他妇女的访谈材料”或“其他田野工作者的材料”说事儿。也就是说,三种声音并没有在实质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平衡。
尽管如此,《尼萨》不失为将个人叙述用作民族志的成功范例,它为我们处理相关的方法论和伦理问题指引了方向,对于当前的口述研究、性别研究和民族志写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参见Shostak,Marjorie. 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New York:Vintage,1983[1981].
②③⑥⑩Shostak,Marjorie. “What the wind won餿 take away:The genesis of 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In:The Oral History Reader. Perks,Robert;Thomson,Alistair (eds). London:Routledge,1998,P402-413,P405,P406,P405.
④关于主体建构问题,笔者得益于黄盈盈博士的指教,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⑤⑨Shostak,Marjorie. 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New York:Vintage,1983,P5,P358.
⑦[13]Warren,Kay B. “Review".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 12,No. 2. (Mar.,1983),pp. 230-231.
⑧[14]Shostak,Marjorie. Return to Nis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1]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社会学研究. 2002,(5):123-125.
[12]Howell,Nancy. “Review". American Ethnologist,Vol. 10,No. 1. (Feb.,1983),pp. 187-188.
〔责任编辑: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