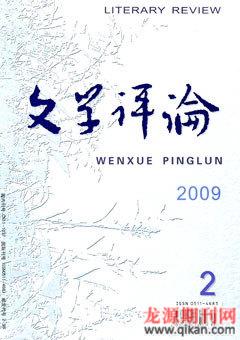怅恨世情与文化才比判
吴效刚
内容提要老舍的小说由一个历尽沦桑的阅世者,采用事理相融的叙述方法,在一种怅惘慨叹的情调中,叙述描写世事人情,以求改良世道人心并改善人的生存状况,形成了怅恨世情的叙述形态。这种叙述形态中包含的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批判思想在于,通过世事描写以显示世情世态,以世事、世情、世态的展现揭示世道人心。这世道即社会世事运行的深层理路和内在规则,就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和亲疏人伦关系。这人心即旧中国国民病态精神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缺乏个体人格精神、缺乏超越灵魂、缺乏抗争精神。
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国外知名度很高的真正走向世界的经典作家,他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还没有得到深入开掘。譬如从叙事角度来看,我们把鲁迅小说的叙述形态概括为悲愤启蒙,把沈从文小说的叙述形态概括为伤怀善美,把张爱玲小说的叙述形态概括为苍凉感悟,而如果这种在比较中得到的概括能够凸现这些作家小说的叙述特点,那么,老舍小说由怎样的叙述者、叙述对象、叙述方法、叙述情调构成了什么样的叙述形态?再譬如,人们普遍认为老舍小说具有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意旨倾向,可是,与鲁迅等同样具有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倾向的作家相比,老舍小说中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独特内涵是什么?老舍文化批判之真义是什么?另外,任何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地与新的时代生活进行对话,使读者能够获得在当下生活中的精神抚慰和借鉴意义,那么,老舍小说中具有怎样的与当下生活进行对话的资源,能够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包括文学创作提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虽然老含小说中市民生活的描写、幽默风趣和鲜明的京味儿都是其突出的特点,但我相信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回答,能够把对老舍小说独特审美个性的发掘推进一步,同时也能够为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对话拓展领域。
一
老舍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饱经沧桑的阅世者。在有些小说中,这个阅世者自身具有深广的生活经历,《我这一辈子》中的“我”作为主要人物兼叙述者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困苦,在饱经沧桑之后通过回忆来叙述过去如何当过裱糊匠、巡警,当巡警时如何巡街执勤、守护官僚私宅和任职官府、放任外地,如何经历个人的升迁沉浮和社会的动乱变迁,可以说是阅尽了人世。在有些小说中,这个阅世者是作为生活的观察者览阔人世。《四世同堂》第一部第一节叙述祁老人的经历,说他壮年时亲眼看见过八国联军怎样进北京,后来又看到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战争,现在又遇上了日本人打进北京来。祁老人成为一个饱经沧桑的阅世者,而叙述者作为祁老人生活的阅历者,自然具有更为丰富的世事阅历,他对北京地区方方面面兴衰变迁的熟稔突出和强化了他阅尽人世的特征。
这个叙述者因为阅尽了人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所以,他的故事情节、事件的前因后果、左右关联是那么情合理顺,从不会让人感到虚假突兀;他的人物的言语行为是那么妥帖合度,从不会让人感到别别扭扭。因为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的叙述过程总是贯穿着对世事、人生、社会透彻的认识和理解,时时绽放出认识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因为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所以他的人物对话往往会成为饱含哲理的警语格言。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形成了其对叙述对象既沉入执着又超越远瞻的心理,形成了自信、坚定、沉稳的叙述态度,形成了机智、幽默、风趣的叙述格调。鲁迅小说怀疑的叙述者的怀疑特质既能唤醒读者的怀疑和反叛意识,但也会使人走向苦闷彷徨。张爱玲小说个体化叙述者的苍凉感悟既使人悟彻人生之真谛而豁然敞亮,又会使人不禁心生悲凉。沈从文小说生存勘探者的叙述者对感性生命的抒写使人领略到生命的畅快淋漓,但又不免给人以虚幻之感。只有老舍小说饱经沧桑的叙述者既脚踏实地热情触摸着日常生活,又时时以超越心态睿智冷峻地批判世事,使人感觉到这个叙述者是一个可信、可靠、可亲、可爱的叙述者。
老舍小说的叙述对象是世事、世情、世态、世道、世人。他不注目于重大历史事变,也不注目于官场攻伐、商场争斗、情场游戏,他专注于叙述一般的、日常的、世俗的生活状况。即使《四世同堂》这样反映民族战争的作品,也把政治军事斗争作为背景,重在描写普通市民在民族战争中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情感。他的小说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笔触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描写了社会的各色人物,构成了一幅中国社会人生世事的真实画面。他要通过这幅人生世事的画面来显示中国社会的世情、世态和世风。而他这种取材和叙事的取向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柬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在《人物描写》中说:“这里所谓的幽默家,倒不必一定是写幽默文字的人,而是说他必须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在《储蓄思想》中说:“有了思想,你该再注意世态。思想是抽象的,空洞的;世态是具体的,实在的。用你的思想去分析世态,而后你才会从浮动的人生中找到脉络,才会找到病源。……你须描摹世态,而描摹世态,正所以传播思想。所谓具体的描写并非照相,而是以态寄意”。在《我的“话”》中说:文学家的语言“必定是从心眼里发出来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动人的言语,使人咂摸着人情世态,含泪或微笑着去作深思”。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地、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写它。”老舍关于小说创作的自述说明活跃在他的意识深处的是人生世事的鲜活画面和对世情世态世风的观感和认识。
“这位人世甚深的作者”用他对世事人生的叙述给我们显示的旧中国社会的世情世态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极其荒诞的生活的不公正和不公平。这种不公正和不公平已经演化成为强者肆意掳掠损害弱者的弱肉强食。在《骆驼祥子》中,如果说祥子用血汗钱买的那辆新车被乱兵抢去是发生在兵荒马乱的非正常时期,那么,孙侦探打劫他千辛万苦积攒的那点钱却完全是在正常安定的环境中,那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有弱肉强食一条规则。第二,人们在做人、做事中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敷衍苟且、怯懦因循、卑怯屈膝,这些病态精神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不仅像祁瑞宣这样具有使作者梦牵魂绕的传统美德和现代意识的人物也只能鼓动别人(瑞全)勇往直前而自己仍苟且偷生,就连叙述者本身似乎在冥冥之中也不自觉的顺从了一种怯懦、屈从的生活逻辑,如在《骆驼祥子》中关于那位老车夫老马两次在祥子的生活里出现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对老车夫和祥子不幸遭遇的不平,但是并没有感受到对老车夫和祥子屈从命运、放弃个人抗争的质疑。当然,在老舍的小说中有赵四、李景纯、李子荣、丁二爷、祁瑞全、钱默吟等作者理想的人物,但这些人物的侠义、勇敢、真诚、务实与那种普遍的病态精神相比还是显得纤弱。
老舍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流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怅惘情绪。这种怅惘来自于对传统文明在时代演进中不可避免的衰落消失的失意和眷顾。《断魂枪》中叙述者对以断魂枪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华曾经辉煌的眷恋和如今衰落的惋惜造成了一种回肠荡气的悲凉气氛。《老字号》中的“三合祥”几十年来在经营上形成的言无二价的君子之风甚至让浮华、奸巧的新派商人周掌柜觉得“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了天成了”。《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新韩穆烈德》中的田家都是忠厚人家,恪守诚信经商的信条,然而在别家的店铺“花样翻新”的经营策略面前,他们只能败落。这些作品怀念那些与旧的经营方式同时共存的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环境和笃实、诚信、淳朴的道德风气,它在新的时代生活中的节节败退使叙述者叹惋不已。这种怅惘情绪也来自于对传统文化中落后部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转换更新的艰难滞缓而生的失望和迷惘。《猫域记》里猫人沉醉于那种使人懒散、健忘的迷叶的争夺和享用之中,他们的文化是一种能改变外来文化而自身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文化。小说第二节描写“我”落人猫人手中,“他们握着我的双臂,越来越紧,……每只胳臂上有四五只手,很软,但是又很紧,并且似乎有弹性,与其说是握着,不如说是箍着,皮条似的往我的肉里煞。挣扎是无益的,我看出来:设若用力抽夺我的胳臂,他们的手会箍进我的肉里去。”这是一个异类被猫人“软箍”的意象,它显示了猫人的文化如何“软箍”外来文化。猫人的愚劣使他们面临着国家灭亡的危险,举国之中唯一的清醒者老鹰自愿将自己的头悬在街上以警醒那些不受小蝎调遣的兵将们起来保家卫国,然而那一批庸众只是麻木地观赏谈论,他们并不问“这是谁?为什么死?”这类传统文化中的劣败面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更显出落后性,然而它的转换更新却是那样艰难滞缓,以至于老舍在年轻时就立下了为革除这种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如同耶稣殉难那样牺牲的决心:“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和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他为改造旧文化而赴难的悲凉意绪和对改造旧文化的艰难的无奈感受融化在叙述中,便造成了怅惘凄迷的情绪。老舍小说中的怅惘情绪还来自对不公正不公平社会中民生艰难困苦的怨恨。《月牙儿》中主人公的痛苦、《我这一辈子》中“我”的凄凉、《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不幸,都使叙述者无限悲伤。“是的,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我的眼前时常发黑,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老舍小说的全部叙述似乎就在《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这种如泣如诉、怨恨交织的语调中行进。
老舍曾经说过,小说叙述“必须把思想、艺术、感情完全打成一片”。他小说的叙述正是他的这种叙述主张的实践。他采用的是融事、思、情、美于一体的叙述。他的叙述不是纯客观的描写和陈述,而是一种述说,在叙述中常带着说和评;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既“述”又“作”。他在事件情节的叙述中常常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的深层本质,常常对事件进行概括提炼,发出富有哲理的语言。他的人物语言既是人物心理意愿的表达,又是对世事的深刻认识,常常蕴含着洞明世事的道理。他的景物、场面、社会风习以及人物面貌、外在动作的描写总是与人物的心理、情绪、品性高度融合。人们大多认为张爱玲小说的叙述中贯穿着即物即事而来的感悟和幽思冥想,使叙述成为意义的生产者,成为形而上哲学思辨的蕴藏库。但是人们并没有过多注意老舍叙述中的哲理蕴含。其实,老舍融事、思、情、美于一体的叙述方法,使得他那幽默干练的情节叙述中时时有哲理的警语,使得他那活泼生动的景物和场面叙述中贯穿着透彻的人情物理。说老舍小说的叙述是世事哲理的蕴藏库同说张爱玲小说的叙述是形而上哲学的蕴藏库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老舍小说的叙述动机存在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他强调显示事物的意义。他说:“我们应先看出事实中的真意义,这是我们要传达的思想,而后,把在此意义下的人与事都赋予一些感情,使事物成为爱、恶、仇恨等等的结果或引导物。”就是说他要通过叙事来揭示世事世情的真相和本质特征,并引起读者的爱憎情感。其次,就是文化批判。老舍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之前,就确立了从文化改造角度切人社会人生的追求,并立下了为破坏和铲除旧的“有毒的文化”而牺牲的志向,而他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到了抗战时期,老舍已经形成了较全面系统的文化批判思想。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指出,“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然而,“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所以,他说他的《大地龙蛇》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能体会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的一点意见”。这话虽然说的是《大地龙蛇》的创作意图,实际上老舍的全部小说都可以作如是观之。再次,对人生的解释和生命的探索。老舍在《怎样写小说》一文中说:“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录。那么,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估计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又有什么启示。……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只有这解释才能使小说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也只有这解释才能把小说从低级趣味救出来。”他在《论创作》中又说:作家创作要“看生命,领略生命,揭示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花。”一般认为沈从文小说创作探索生命存在的意图很强,其实,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探索,对改良世道人心和改善人的生存状况的执著,在老舍创作中成为其叙述畅快淋漓展开和推进的重要动机和活力。
通过上述对老舍小说叙述的几个重要因素的讨论,我们对老舍小说的叙述形态可以作如下描述:一个历尽沧桑的阅世者,采用事理相融的叙述方法,在一种怅惘慨叹的情调中,叙述描写世事人情,以求改良世道人心并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概括而言:怅恨世情。
二
评论者普遍认为文化批判是老舍创作中最有独特价值的思想蕴涵,但对其文化批判内蕴如何阐释才更符合老舍小说的实际呢?通过对老舍怅恨世情叙述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老舍通过世事描写以显示世情世态,而世事、世情、世态展现的目的是揭示世道人心。这世道是污浊的,这人心是低劣的,它是由文化培育并制约着的,这文化也是落后的、腐朽的。老舍怨恨这污浊和低劣的世道人心,怅惘这落后文化转型之艰难,渴望着改良世道人心和改造传统文化。老舍于1940年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邀请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对于研究老舍思想很重要,对于理解老舍
小说创作的动机意图和他小说叙述的内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演讲中谈到中国社会因缺乏灵的生活、灵的文学而形成的卑劣状况。他认为“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但是,中国近两千年来,“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里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里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人民的心理卑鄙无耻”。“最奇怪的,中国文学作品里没有劝善改恶的东西,很多的书本里,虽也有写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眼,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的灵的文字”。“没有灵的文学出现,怎能令人走上正道,做好好的国民?”“因为人民缺乏灵的文学滋养,结果我国的坏人并不比外国的少,甚至比外国还要多些,大家都着重于做人,然而着重于做人的人,却有很多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叫他吃点亏都不肯,专门想讨便宜,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中国社会每阶层,无不充满了这种气氛”。因此,他希望中国有一个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希望有人“发心去做灵的文学的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的心”。如果把老舍这次演讲的内容和他小说中描写的世态人情联系起来看,就能发现老舍怅恨世情的叙述形态中包含着何等深刻独到的文化批判的真知灼见。
老舍揭发旧中国社会世道污浊之事实,揭示了这污浊世道之道——社会世事运行的深层理路和内在规则,就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和亲疏人伦关系。在中国传统家族血缘关系中,人生而不平等,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有着天然的等级界限,家族内部与外部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疏不同。由这种家族血缘关系向外扩展形成了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各种不同等级、不同亲疏的人伦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规定了这种等级和亲疏人伦规范,在千年封建社会中,这种等级、亲疏观念和伦理规范已经渗透到国人的血液命脉里去。中国社会从清末的改良到民国到北伐到抗战,加上其间外国科学文化的输入,变化使人眼花缭乱,但老舍向人们展示了;世事和社会运作的深层规则——等级和亲疏人伦关系始终不变。
《正红旗下》写“我”姐姐做媳妇时应对家族等级亲疏关系的艰难,《我这一辈子》写当徒弟的“得听一切的指挥和使遣,得低三下四地伺候人”,“一个学徒的脾性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被板子打出来的”。《老张的哲学》中龙树古的人力车在马路上翻车,巡警先是毫不在意,但当接到龙树古递过来的印着救世军军官的名片时,立即向他行礼并照办一切吩咐,因为北京的巡警“只要你穿着大衫,拿出印着官衔的名片,就可以命令他们”,老张待人刻薄无情,但当“学务大人”巡查学校时,他和孙八等人使却尽了低头哈腰曲意奉承之能事。在老舍的叙述中,家庭成员、师徒、主顾、官民之间都存在一种有形无形的森严的等级关系,人与人之间存在内外、远近判然有别的亲疏关系。这种等级人伦关系把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平等看作是天经地义,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既然在上者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削和奴役在下者,因此人们自然就千方百计向上爬以获得更大的权利,这就是旧中国社会几千年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思想的根源。这种等级人伦关系把人在人格精神上的不平等也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从而把人的不平等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在思想情感上的不相通。孙侦探根本不可能理解祥子的艰辛,所以他心安理得地敲去了祥子的钱;但是,祥子也根本不知道刘四对虎妞毕竟有父女之情,所以他十分得意自己不告诉刘四虎妞的坟在哪儿。这种亲疏人伦关系把对内外、远近不同亲疏关系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和至高无上,导致了普遍地重视带有自然性人情关系而不重视人与人之间建设性的尊重、信誉、互助的人际关系,导致了普遍地利用人情关系讨好处和便宜甚至邪门歪道、弄虚作假倡行而难以形成遵守法规的风气。
老舍揭发旧中国国民精神的病态,揭示了其病态精神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缺乏个体人格精神、缺乏超越灵魂、缺乏抗争精神。在老舍小说中,无论老派市民、新派市民还是正派市民,他们身上的精神病态都凸现着这些深层文化心理的“景观”,只是我们的认识不要停留在那些病态精神的表面,正如老舍谈到《骆驼祥子》时所说,他“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下面让我们以祥子为例进行分析。
祥子在遭遇孙侦探敲诈和恐吓后逃到王家老程处,深更半夜睡不着,他先是对曹宅放心不下,继而想到自己何不去偷几样东西来,反正院子中没人,但当他打消了这个做贼念头后紧接而来的则是对自己可能被诬以作贼的恐惧,因为高妈知道他到了王家,要是夜间曹宅果真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他急得手心上出了汗,翻来覆去不能安静下来,直到把老程叫醒,让老程检查自己的东西,能证明自己没有偷曹宅的东西后才安下心来。祥子这段紧张翻腾的心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必须经由老程证明他没有做贼才能安心,也就是说,他不能自己确定自己,而要完全依赖别人来确定自己。从祥子因看清了车夫老马一生穷困潦倒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可知,他在人生路途的重要时刻不是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作出判断和选择,而是依从别人的经验或顺从外在的理由。一般认为虎妞的骗婚使祥子无奈并受到精神的摧残,其实,在祥子与虎妞的婚姻过程中,样子基本上放弃了自主性,任虎妞操纵事情的发展。祥子的所有这些行为表现了他心理深层的缺陷——缺乏个体人格品质。他没有自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意识,没有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的精神,没有自我独立选择和承担责任的品质。这种个体人格品质的缺陷是旧中国国民普遍的心理素质,而这种心理素质正是泯灭个人的旧文化传统所培养。“中国人对‘人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立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所以,中国人总不能由本身去确定‘自我价值,而必须常常以别人为学习对象。”但这种对人的设计和培养恰恰是违背人本来的规定性的,是反对生命的,因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就在于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是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在西方文化中,从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摆脱原始群体意识而萌生个体意识。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认为,既然世间万物都是由不可人的单个原子构成,那么人类社会也就是由互不粘连的独立个人组合起来的,在这种组合中个人的独立性并不被打破。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个体性从自然哲学的物质结构提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为个体独立性的存在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理由。从这种文化传统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始终承认并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个体和权利主体,因而形成了西方人由自我去定义世俗关系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品质。老舍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达到了对旧中国国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
祥子从农村来到城里,一心想凭着自己的勤劳拉车谋
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自己的车拉,并且娶个能吃苦的媳妇。但是祥子的一切努力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都成了泡影。祥子的奋斗和挫折常常被评论者说得神圣而悲壮。其实,祥子的愿望、理想和在现实挫折面前的败退正显示了祥子身上最可怕的精神缺陷——缺乏超越灵魂,缺乏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追求。他没有个人信仰,没有个人价值的理念,没有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没有精神探索和体验的情操,也没有服务民族、国家、大众的境界,他只有拼命拉车攒钱以安身立命。这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生活,“这种不要有‘灵魂的事业,不要让自己放光放热,只图保住臭皮囊,使它‘可以尽年的活命哲学,基本是一种身体化的哲学”。这种身体哲学使人缺乏与命运抗争的意志和精神,而这正是祥子身上另一种可怕的精神缺陷。
祥子在他遭遇的一系列打击面前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抗争。他顽强拉车挣钱的努力并不是什么抗争,而仅仅是一种求生的动力。孙侦探勒索他的钱时,他最强烈的反抗就是说了那句“我招谁惹谁了?”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声音很微弱,微弱到几乎是自言自语,微弱到几乎不敢把对方当作明确的怨恨对象。老舍小说中还有一些人物也说过类似的话。《离婚》中张大哥在其儿子张天真被特务抓走后绝望地哀叹道:“我得罪过谁?我招惹过谁?”《四世同堂》中韵梅听到祁老人说日本鬼子打进北京“不出三月,事情便会平定”后,也说:“咱们管谁也没得罪过,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这句话表现出一种自足自保而放弃自我主动性的心理特点,在遭遇不平后满足于这句话不做实际的抗争,就是软弱和卑怯。《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淋雨患了一场病:
他躺了十天。越躺着越着急,有时候他爬在枕头上,有泪无声地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挣钱,那么一切花费就都得由虎妞往外垫,多咱把她的钱垫完,多咱便全仗着他的一辆车子;凭虎妞的爱花爱吃,他供给不起,况且她还有身孕!越起不来越爱胡思乱想,越想越愁得慌,病也就越不容易好。
……假若病老不好,该怎么办?是的,不怪二强子喝酒,不怪那些苦朋友胡作非为,拉车这条路是死路!不管你怎样卖力气,要强,你可就别成家,别生病,别出一点差儿。哼!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又招谁惹谁了?不因生病,也不是为成家,就那么无情无理的丢了!好也不行,歹也不行,这条路只有死亡,而且说不定哪时就来到,自己一点也不晓得。想到这里,忧愁改为颓废,瞎,干它的去,起不来就躺着,反正是那么回事!他什么也不想了,静静的躺着。
到八月十五,他决定出车,这回要是再病了,他起了誓,他就去跳河。
从这段心理活动来看,祥子内心深处也一直交织着倔强、顽强、奋斗与软弱、退却、颓废的矛盾,但这种顽强奋斗,是为了眼前的日子,并不是因为认为人本身就应该奋斗。这种软弱颓废来自于安生的渴望,因为当奋斗的艰辛有甚于穷困屈辱的困苦时,他就放弃奋斗。跳河自杀当然不能叫做抗争。因为当个体面临强大的现实压力时,如果是毫无个体精神和自我意识,就会退让屈服,而如果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而没有顽强的自由意志,那就会以自杀来逃避承受不住的压力。所以,自杀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抗争。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