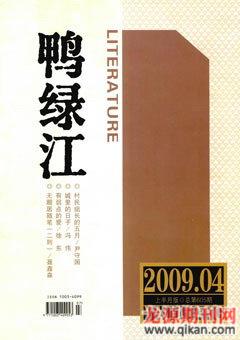城里的日子
冯 伟
米镇最热闹的地方要属腰街了,这儿的人都管腰街叫裤裆街。其实腰街就是个三岔路口,岔口的北端是一个新建的大型建材市场,每天都有无数的建筑材料从这里出出进进,人也自然是进进出出,或买或卖忙个不停。在岔口的西面是个银行,人民银行,银行门的两侧摆放着两个威风凛凛的大铜狮子,一个是张着嘴的,一个是闭着嘴的,意思是有出有进,财源不断。银行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校,学校是封闭的,从里面看不到外面,从外面也看不到里面,高高的围墙与世隔绝。在学校围墙的外面是一排1975年地震时遗留下来的简易房,已经很破了,原本白白的屋身,多年来被风雨侵蚀得破败不堪,灰头土脸的,打远看,像块脏兮兮的膏药贴在了那里。按米镇的市容规划,这样的房子早该扒了。可就是时时没动,到现在两年多了,还是那么鸡立鹤群,挤在高高的楼下,看上去那么猥琐,像个乞丐站在一群大款面前,既寒酸又无精打采。在银行的旁边也是一排房屋,新的,是用大块儿大块儿的玻璃围起来的那种房屋,宽大而明亮,从外面往里面看一切都很清晰,干净,和这边的旧简易房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寒鸦,一个鸾凤。
在“寒鸦”和“鸾风”门前的路旁总是站着一帮一帮的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他们是打短工的。正是冬天,刚刚下完雪,从月历牌儿上看再过个月儿八的就要过年了,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些人想趁机多捞几个,回家过年,可越是想多捞就越是捞不到,打工的人太多了,用工的人更是有限,一天天地没活干。他们糗在那里,脚旁或是立着个小牌儿,或是戳着什么工具:修炕的,刮大白的,钻眼儿的,维修下水道的,做防水的,搬家的,还有一些做苦力的装卸工等,七十二行手艺,各显神通,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岔口处简易房的第二家是爿小饭店,门楣上横挂着一块涂有深绿色油漆写着红字的简陋牌子,牌子不大,由于颜色不协调,并不显眼,反倒显得很俗气,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夫妻小吃”四个字,那字看不出体,也不是什么美术字,笔道儿是用板刷硬戳上去的,一看就知道写字的人没多少文化。
饭店不大,憋屈,也不那么明亮,屋身是青砖垒成的,赤裸裸的没有装饰;一个小窗子,是木制的,原本蓝色的油漆已经斑驳了;门是新的,铝合金的,和窗子比起来很不协调。由于门不严紧,冬天怕进风,在门的里面挂着两扇大棉布帘子。拉开门儿挑帘子进去,靠门口的旮旯处放着一捆大葱和两袋子土豆。那葱已经蔫了,葱叶儿早没了绿色,从葱梢开始黄,直黄到腰部,软塌塌地堆在了那里。土豆是用装尿素的编织袋儿装的,看不见土豆,却能联想到尿索的味道。屋里只能放四张小方桌,中间是过道儿,左边两张桌,右边两张桌,桌子是那种二三十块钱一张的,灰白色,有的桌面已经破损了,露出了烟黄色锯末子,用手一碰直掉渣儿。凳子就更便宜了,红色塑料的,大街上摆着卖的那种,明码实价,五块钱一个,坨儿大的人坐上去,凳腿就发颤,像得了软骨病那么难以支撑。地面儿是水泥的,由于天天擦,灰号大的地方擦亮了,灰号小的地方擦破了,露出了沙子,像一张长了癣的脸那么难看。在厨房和饭厅的过渡处有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床,床上堆着一些脏衣服,一个笤帚头儿,还有一袋子大米,靠米袋子上方的墙上是个木架儿,木架儿的上面站着一个人,财神关公,正满脸通红地拿着大刀站在那里,那架势,看哪个吃饭的人敢不给钱就走,他一定会毫不客气地从上面跳下来,挥起青龙偃月大刀跟他玩儿命。在关公的身旁是个很精致的木制相框,里面镶着一张照片,彩色的,是一对夫妻和一个小男孩儿的合影,三个人笑着,很开心的样子。再往里就是厨房了,厨房有些暗,虽说亮着灯也不是很亮,有一股刚刚炒完韭菜的油烟味儿弥散开来。厨房没有案板,只有一个稍微宽一些的灶台,也不是那么规整,东边一棵葱,西边一瓣儿蒜,这儿一把蒜薹,那儿半碗大酱,显得既拥挤又零乱。墙早已被油烟熏得黑乎乎的了,你绝对不能往上看,谁看谁吃不下饭。靠东面的墙上是个碗架,没了木质的本色,锅碗瓢盆也不光亮,大多都有磕磕碰碰的痕迹,瓷制的,不是裂纹,就是掉了茬儿,像是吃饭的客人不小心,“嘎嘣”一声给咬下去的。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田大奎在灶台上炒着韭菜,老婆徐二梅站在大奎身旁的灶台边做下手,切着干豆腐。她一只手按着,一只手持着菜刀,一下下地切。那磨得锃明瓦亮的菜刀切着软绵绵的干豆腐,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声,随着刀的一起一落,一些匀称的豆腐丝儿花瓣儿一样一束束地绽放了。相比之下,倒是男人更忙乱些,从后面看男人的两只手臂在不断地摆着,一只手握着大马勺,一只手拿着小炒勺,不停地舞动。炒菜的声音很大,小炒勺碰着大马勺,铁碰铁,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二梅看了一眼,说:“轻点儿,马勺敲漏了。”
大奎不言语,继续敲,直到把一个菜敲熟了,盛到盘子里,说:“你懂啥?厨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敲马勺,不敲就没意思了。”
二梅看了男人一眼,心说毛病就是多,便将切完的干豆腐放到一个豁了口的盘子里,递给大奎,说:“敲吧,这点劲儿都使在白天了。”说着,端起那盘儿炒熟的韭菜走了出去,身后便又响起那叮叮当当的脆晌。
屋里只有两个人在吃饭,是他们的邻居,刮大白的,男人叫大白胡,女人叫大白赵,两个人不愿做饭,每天中午都要在这里简单地吃上一口,人也就都熟了。他们不是本地人,大白胡是黑龙江的,大白赵是安徽的,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是不是夫妻,反正两个人住在一起,还总吵架。
二梅将韭菜放到大白胡和大白赵眼前的饭桌上,说:“这雪真不小。”
大白胡拿起筷子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说:“电视上说了,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二梅说:“这天儿,没活儿干。”
大白赵也吃了一口,说:“来两碗米饭吧。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闲着。”
二梅边盛饭边说:“你们还行呢,像咱这样的就更完了,为了挣两个破钱儿,一天累得大梁骨都要断了。”
大白赵说:“你有福,找了个能干的男人。”
二梅岔开话说:“又一年。真快。”
大白赵说:“再干个十天半月的,就得回家过年了。”
马勺响了,二梅进厨房去端菜。
二梅刚进去,大奎走了出来,边走边用围裙揩着手,也不说话,直接来到了门前,将一扇棉门帘的一角儿挂到门框的一个钉子上,露出一块玻璃,站在那里往对面望。
小饭店的正对面是个大酒店,斜对过是个药铺,大酒店的门面装饰得漂亮,像个孔雀在开屏。药铺虽不那么豪华,在雪的映衬下却明亮得耀眼。药铺没有牌子,就一个写有“药”字的白色布幌儿,像一个永远也放不起来的风筝,在随风飘摇。药铺也不是很大,里面有两个女孩儿在卖药,她们穿着白色的大褂,天使一样守在那里,等着服务,你想买什么,她就给你拿什么,吃好吃坏你自己的事儿。
正在大奎望着、想着的时候,门儿一响,又进来一个人,是水暖工陈秃子。陈秃子没戴帽子,就那么挠着头皮,捂着耳朵,光溜溜地进来了,像个大灯泡儿,他先是跟大奎点了下头,说:“还是屋里好,暖和。”
大奎表情木讷地问:“今天吃啥?”
陈秃子说:“老一套儿。”大奎就进厨房准备去了。
陈秃子坐下来,又对大白胡和大白赵说:“还是你们吃饭积极。”
大白赵说:“饿了就吃呗,早晚一顿儿。”
陈秃子看了眼大白赵说:“大嫂,什么时候又买一件衣服?一定是挣着了。”
大白赵说:“没挣着也不能光着。”
陈秃子又问:“你的脸咋了?”
大白赵说:“咋了?没咋。”陈秃子说:“还没咋,明明是让人给啃了嘛。都紫了,你当我看不出来。大哥的劲儿使得也太大了吧。”大白胡吃着饭,红着脸,也不说话。
这时二梅走出来,对陈秃子说:“你的老一套没有了,换个别的菜吧。”
陈秃子说:“那就给我来个爆炒大头菜吧,一碗饭。”
二梅说:“你拉屎肯定没有油,能不能吃点儿正经东西,吃个鱼吃个肉什么的,一年了,也没见你吃过一回荤腥,都像你这样的客人我什么时候能发家?”
陈秃子说:“你指我发家呀?那可真是老爷子看好儿媳妇——指不上了。”
大白赵说:“人家是攒钱,准备娶二房呢。”
陈秃子说:“我怎么攒钱也没有你挣的快。”
大白胡说:“秃子,你别在那儿胡诌好不好。”
厨房里又响起了敲马勺的声音,工夫不大炒甘蓝的味道就传了出来。
大白胡说:“炒大头菜的味道还挺好闻呢。”
陈秃子说:“过来一起吃吧,天儿冷,咱俩喝点儿。”
大白胡说:“不用了,吃完了。”
马勺又响了起来,二梅将菜端了出来,放在陈秃子的桌上,问:“还要大葱吗?”
陈秃子说:“有就来一根儿。”又说:“冬天大葱太贵,不好意思管你要。”
二梅说:“看你说的,一根大葱值几个钱?真要是想让我多赚钱下次就要个鱼要个肉什么的。”
陈秃子说:“大嫂,我这人吃鱼吃肉都过敏。”
二梅说:“那你就在家吃你老婆的奶吧,原汁的,还绿色食品呢。”说着就又折到了后厨,将掉在地上的半棵葱拣起来,两手一使劲儿,掐头去尾,在一个盛有洗碗水的盆子里涮了一下,就那么光溜溜地给拿了出来,走到陈秃子身边,用葱在陈秃子的光头上敲了一下,说:“吃吧,免费的。”陈秃子笑嘻嘻地躲闪着,接过葱,看也不看,上去就是一口。
二梅看了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就又回到灶间去了。
大奎炒完菜,又一次出来,他看了眼吃饭的人,还是来到门口的那个位置,往外看。
对过的大酒店已经有人来吃饭了,一辆辆车停在那里,三三五五的人出出进进。大奎看了一眼,喉骨滑了一下,又把目光抛向对面的药铺。药铺里的两个女孩儿没事可做,一个在看报,一个在拖地。二梅从后面走过来说:“今天你是咋了?总往对面看啥?”
大奎看了眼老婆,没说话,就又把目光挪到大酒店这边来。
陈秃子说:“大嫂,你得注意了,药铺里的那两个可是小姑娘,千万别让大哥犯错误。”
二梅说:“放心着呢,我还不知道他那两下子?一二三买单。”
大白胡说:“你家大哥还能一二三?你家的床不是天天晚上响吗?”
二梅说:“你上去也响。”
陈秃子瞅着大奎,说:“是嘛,原来你也是个孬货。”又说:“大嫂,这么说你家大奎就赶不上我了。”
二梅说:“赶不上也不用你的,自己家的东西有撇。”
陈秃子说:“死心眼儿了不是,还想不开,像咱们这样的,一天累得跟驴似的,就晚上这点儿乐子了,再乐呵不好就是白活。”
二梅说:“你自己乐吧,咱挺好。”
陈秃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总吃大葱吗?”
二梅说:“占便宜呗。”
陈秃子说:“小瞧我了不是?告诉你,壮阳,你们开饭店的应该懂得什么叫食补。告诉大哥多吃点儿。”
二梅说:“吃不起好的就别瞎说。吃大葱壮阳吗?我怎么看你越吃越佝偻。”
几个人就笑。
门开了,又进来两个人,是木匠,其中一个大个儿进来就喊:“老板娘,半斤酒,一个土豆丝儿,一个酸菜粉儿,再来一个炝花生米。”又说:“这天儿真他妈冷。喝点儿暖和暖和。”
二梅说:“挣钱不要命了,这天儿还出来。”
木匠说:“不想你了吗,哪天不来看看。”
二梅就抓起一个有些打卷儿了的满是油渍的算草本儿,边在上面写边喊着:“一个土豆丝儿,一个酸菜粉儿,一个炝花生米。”
大奎昕了,把目光从药铺里拔了回来,又折进了后厨,工夫不大,马勺又响了,一股炒土豆丝儿的味道飘了出来。二梅也跟着走了进去。
外面的雪早停了。风却还刮着,虽说不是很大,却很硬,“嗖嗖”的,看马路两旁那枯瘦的树枝就能知道风刮得强劲。
这时从药铺里走出一个女孩儿,在白色大褂的外面套了一件艳红色羽绒服大衣,很显眼,也很招摇地向小吃部跑来。门开了,带进一股风。同时也带进了一串儿带雪的脚印儿。女孩子个儿不高,穿的是高腰筒靴,擦得很亮,由于沾上了雪,进屋后很是轻柔地跺了跺脚,吃饭的人也很是自然地把目光投了过来,顿时觉着房间亮了好多。
二梅听到开门和跺脚声,又从后厨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个小碟和两双筷子,放到了刚进来的两个男人面前,说:“稍等,马上就好。”然后又对进来的女孩儿说:“姑娘,想吃些啥?”
女孩儿看了眼正在吃饭的人桌上的菜,问:“有饺子吗?给我来一斤,送到对过的药铺去。”
二梅问:“有酸菜馅儿的,韭菜馅儿的,萝卜馅儿的,三鲜馅儿的,想吃哪种?”
女孩儿说:“要三鲜馅儿的吧,多钱?”
二梅说:“十八。”
女孩儿递过来十八块钱,然后又走了出去,马路上就又多了一行脚印儿。
陈秃子说:“真他妈青春。”
大自赵说:“十年以后,跟我一个样儿。”
人多了,屋里就显暖了,气氛也好了,室内除了吃饭的声音,再就是后厨敲马勺的声音了。当二梅再次出来的时候,吃饭的大白赵说:“大哥的马勺敲得真响。”
陈秃子说:“可不,菜做得不咋样,马勺敲得杠响。”
大白赵说:“开个小饭店也挺好,风不吹日不晒的,还赚着自己吃,自己住。”
二梅说:“就是太忙活人了。”
大白赵说:“干啥都不容易。”
外面还有一些人在马路边上站着,不肯进来吃饭,他们一个个穿着臃肿破旧不同颜色的大衣,抱着肩胛,错着脚步站在马路的两侧,或是东张西望,或是叼着烟在那儿聊着什么,看上去很是无聊,也很是无奈。二梅站在门前看着,想,都啥时候了?赶紧进来吃饭得了。嘴上却说:“这雪一半天儿化不了。”
所有吃饭的人都不是很急,他们知道这样的天儿,这个时间是不会有什么人找他们干活的,他们要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一是吃饭,再是消磨时间,更重要的是躲避寒冷,暖暖身子,没有必要吃得太快。
叫大白赵的女人说:“今年我不打算回家了,大南大北的,跑一趟得花好几百呢,再说回家给这个拜年给那个拜年,老的老小的小,没个一两千的不够,回去一次就够咱们在这里忙活半年的。”
叫大白胡的男人放下筷子不再吃了。
大白赵又说:“你这个小饭店儿也得收拾收拾了,过年这几天我给你刮刮大白吧,见见新儿,亮堂
亮堂。”
二梅说:“刮啥?开春儿就拆迁了,昨天来人都告诉了,要扒,盖商场。这个地方呆不长了。”
陈秃子说:“扒了好,开个大一点儿的饭店。”
二梅苦笑着说:“凭这进项,搁啥开?守着你一辈子也别想开大饭店。”
马勺又响了,二梅又折进了厨房,同时端上两个菜和两壶烫热了的酒,放到了两个木匠面前,说:“烫热的。”
矮个子木匠说:“还是你心疼男人。烫热的好,喝热酒不犯病。”
大奎又出来了,同时端来一个炝花生米,递给二梅,说:“你去煮饺子吧。”
二梅把花生米放到木匠的桌上,又转身去煮饺子。
大奎四十多岁,人有些瘦,也有些驼背,他身上穿着件儿松松垮垮的有些发黄了的白色大褂,头上戴着个白色的帽子,那帽子虽说没有衣服那么黄,可也绝不能说像白的那么白。特别是靠帽沿儿的这一圈儿,简直就是由黑渐渐地变黄再变白了。他又一次来到门前,扯过一个塑料凳子坐下,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来,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开始抽。顿时屋内有了烟味儿,那烟味儿辣得强烈,没抽上几口,大白赵就咳嗽着说:“大哥抽的是什么烟?这么呛。”
大奎没回答,坐在那里,还是那么往外望着,继续抽烟。那夹烟的手粗粗大大的,指甲里面蓄满了黑色的泥垢,看上去就不是个干净人。他抽着抽着。突然身子哆嗦了一下,打了个喷嚏,很响,有些像炸雷,每个吃饭的人都奇怪地瞅了他一眼。
陈秃子说:“听大哥的声音,阳劲儿足,晚上肯定行。”
大白赵说:“你还没听他放屁呢,更响,跟炸二踢脚似的,咱们住隔壁,房灰土都震下来了,那真是响彻云霄啊。”
大奎听了,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嘴咧着,眼眯着,像是要哭,很难受的样子,整个面部扭曲了,还想打喷嚏,等了半天,没打出来,五官才缓慢地恢复了正常,只见他“哧哧”地擤了两下鼻涕,一把从头上将帽子撸下来,揩了揩手,又揩了揩鼻涕,戴上。
大自赵说:“大哥,轻点儿吧,还让不让咱吃饭了。”大奎不言语,继续抽烟,往外望。
正午,到了饭口儿的时间,马路边上站着的人越来越少了,整个街面也一下子空旷萧条了,只有大酒店招引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对过药铺门前的布幌子飘得不那么厉害了,像是累了,或是得了哮喘的病人刚刚吃完了药在那喘息着。大奎把目光从布幌上移下来,去瞅药铺。里面卖药的两个女孩儿在聊着什么,听不清,很专注很神秘的样子,还时不时地笑上一笑,往他这边瞧上一瞧,大奎就想这两个女孩儿是不是在说自己。于是就打量了一下自己,一切正常,没什么纰漏,便不去多想,又一次把目光甩向药铺的橱窗上。药铺橱窗的玻璃很大,贴着药品的宣传广告。有的是文字,有的是宣传画儿,文字是电脑打印的。红的黄的蓝的很好看,比他饭店这个牌子的字好看多了,虽说他看不出那是什么体,可他认识那字,左面的一排叫“货真价实”,右面的一排叫“质量可靠”,再就是那些宣传画儿了,有一个他认识,是总扮演皇上的那个叫张国立的演员。
大奎端详了一阵,最后把目光投到了离药铺门儿远一点的一个角落里,他很熟悉那个角落,是男人们尿尿的地方,很脏,地面上和四周的墙上有一片片尿渍,天一暖就散发着一股股臊味儿。在这儿打工的人都知道。这么大的市场没有厕所,这些人只能是逮哪哪尿了,他大奎也尿过,那是在晚上。药铺角落的一旁放着个灯箱,白天不用,只有晚上才点亮,放到路旁,做着一种夜间售药的广告。大奎对灯箱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灯箱上“性保健”那三个字。
昨天,就是昨天,大奎切菜时不小心把手弄破了,血当时就出来了,他立刻用餐巾纸将伤口捂住,来到药店买“创可贴”。在小女孩儿给拿药的时候,他无意间往柜台里瞅了那么一眼,发现一样东西,他的目光当时就僵在上面了,那不是男人的那个东西吗?他拢眼神细看,果然是那个东西,就那么大大咧咧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直挺挺地躺在柜台里。他当时有些紧张,也有些难为情,仿佛自己的那个东西被掏出来让人家看了。他的脸有些发热,咽了口唾沫,向四周扫了一眼,没人注意,身下便暗自使了使劲儿。觉着自己的那个东西还在,心里便骂:妈的,还不小呢。这是卖的吗?药店怎么能卖这种东西呢?他想着,看着,心里觉得好笑,这个东西做得还真挺像呢,粉嘟嘟的红。当女孩儿把“创可贴”给他拿过来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瞅着,遐想着,女孩儿看了他一眼,将药重重地往柜台上一放,说:“两块。”他当时吓了一跳,脸立刻就红了,他想,那时候他的脸一定比柜台里面的那个东西还红。
饺子熟了,二梅用小盆儿装着,怕凉了,又套上一个塑料袋儿,开门儿走出饭店给药铺送了过去。大奎看着自己女人的背影,觉着女人的腰实在是太粗了,对过卖药的两个女孩儿加起来也没她粗。
二梅送完饺子又转身回来了。这时大奎看的不是老婆的后背,而是完整的一张脸,老婆长着一张方脸,很白,个子不高,由于冬天穿得多,更显得笨拙,个子也就更显矮了,看着看着他笑了,想起了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开始没有落雪,建材市场门前那群跳舞的老太太跳完了舞,他们才关了门儿,也就九点多钟吧。
事实上,他的小店儿每天只有中午吃饭的人多,到了下午和晚上就很少有人光顾了,可他们不气馁,就是要等,守株待兔,万一有人来吃饭怎么办?
昨天晚上大奎没有收拾碗筷儿,也没有干什么别的,都是老婆二梅一个人干的,他的手破了,只干了一样活儿,把饭店的栅栏板儿放上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上床的时候那床依旧是“嘎”地叫了一下,他很讨厌这种声音,像是骨头裂了。那床是他用两块旧门板搭拼而成的,底下是用砖和四个小凳子支起来的,不是那么平整,不可能不响,身子躺在上面总是有些不踏实,有一种要瘫倒的恐惧。特别是偶尔干那事儿的时候,老婆叫,床也叫,他喜欢老婆的叫声,不喜欢床的叫声,这两种声音就像美声和通俗合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
上床前大奎犹豫了一会儿,他看着床,站在那里发呆。从前大奎是很喜欢上床的,特别是在乡下的时候,喜欢和老婆搂在一起身贴身的感觉,然后两个人再在一起“炒菜”,翻来覆去颠鸾倒凤的,那个兴奋那个舒坦就甭提了。可自从到了城里他就不行了,侍候不上去了,那“菜”怎么也炒不出味道了,或者半生不熟,或者干脆就是生的,每一次都弄得他像个败军之将,不欢而散。二梅虽不说什么,偶尔也是敲碗儿给盆儿听,没从前那种欢畅劲儿了。
虽说大奎的“活儿”不行了,梦却好了起来。在乡下的时候他是很少做梦的,那会儿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二梅身上了,不仅把二梅弄得神魂颠倒,把自己也弄了个神魂颠倒,每天晚上干完活儿就“呼呼”大睡,没梦可做,和其他乡下人一样,一睡到天亮,没有大的奢望和负担。可自从到了城里,身子懒了,大脑却活跃了起来,总做梦:什么好房子,好衣服,好车,好环境,小饭店也变成了大酒店,仿佛一夜间成了阔佬,成了人上之人了。每次做完梦,早上起来,大奎都
要对老婆讲,听得二梅那个兴奋,那个乐,别提多高兴了,动不动还要亲上大奎一口,说:“真要是像做梦那样就好了。”
大奎勉勉强强地上了床,躺在那儿抽烟,想着什么。这时二梅也忙完了,二梅洗了头,她每天晚上都要洗一次头,嫌油烟味儿太大了,上床的时候头发湿淋淋的。屋子里很凉,两个人开始谁都没有脱衣服,太冷了,得相互捂一捂,然后才能脱光。大奎搂着老婆湿漉漉的脑袋,抽着烟,看着有些发黑的棚顶,想白天在药铺里看到的那个红红的东西。
屋内静下来了,终于静下来了,他们忙了一天,太阳从东方转到了西方,又该睡觉了。大奎在想,怎么又到晚上了呢?怎么又要睡觉了呢?说心里话,这两年,特别是最近这半年,他有些害怕过晚上了,甚至有些怕天黑,当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担心,一种忐忑,一种惆怅,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特别是这张床,只要一见到这张床就像见到了曾经打过败仗的战场那么让他耿耿于怀。见到了自己的女人就像在战场上见到了攻不克的堡垒那么打怵,有一种短兵相接,而且屡战屡败的恐惧。大奎想着,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二梅猛地坐起来,说:“钱还没数呢。”
大奎说:“明天再说吧。”
二梅说:“不行,我得数数,不数心里没底儿,不踏实。”于是,趿拉着鞋,带着湿漉漉的脑袋下床,到厨房取来一个破饭盒子,“哗”一下倒在床上,开始数钱。
这是他们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候。
二梅笑着说:“你是不是有些怕我?”
大奎装糊涂说:“怕你?谁怕你?怕你啥?”
二梅说:“还不怕?我发现我一上床你就紧张,底下不硬,上面倒硬了。”一句话把大奎说得脸通红。
二梅开始归弄钱,钱的面额不是很大,十元的五元的一元的,还有好多的钢铺儿,她归弄着,大奎看着,他不仅看钱,还看自己的女人。在他的眼里老婆总是那么美,虽说比先前蠢一些,可感觉更好了,有肉儿,有摸头儿,碰哪儿都暄乎乎的了,特别是那两个大咂儿,像两个刚出锅的大馒头,热气腾腾的,看上去就想咬一口,于是就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女人说:“干吗?数钱呢。”
二梅的钱归弄得很仔细,一毛一毛一块一块地捋着,钢鏰儿放在破饭盒里,十元的放在床上用脚踩着,五元的放在枕角旁压着,一元的放在盒盖儿上,有的钱很皱,很破,她就用手捋,用指甲抠,直到捋平了,捋坦了,捋顺了,便开始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数完了,大奎问:“多少?”
二梅说:“比昨天多三块。”
大奎就在那儿翻着白眼儿,说:“一天多三块,十天多三十,一百天多三百,一年就是一千多,在家种地干一年也挣不了一千块钱。”
二梅说:“没你那么算账的,还能天天多呀,你咋不算算你赔的时候。”又说:“明天又要来收税了,国税地税卫生费综合治理费,划拉一起好几百呢,什么时候把这些费都免了,咱们就好过了。”
大奎说:“做梦吧你。你知道城里人指啥活着,那些当官儿的工资从哪儿出,包括绿化,市政建设全指这些税呢。不收税他们喝西北风啊。”
二梅说:“真是的,咱挣钱也不容易啊,国家咋这样呢?”
大奎说:“哪个国家都这样,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梅说:“咱也没享受着啊?”
大奎说:“咋没享受着,你看这马路,公园儿,草坪,还有那些大树,不都是咱的钱吗?”
二梅说:“那他们咋不给咱乡下弄一弄呢。”
大奎说:“弄完城里就该弄乡下了。”
说着,二梅将破饭盒里的硬币拿起来掂了掂,晃了晃,那些硬币就在饭盒里相互拥抱着,亲吻着,发出“哗哗”的笑声。
大奎说:“睡吧,别晃了,那几个破钱儿晃啥,困了。”
说是困了,可当女人再次上床的时候,就不困了。这一次二梅脱光了身子,大奎也脱光了身子,两个肉身贴到了一起。开始有些凉,其实男人的身子是热的,女人的身子是凉的,二梅把凉的腿向大奎那温热的两腿间插去,取暖,大奎不让插,说:“太凉了。”二梅也不说话,硬是插了进去,不仅把腿插了进去,整个身子也趴了上来,肉贴肉,脸儿对脸儿,心对心那么躺着。于是,大奎的两腿之间就多了两条腿,身上就多了个肉乎乎的身子,这一下不仅他的腿跟着凉了,肚皮也跟着凉了,只是他没再说话,他知道说了也没用,老婆是在跟他撒娇呢,大奎喜欢老婆跟他撒娇,这样才叫夫妻,才叫两口子。
二梅在大奎的身上趴着,双手摸着大奎的额头,大奎的一只手搂着二梅的腰,另一只手摸着她的一个肉乎乎的乳房,捏着,乳房就像个皮球,时扁时圆。突然二梅说:“轻点儿。”又问:“你的手咋样?”
大奎不说话。
二梅又说:“炒菜又不是没肉了,干吗切手?”说着,吻了下大奎的脸,又说:“你的胡子都扎人了。”
大奎说:“你不喜欢我扎你吗?”
二梅说:“晚上喜欢,白天不喜欢,看上去埋汰。”说着又亲了一下。
男人的脸很刚毅,二梅喜欢这样的脸。她摸着说:“你知道我喜欢你啥吗?我喜欢你白天像个爷们儿,晚上像个孩子。”
大奎也亲了下女人。
二梅把手伸到了大奎的身下,问:“今天怎么样?都好几天了。”
大奎没说什么,想了想,将身子从女人的身下抽出来,翻上去。翻的时候有些无奈,懒洋洋的。像嘎巴锅的鱼,很是勉强地翻了个个儿。
床又“嘎”地响了一下。
二梅说:“等有了钱,买新房了,一定买张好床。”
大奎说:“要大的,那种‘席梦思双人床,再买两床好被。鸭绒的,一定很暖和。”
二梅说:“买那么好的干什么?你也不好用。”
大奎不说话,在努力着,二梅也闭上了眼,像一个暂时停在空中的飞行物,那么静静地等待着对接。
天一黑,空气就显得更凉了,整个房间的空气冻凝了一般地死气。为了省钱,他们舍不得烧煤,只插了个电褥子,温度还没有上来。二梅扯住被头,盖住了男人的后背,怕冻着。突然,二梅“啊”地一声轻轻地叫了那么一下,对接上了,大奎粗着气说:“要说人类就是聪明,你说在宇宙,在空中,那么大的空中飞船说对接就对接了。”
二梅皱着眉,脸向上微微地仰着,半吟半叫地说:“这么说你就是个笨蛋。这么近都对接不上。”
大奎说:“我不是对不上,是对上了锁不住。”
二梅软绵绵地打了一下男人的后背,说:“狗啊。”
外面不知有没有风,反正被窝里这时是有风了,那风很急,也很硬,女人像一把号似的被男人“吹”响了。
床也响了,那床的“吱嘎”声,伴随着两个对接上的“飞行物”,绕着地球飞行,他们遨游在整个太空,奏响了人类最原始的兴奋之音。只是在女人刚要嘹亮的时候,那个吹号的号手不行了,一下子没了气力,滑音儿了,萎靡了。于是,那号声也跟着软了下来,二梅看着伏在自己身上的男人,知道是又不行了,也没有抱怨,用手摸抚着男人的后背,说:“歇歇吧,可能是白天太累了。”
大奎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眼泪却掉了下来。
屋内很静,能听到心脏的跳动声,也能听到眼泪的流淌。
二梅安抚着男人,说:“看你,没事儿。”
大奎不说话,二梅用舌头把男人的泪舔了,说:“好了好了。我生气了啊。”
大奎亲了下女人,说:“我真的不行了。”
二梅说:“不行就不行。”
大奎说:“那怎么行?咱们就这点儿乐子了,这点儿乐子再没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女人也不说话了。
外面大酒店依旧是人来人往,那霓虹灯的闪耀透过小饭店窗子的缝隙挤了进来,把屋子也弄亮了。
大奎摆弄着二梅的头发说:“我跟你商量点儿事儿,你说你不生气。”
二梅问:“什么事儿我生气?”
大奎说:“你说你不生气。”
二梅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了?我不生气,你说吧。”
大奎刚想说,又咽了下去。
二梅急着用手拍了一下他的屁股,说:“说呀,不会是让我找别的男人吧。”
大奎说:“你胡说些啥。不说了,怕你生气。我累了,睡吧。”便翻下身去。
大奎拱到二梅的怀里,这时女人的身子是温热的,他猫儿似的很乖巧地躺在二梅的臂弯里,说:“不好意思。”
二梅说:“没事儿,我都习惯了,都不咋想了。”
大奎说:“我一定是病了。”
二梅说:“不检查过了吗,说你没病。”
大奎说:“那怎么不行了?”
二梅说:“累的,一定是累的。”
大奎说:“你说在乡下的家里咋还行,到城里反倒不行了。”
二梅说:“我怎么知道。”
屋里很静,好像有老鼠在厨房的什么地方啃吃着什么,发出了一阵阵的碎响。
二梅抓起身边的一个小笤帚,向厨房扔去,那碎响立刻就没了。
大奎将二梅搂过来,用手摸着她那软软的身子,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二梅高兴说:“真的,讲啥?”
大奎想了想说:“算了,还是想想咱们搬家的事吧。”
大奎依旧坐在门前,这时吃饭的人已经走光了,饭店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两个人。寂寞又一下子袭了上来。
二梅走上来,说:“我怎么觉着吃饭的人越来越少。”
大奎说:“吃不起呗。”
二梅说:“你看那大酒店里总是那么多的人。”
大奎不语。
二梅又说:“咱们吃点儿什么吧。”
大奎说:“你吃吧,我不饿。”
二梅说:“怎么也得吃饭哪?你早上就没吃。”
大奎说:“我真的不饿。”
二梅问:“别想那么多了,咱也不是第一次搬家了,到时候再说吧。实在呆不下去了咱还回家。”
大奎说:“地都没了,回家干吗?”
二梅说:“就怪那个村长,把地都给卖了。瞎了那块地了,我爷爷小的时候就有那块地,风水宝地,哪年打粮都比别人家的多。”又说:“那我也不吃了。”就挨着男人坐在了一旁,往外面看。
正是下午时分,外面马路上的行人又多了,路两旁又站了好多打短工的人。
二梅看着说:“咱刚搬来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小平房,这才几天就盖了这么多楼。”又问:“你昨天晚上想跟我说啥?”
大奎看了眼对过那写有性保健的灯箱,说:“没想说啥。”
二梅说:“不对,你一定有话跟我说。不许你胡思乱想,只要你对我好,我什么都能忍。”又问:“你今天总瞅药铺干吗?”
大奎真的又把目光移到了对面的药铺,药铺的两个女孩儿在吃饺子。
二梅问:“你说,大白赵能出去找别的男人吗?”
大奎说:“谁知道。”
男人不说话了,女人也不说话了。
挺了一会儿,大奎突然问:“你去药店看过别的什么东西吗?”
二梅问:“啥东西?尽是药,有啥好看的?”
大奎瞅了眼女人,女人的目光很纯粹。大奎又不说话了,二梅把头靠到了男人的肩上,说:“你说咱俩以后怎么办?一想到搬家我就打怵,搬多少回了,还往哪儿搬?”
大奎不说话,摸出烟来抽。
二梅又问:“你昨天晚上到底想说啥?”
大奎想了想说:“没啥,我是在逗你玩儿呢。”
这时,从对过的大酒店里出来个女人。
二梅看着说:“你说那些人总去大酒店吃饭,哪儿那么多的钱?”
大奎不说话,吐出一口烟,一个大大的烟圈儿,从门缝里挤了出去。
二梅说:“你看她穿得多好看。那一件貂皮大衣得好几万吧?我有钱可不舍得穿在身上。城里人真是有钱,又是小车儿,又是别墅的。”
大奎说:“也不都那样儿,在咱门前站着的也有不少是城里人。”
整个下午没有人吃饭,大奎和二梅就这么坐在门前,看着,想着,说着,抽着烟。快到天黑的时候,二梅说:“晚上早点关门儿,陪我出去走走吧,总在这里呆着,我都要憋屈死了。”
大奎说:“咱们跟那些老太太跳舞吧。”
二梅说:“我可不去跳舞,男男女女的扯来扯去,丢人。你陪我到大街上转转就行。”
天黑了,大奎和二梅破例提前关了店门。两个人来到街上,他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慢慢地走着。
风停了,空气也不是那么冷了,二梅说:“城里下完雪空气真好。”
大奎说:“那也没有咱们乡下的空气好。”
两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走了,附近的路他们都很熟,米镇不是很大,一共两条主干线,南北一条,东西一条,再就是新修的那条环路了。
二梅走着说:“我想孩子了。”
大奎说:“娘的病也不知好了没有?”
二梅看着天,说:“你看那天上的星星多亮,跟萤火虫似的。”
大奎说:“傻瓜,哪有这么多的萤火虫。”
他们往前走,星星也跟着往前走。
路灯不是很亮,照在雪地上有些发黄,两个人走着,影子被路灯的光扯来扯去,在他们的脚下晃动着,时大时小,时隐时现。大奎把二梅的手拉过来,放到自己的大衣兜里,紧握着。
二梅说:“咱俩刚认识的时候,我就喜欢你拉着我的手。”
大奎说:“那时候不敢,怕你不让。”
二梅说:“那你怎么敢亲我?”
大奎说:“憋不住了。”
二梅用力地握了握男人的手,说:“今年回家咱俩好好给村里人拜个年。多给他们买些城里的东西,让他们看看咱在城里混得不错。”
前面是个教堂,教堂很高,隐隐约约有个十字架支在空中,打远望去,整个夜空像一把大伞,撑在十字架的上面。
大奎说:“咱第一次来城里开饭店就在这儿。”
二梅说:“有个疯子总去要饭。说他老婆跟别人跑了。”
大奎说:“你跑我也能疯。”
二梅说:“有你这句话,我也不能跑。”两个人的手握得更紧了。
二梅又说:“明天我信教吧。”
大奎说:“为啥?”
二梅说:“听说人信教了,心静,心静了晚上就不想那事儿了。”
大奎说:“谁说的?胡说八道。”
二梅用身子撞了一下大奎,说:“我骗你呢。”
马路是平整的,宽阔的,积着雪,满眼的白,在路灯的照射下人踩上去有些像踩在一条冻僵了的哈达上。经过一天的人行和车轧,雪已经牢牢地板结在地面上了,像块白铁。他们走着,脚下很滑。
前面是一片小区。
二梅说:“咱俩开的第三个饭店是在这儿。那个房子没了,变草坪了。”
大奎说:“应该是琴行的那个位置。”
二梅说:“不对,应该是卖家电的那个位置。”
大奎说:“开了四个饭店,这个位置最好,朝阳,
吃饭的人也多。主要是守着公共汽车站。”
二梅说:“好景不长。”又说:“咱可以回乡下开饭店。”
大奎说:“现在那儿的饭店比吃饭的还多。”
两个人又不说话了,都很无奈地吸了一口凉气。
路过一个邮局,又路过一个律师事务所,前面是市府广场。这是米镇唯一的一个广场,是刚刚铺建的,正在往上安装饰灯,灯没有安完,有的亮了,有的还没有亮,看上去不舒服,像一双双眼睛,有的瞎了,有的没瞎。
大奎说:“这些灯都安完了一定很好看。”
二梅说:“这得多少电?这么多灯泡,城里人真能祸祸。”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数灯泡。
数着数着,大奎说:“这叫槐花儿灯,那一个电柱上120个灯泡。”
二梅说:“这么多?足有二十个电柱吧。”
大奎说:“还没算马路两侧的呢。”
二梅数着数着,不数了,说:“妈呀,数都数不过来。”
说着,两个人来到了广场中间。
二梅说:“这么大的广场,得有十亩地。”
大奎说:“多少?二十亩也不给你。”
二梅说:“这么大块地在乡下能打多少粮食!”
大奎没说话,他摸着一个电柱,说:“这么高,都是铁的,得老钱了。”
二梅说:“还是城里有钱。”
广场的西侧是火车站,时而有火车的鸣笛声,也有上下火车的人从广场匆匆走过。
两个人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广场的东侧是市政府,在市政府的对面是个叫“金色港湾”的大型歌舞厅,从里面传出一阵阵男男女女的歌声。
大奎和二梅走过去,脸一下子被霓虹灯映红了。
二梅说:“真好看。”
大奎兴奋地说:“咱们去歌厅唱歌吧,从来没去过,咱也享受享受。”
二梅说:“算了,看看就行了,还唱歌?没听人家说一瓶啤酒二十呢,一个果盘儿就一百多。”
大奎说:“那咱俩就坐在门前听听吧。”
二梅说:“行,我还真没听过歌厅里唱的歌是啥味儿呢。”
于是,他们走上台阶,拣了个干净的位置坐下,手牵着手,身贴着身,聚精会神地听着。
里面有歌声传来:
我的家乡并不美。
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枯的小河,
依恋在小村的周围……
听着,二梅说:“我想家了。”
大奎说:“要是没有孩子和我娘在那里,我一辈子都不想回去。”
眼前是个很大的停车场,雪已经被除净了,地面很干净,也很平坦,停着一辆辆豪华轿车。
大奎说:“将来咱挣着钱了,也买一辆车,我带你兜风。我这辈子就喜欢车。”
二梅叹了口气说:“买三轮车吧。”
大奎说:“市内的房越来越贵,租不起。”
二梅说:“实在不行就远一点儿,城边儿的房能便宜。”
大奎说:“那不又回乡下了?”
二梅说:“那怎么办?回不去,又留不下。”
大奎又无话可说了。
二梅说:“明天咱买个小电视吧,不能总上大白赵家看了,大白胡有点儿嫌。”
大奎说:“好几百呢。”
二梅说:“晚上没事儿干。真是难熬。”
大奎说:“过年回家把爹的半导体拿来听吧。”
二梅说:“爹听啥?”
大奎说:“他耳背,早听不清了。”
二梅问:“那他天天拎着干啥?”
大奎说:“那是他当队长的时候在县里得的奖。”
二梅说:“那咱可不能要,爹一定稀罕。”
这时身后有脚步声传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坐在这里?”
大奎和二梅吓了一跳,回头看,见一个年轻的保安威风凛凛地站在身后,大奎刚想说听听唱歌儿,二梅就拉着大奎的手,说:“咱们还是走吧。”
大奎来到台阶下,又看了眼保安,还想说什么,二梅又使劲拉了他一下,离开了。
两个人离开了歌厅的门前,继续往前走,大奎说:“有什么牛的,听听都不行。”
二梅说:“咱是坐在人家的大门口了。”
大奎说:“门口咋了?又不是屋里。”
二梅说:“你怎么知道车停在你家门前你不高兴,那不是碍眼挡路吗?再看看咱这穿戴。”
大奎骂了一句:“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等老子有了钱天天来玩儿。”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在走到一个拐弯处的时候,突然看见了大白赵跟一个男人从一家小型录像厅走出来。
二梅看见了忙说:“你看大白赵。”
大奎说:“小点声。”又说:“咱也去看录像吧,通宵的,有武打,什么都有。”
二梅说:“看那干啥?两块钱一张票呢。”
大奎又没话可说了。
二梅说:“咱们还是回去吧,我有些冷了。”
大奎说:“回去给你讲故事吧。”
二梅说:“你给我讲半年了,就那两个故事,翻过来倒过去的,我都听腻了。”
大奎说:“那咋办?”
二梅也不知咋办。
大奎又说:“我总觉着对不起你。”
二梅问:“啥对不起?”
大奎说:“晚上。”
二梅说:“没事儿,听老人说年龄大一大就不想了。就年轻时这几年,忍一忍就过去了。”
两个人走在冰冷的路面上,相互依偎着,像一对儿新婚恋人,身后留下了大型歌舞厅的娱乐声和录像厅里那男欢女爱之声。
二梅说:“大城市玩儿的地方真多,比乡下热闹。”
大奎听了,叹了一口气。
前面就是自己的家了,二梅看了看天,突然说:“今天没有月亮,明天是腊月初一,我的生日,你送我个礼物吧。嫁给你这么多年了,过生日你从来没送过我什么。”
大奎问:“你喜欢啥?我给你买。”
二梅想了想说:“算了,还得花钱,吃两个鸡蛋滚滚运就行了。”想了想,又说:“还是煮一碗长寿面吧,省两个鸡蛋,能多卖好几块呢。”
两个人说着,来到了家门前。这时药铺旁边写有“性保健”的灯箱亮了,那亮白的光色映着路面白白的积雪,同时把大奎的心也照亮了,大奎说:“明天我给你买件礼物你一定喜欢。”
二梅高兴地问:“真的?买啥?”
大奎说:“明天买给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