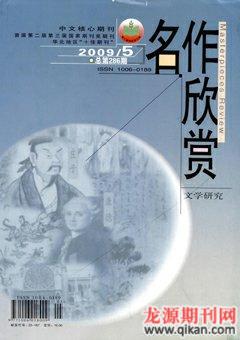颤动的都市风景线
关键词: 新感觉派 施蛰存 都市风景 审美追求
摘 要:施蛰存是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对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刻的描绘,注重捕捉独特的人生感受,既表现灰色现实中都市人生存的心理困惑,又极力挖掘人们善良美好的秉性。施蛰存擅长用心理分析的手法解读人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体现出作家执著而独特的审美追求。
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他们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仅把眼光投向普通市民的悲欢离合,表现繁华喧闹中都市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对都市人的深层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把人们置于深度心理学的透视镜下,揭示出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人们精神的寂寞、疲倦和堕落的心理。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功尝试标志着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渗透,说明文学开始走向内心、回归自我,深入到作家的灵魂底层,进行深刻强烈的自我体验,从而获得创作生命的全面展开。作家在创作时,既与笔下的人物有着相同的心态,又超越他们,以神圣的眼光审视着人物灵魂的苦与乐、爱与恨,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新感觉派的创作填补了人生派作家、左翼作家所忽略的许多空白点,也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一道奇妙而另类的景致。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小说在表现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时,注重捕捉独特的人生感受,表现人们的生存困惑和心理压抑,但同时又极力挖掘人们善良美好的一面。小说擅长用心理分析的手法解读人性,追求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现代小说在表现领域和表现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开拓,对新文学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
一、在生存困惑中展现美好的心灵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中,大多写都市人的生存困境。那些在喧嚣的都市中被紧张而紊乱的节奏所拖垮的主人公,对现实世界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感,那种病态的情感,扭曲的心灵,与性的欲念相掺杂,迫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如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强装笑颜的“特吕姑娘”(《特吕姑娘》);生活困顿,小两口反目,深夜出去拉车而顿生抢劫之心的四喜子(《四喜子的生意》);有表面上尊敬患病的妻子、内心里等待着情妇到来的伪君子(《港内小景》);有对丈夫吝啬,对自己“会用了许多钱”,背着丈夫同情人栖息于公园的“蝴蝶夫人”(《蝴蝶夫人》);有失望于婚后生活的单调,寻求着新的浪漫恋情的“他”(《散步》)……最典型的是《魔道》,小说的全部情节都是由幻觉和梦幻组成的。小说中的黑衣妇人象征着充满灾难和敌意的无法摆脱的生活,象征着生活中的恐怖和失望,它时时刻刻地纠缠在孤独者的灵魂内,使人感到无处不在的威胁,而又始终摆脱不掉。所以,施蛰存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一样关注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压抑以及病态的特征。
但施蛰存为了“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就只得“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生活中虽然充满了痛苦和压抑,但施蛰存在描写都市人的生存困境时,极力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美满的爱情是人生的真谛。有了它,一切的不幸、不平、不快都会烟消云散,人类就靠着它支撑到了今天。但其中也有苦涩的恋情、有相思的痛苦。因此,能否把握好这一常写常新的古老主题就成了衡量作家身手高低的不成文的标志。施蛰存的成功在于既写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又把镜头推向生活中的美好、善良,以“秀色、动人的文字”(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写下了一篇篇一唱三叹、回味无穷的艺术珍品。它们是人间至情的自然流露,读着这些作品,我们就像饮着甘洌的美酒,陶醉在纤尘不染的别样天地。施蛰存的《阿秀》最为出色:阿秀为反抗命运的不公平,为争得“把人当人看待”的平等权利,两次从可恶的丈夫身边逃走。这种抗争精神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发现,人性的复归,显得非常珍贵。《莼羹》、《妻之生辰》虽然写的是家庭生活的日常琐事,但夫妻真情却力透纸背,写得缠绵悱恻、荡气回肠。作家洞察了人生的底蕴,以体验领会的方式展示了人性的本质,达到了与鲁迅《伤逝》一样的感情深度和纯度。
施蛰存最唯美的心理分析小说是《梅雨之夕》,这篇小说写一位带着雨具的男子在街头邂逅一个躲雨的姑娘,主动送她回家时一路上的心理变化。这是一段没有结局的萍水相逢,小说却详尽地表现了主人公如何被潜意识驱使去接近年轻美貌的女性,而又惴惴不安的心理状态。如由身旁姑娘而引起对自己初恋的怀念,害怕遇见熟人的惶恐,在惶恐中感到的秘密的愉悦和快慰以及雨停姑娘告别时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小说把主人公多角度的意识流动与微妙心理的瞬间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却没有任何暧昧和猥亵的感觉。作者把这种性心理活动写得细腻生动,富有层次而饶有兴味,使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阅读愉悦感。
二、用心理分析的手法解读人性
施蛰存是最早把弗洛伊德带入中国现代小说的人。他年轻时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又受到了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小说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把这些理论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写出了理性背后的非理性世界,意识领域背后的无意识、潜意识领域,所以被誉为“中国现代派鼻祖”。他的小说在分析人物心理时,往往侧重于表现人物的深层意识,尤其是性意识。《将军底头》中四篇小说,就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古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石秀》写石秀对结义兄弟杨雄之妻潘巧云的迷恋,表现那种熊熊燃烧的饥渴和情欲与对兄长的情义之间的冲突;《将军底头》表现作为大塘武官的吐蕃武士后裔花惊定,对一位汉族姑娘的压抑不住的情欲与种族意识的冲突;《鸠摩罗什》揭示大德僧人鸠摩罗什对淫荡女子梦娇娘的迷恋与宗教虔诚之间的冲突……这些小说都把潜意识与意识的冲突作为小说结构的基础。甚至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如石秀对潘巧云“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并且欣赏她的裸体上的鲜血的美艳;又如花惊定将军被汉族姑娘的美色所魅惑,情火中烧,产生了对姑娘肆意侮辱的幻觉描写,都显示出浓厚的弗洛伊德的色彩与独特的审美视角。
《石秀》最突出表现了这些特点。小说开头就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作家开始深入到石秀的“冰上”底层进行探幽烛微、层层剥离,使一个真实的石秀初次展现在我们眼前:陌生的环境使他思绪万千,由自身想到与杨雄及梁山英雄的结识,由杨雄的平常的相貌又想到杨妻的光彩照人的肌肤丽质。因为他还从未同女人接触过,所以一股从来没有过的热情从内心深处涌起,这是石秀性意识的萌芽。作家接着用特写镜头突出了潘巧云那双美脚对石秀的刺激,说明石秀的性心理不是凭空产生的。“脚”这个特殊刺激物通过眼睛进入石秀的大脑就使他产生了难以遏制的性的渴望。可是,他转而一想:我怎能爱义兄的妻子呢?道德理性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力量:把强烈的情欲压抑下去。形而上的精神主体战胜了形而下的肉体欲望。这是作家对人物二重人格的第一次亮相。
紧接着,作家安排了潘巧云对石秀的两次引诱和石秀的心理反应。他妒恨她的天姿国色是因为不得与其亲近;他又感到欣慰是因为住在她家,还有得到她的希望。这样,一种恐惧与罪恶的感情笼罩在他心头。爱欲与道德又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外表上,他抵挡住潘巧云的诱惑,可在下意识里他却失败了:他深深地渴望着她的肉体。他生活在煎熬之中。这是理性精神对情欲的第二次胜利。由于石秀的拒绝,潘对他冷而淡之,投向僧人的怀抱。石秀发现后,异常痛苦。烦闷之下,来到妓院。这个情节似乎有点不符合石秀的性格逻辑,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正是潘巧云的美姿唤醒了他的性意识,无可抗拒的“力比多”终于使他放弃了以前那种清苦的生活。这种自然情欲的满足,实在无可厚非。那么如何看待石秀对于妓女的爱欲,尤其是在她割破指头时,石秀看着鲜红的血液往外涌时产生的那种疯狂的满足心理呢?这表面上不近情理、带有病态的色彩,但人的潜意识里还是存在着那种猎奇的心态的,这是人类野蛮性格的遗留。当理性放松警惕时,它就会跳出来捉弄人的文明性,只是自觉的人格意识把它压抑下去而不被人觉察或不敢正视它的存在罢了。作家的这种描绘正是他的不同寻常之处。
小说进展到这里,石秀的心理已基本披露,但为了更好地表现石秀的真实性,作家还设置了下面三个情节:石秀告诉杨雄潘背叛了他;石秀被误解,亲手杀死奸夫;石秀怂恿杨杀潘。这些情节伴随着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使我们感到:推动石秀行动的动力,有他对朋友的忠义,更为重要的确是“力比多”的强大推动力。他疯狂地渴望着得到潘巧云的身心,却得不到;而一个比他丑陋的和尚却占有着她。因此,他要报复,要看着她的肉体裸露在自己面前,要看着美女的鲜血的外泄以慰藉他那颗燃烧着欲火的心。作者用惊世骇俗的笔触写道,每剜一刀,石秀看见那美丽的肢体泛着最后的桃红色,都感到一阵满足的愉快。这是一种奇特的恋情——热切、疯狂带有一点病态;“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这就是作家创造出的“这一个”石秀的独特心理,其他方式恐怕会减弱他的真实性、审美性。就这样作家完成了石秀心理矛盾发展的全过程。用现代派的手法去演绎一个古老的故事,从生理学而非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人物的行为,小说把《水浒传》中的伦理范本变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病案。这无疑为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三、现代表现手法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施蛰存是一个有着独特审美追求和艺术敏感的作家,他的心理分析小说接受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虽然写人的感觉、幻觉,但小说故事情节又非常分明,不颠三倒四地打乱时间的顺序,而是有一条清晰的情节梗概,所以他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结构特点。如《春阳》中,婵阿姨从银行取钱出来到三友实业社,再到饭店吃饭,最后又回到银行,事件的发展过程清楚明白。《梅雨之夕》中,“我”从下班到遇雨,然后遇到躲雨的少女,一直送她回家,情节进展也明明白白。他的小说都有清晰的时间顺序,并顺着这时间顺序展开人物任意的心理流动,而任意的意识流动又往往围绕着某一个核心意念。比如《春阳》中婵阿姨的意识流动围绕着对家庭生活、对异性的渴望;《梅雨之夕》中则围绕着对异性美的爱慕及隐伏着占有欲。他的小说中往往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情节线索,另一条是沿着核心意念向前运行的意识流轨迹,整个小说就呈现出意识在现实情节与核心意念之间向前平行流动的状态。这种独特的小说结构使人感到新颖别致,又容易接受。
施蛰存小说的叙述角度也很独特。作者与故事的关系,他选择什么身份充当故事叙述人——这就是小说的视点,通常可分为内视点与外视点。外视点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作者是全知全能的,这是一种传统的叙述方式。内视点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显得真实、可信,读者更容易接受。施蛰存汲取西方现代主义营养,叙述角度突出了内视点,作家退出小说,让人物直接倾诉衷肠,直逼人物的内心世界,写活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深层心理结构。《梅雨之夕》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只是写“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躲雨的姑娘并主动送她回家时一路上的意识流动。“我”先把她作为美来欣赏,又仿佛觉得她是自己少年时代的女朋友;后来,雨停了,姑娘向“我”道别,“我”竟埋怨老天为何不多下半小时的雨。最后,“我”回到家里,怅然若失,竟连自己的妻子似乎都不认识了。把一小时的散步写得如此曲折动人、扑朔迷离是与作者全部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有关的,这样就有利于让人物心理活动全面展开,自由流动,可伸可缩,达到了通过剖析人物心理再现人物的审美目的。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人性深度和审美形式两方面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局面,推进了小说创作现代化的进程。形成这种审美风格的原因是与他的气质、环境及所受教育分不开的。因其“纤细、机敏、有涌流不尽的才情”(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并且“生活是很平静和顺,没有突兀的激变”,所以他的“创作也如静水一般,很从容自然,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完成了人生的诗化给世界带来的美。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新平,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2]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昭明出版社,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