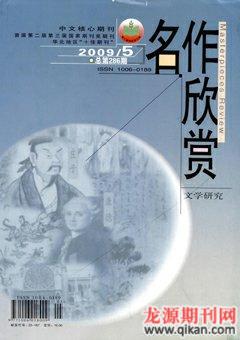自然人性的复苏与回归
沈从文的《丈夫》于1930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4号,先后被译成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希伯来文等,在海外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出版或刊载。《丈夫》广泛流传,其魅力何在?显然,
我们不能仅只把它看作是对“农村社会精神上的溃烂”①现象的揭示。我认为,作品的重心在于,作者用优美细腻的笔墨,倾力写出城乡冲突中乡间男女自然人性的复苏与回归。
对于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来说,“享有心理健康和尊严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②。他们在大自然中,与那“宝塔烟雨红桃好景致”融为一体,安然享受着健康与尊严。就算做妻子的去城里当妓女,在乡间男子们看来,也“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是“极其平常的事”。但在城乡冲突背景中,事情却不再如此简单,乡下人的健康和尊严在城市中被漠视,甚至遭到了蹂躏与践踏。尽管丈夫们都认为事情极其平常,尽管他们忠厚和平,沈从文还是想把丈夫心中这种似有若无的失落揭示出来,凸现城市加给乡村的伤害。他选择了丈夫去妓船上看望妻子的时节细加描绘。在丈夫看来,女人“自然已完全不同了”:“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这么多的修饰,对乡村的素朴是掩压,或者也是抛弃。而深一层的改变随之也被发现了:“女人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畏缩神气了。”又忽然夺去丈夫的短烟管,塞给他哈德门香烟。这里固然不乏女人对丈夫爱的表示,但也似乎意味着对“哈德门”所代表的城市享受的追求,以及对“短烟管”所象征的乡土生活的不屑。香烟对丈夫来说,是“有新鲜趣味”的;而女人也许享受到的“新鲜趣味”物事更多些。可正是这些物事,改变了她,祛除着她身上那份乡野间的素朴清新。
就像文本开始的介绍一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与乡村离远”了。一旦她们“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很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看似静止般的恒常之中,一种“慢慢的”“谁也不去注意”的“毁”和“变”就这样发生着。沈从文的感慨是深刻的。细致行文中注入的这份深刻历史感,在乡村为后景、市镇作近景、妓船为前景的布局中缓缓地流,那份沉重,也只有在对乡村的深情回望中,才可深入体会。
作者还是想进一步呈现这“毁”和“变”给自然人性带来的刺激和伤害。这也是故事的逻辑必然:质朴憨厚的丈夫因思念妻子从乡下赶来,却在船上无所措手;妻子的变化对于外人来说或者无足轻重,可对于丈夫,却引起一次次深深的惊讶;也许“吃惊也仍然是暂时的事”,但面对晚上妻子伺候船主或商人的工作,怎一个“吃惊”了得?他感觉到“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这种伤感很模糊,也较为清浅,女人抽空来塞他口中一小片糖,他也就原谅了她,“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那淡淡的寂寞会飘散在河中,消失在梦中。
也许老七和她的汉子是其中的例外,但沈从文偏要把他们写出来,使寂寞成长,使伤痛凸显,以此促成自然人性的复苏与回归。
水保巡查船只,发现了留守在船上、才从乡下来看望妻子的妓女老七的丈夫。水保的到来,先是使他“虚怯”、“拘束”。但当他看出来人愿意聊聊乡下事情,因意外而高兴起来,“凡是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都拿来同水保谈着”。世故的水保虚应着他,有一句没一句地随便答着话,可丈夫却滔滔不绝。栗木做的犁柄、爱捣乱的小猪、新整治的石磨,还有那个“狡猾”的小镰刀,甚至希望明年得个小宝宝——丈夫有多少话要向女人说啊,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随着这些话汩汩流溢的那份寂寞,怕已不是“淡淡”的了。可是既然已经说出来,有人听了去,这寂寞也就不窝在心里了。水保走后,丈夫回味刚才的谈话,想起水保喊他做朋友,还要请他喝酒,“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完全是乡下人的憨厚心理和素朴至极的表情方式。那山歌也是纯净如洗,“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也许,他理解到妻子的生意,“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就像他原来认为的那样,“事情非常简单”,“名分不失,利益存在”。寂寞感既已发泄出去,自己也确乎感觉不到还有什么损失和不满了。
该吃饭了,老七不回,自己又不会烧湿柴,饿了,生气了,“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水保装满钞票的抱兜似乎一副“骄傲模样”,那张橘皮红色四方脸也变得“极其讨厌”,而“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的话,也尤为刺耳。他止不住心中怒骂,愤怒和妒忌使他“唱不出什么歌”,“也不能再有什么快乐”。这种情绪不断滋长,他想发脾气,把所有湿柴都丢到河里,但湿柴被别的船家捞去,并即刻点燃了。丈夫由愤怒而感到“羞辱”。汉子的烈性,就像那湿柴,本来在乡下哪里有事情会让他如此发作,可是城里人人都可把它点燃,爆裂出火焰。无处不在的对抗和冲撞攫住了这位憨厚老实的乡下汉子,“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走路”。这位刚烈的乡下汉子不再能够与城里的人事、物事和平相处了。他开始感受到深深的刺激和伤害。他鄙夷、咒骂他们,并迫切需要回到有那么多可爱的物件、朋友和有趣事情的乡下。他在那里才能得到精神和情感上的滋养和抚慰。走到街尾,却遇到回来的妻子,还有特意给他买的一把崭新胡琴。妻子借掌班大娘的话向丈夫陪了错,有硬有软地抚慰,丈夫也不好坚持回家了。他们一起拉琴唱歌,“年轻人在热闹中心上开了花”。但歌声琴声引来了两个醉鬼兵士,妻子无奈只好又去伺候他们。更深的伤痛袭上丈夫心头。即便没有他们,丈夫能跟妻子度过一个安静甜蜜的夜晚吗?水保可是说过要来的!丈夫沉默了。送走兵士后跟大娘说笑的老七也“像是想到了什么心事”,拉住五多,不许她说话。“一切沉默了。男子在后舱先还是正用手指扣琴弦,作小小声音,这时手也离开那弦索了。”老七去讲和,也不成功,只好说:“牛脾气,让他去。”汉子看来是决心明早离开了。
半夜里,巡官和水保来查船。醒来的汉子惶恐不已,等人走后,他希望同老七讲和了,“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件事情”。大娘“明白男子的心事,明白男子的欲望,也明白他不懂事”,因为巡官就要来的,汉子仍旧没有机会跟媳妇在一起。而“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看来,两个人都感觉到了伤痛,很深。
汉子一早就要回去了,老七往丈夫手中塞了七张票子,但丈夫把钱全撒在地上,“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钱有什么用?谁也无法摆脱这份伤害了,钱只能带来更多刺激,它会勾起更大的耻辱感——原来这损失,钱根本无法买回来!这本来在他们意识中“非常简单”、“极其平常”的事情,终于让这对夫妇不堪忍受,于是双双离开城市,回到乡下的家。
促使夫妇回归乡野的直接动因,就是两人先后体味到的、愈来愈浓重的、城市带来的伤害。城乡有着两类生活,两套话语,两样情感,人也是两种不同的人。城里那么多淫糜、矫饰、虚伪,乡野间则是那样的素朴、单纯、真诚。农村向城市输入女人青春的肉体和纯朴的感情,城市接纳着、也毁灭着。这样的伤害终于累积到令淳厚的乡间汉子也愤怒,也感到了羞辱。美丑、善恶、真伪的对照中,乡下夫妇选择了对前者的回归,完成了自然人性的觉醒与修正。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乡下人的情感、心理、精神在遭遇城市带来的摧折时,由浑然不觉到淡淡感伤、愤怒不平、不堪忍受、愤然回乡的过程。仿佛百川归海,所有这些,都指向对远景中包蕴无限美好的乡村的回归。
作者落笔在城市,却从丈夫——老七——水保的对比与变化中,从对城市加于乡村层层伤害的剖示中,从夫妇俩的最终选择中,充分显示出乡村与城市喧嚣相对的静谧、与城市芜杂相对的单纯、与城市丑恶相对的美善、与城市矫饰相对的素朴、与城市虚伪相对的真诚。乡下男子身体强健,“诚实耐劳”,安分守己,又会拉胡琴,又会唱山歌;女人“大臀肥身”,细致多情,有着“乡村纯朴气质”;家里有石磨、小牛、小鸡同小猪,有水碾子、麦子和风干的大栗子。不仅仅是夫妻恩爱,人与物之间也宛若有亲密的感情:在丈夫看来,小鸡小猪亲近如朋友;提到屋后栗树上的栗子,说它们“乖乖的从刺球里爆出来”,“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说到小猪捣乱的脾气,称小猪为“乖乖”;那把心爱的小镰刀会像“躲猫猫一样”的“躲在屋梁上饭箩里!半年躲在饭箩里!它吃饭!一身锈得像生疮。这东西多坏多狡猾!”失而复得的小镰刀更受珍爱,那么精巧,不舍得用它割草,只是“削一点薯皮,刮刮箫”。对乡村虽不是整体描绘,却随处点染。那份对乡野质朴、圆融人性人情的护守,对自然、美好、和谐乡村的回望,有着持久而深挚的感人力量。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赵慧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①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31页。
② [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月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