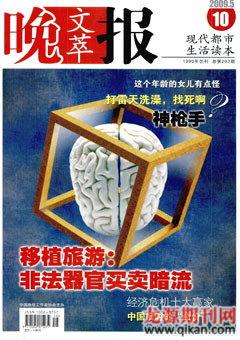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韩少功
说·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
易某最爱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了不少。
知青中还有故事王,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基督山伯爵》、《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
“玛——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多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老祖宗都不认识了?”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有人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我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是指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
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擦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这本书很反动的,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啊。你没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本。对方很高兴,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是否要去看看?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中,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他后来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他们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的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
事情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致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清醒还俗?
“文革”远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我终于沉不住气:“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摘自《扬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