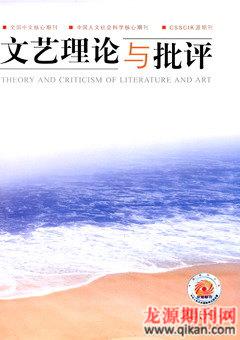游历西方与中国认同
项 静
文革结束之后,以寻找“真实”的名义叙述西方,成为新时期作家一种努力的出发点。1980年代初期作家们的西方游记作品正是这种努力的明证,作家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西方的现代世界。那是一个以交流为尚的时间段,最早获得机会的中国人开始出国考察、讲学、读书、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性活动,外国人也陆续进入中国考察、旅游、讲学,西方的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开始登陆文学界,乐团、歌舞团在中国舞台上演出,外国电影、电视剧等开始引进,交流碰撞的机会越来越多。张承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和其他作家一样对西方充满了好奇与向往。1984年前后,张承志访问了蒙古、西德、美国、日本四国,将旅途经历与心灵感受记录在第一本散文集《绿风土》第1辑的前9篇文章中。张承志在西方游记中也提到了“真实”问题:“我看见了MESA VERDE(美国印度安人的聚居地),我看见了我有生以来惟一一次见到的不合理自然景观,也感受到了那么多书籍都没有写到过的一种真实。MESAVERDE使我的美国之旅成为有益的,在苦于语言隔阂又从未获得语言之外的交流——这种已经连续了十数年的我的经历中,MESA VERDE终于变成了最新的一环。”
不同的是,在以“真实”的名义对西方进行游记体叙述的过程中,张承志的游记里所遭遇的是另一种“真实”。其他作家游记中所呈现出来的物质丰富、技术先进、民主自由、环境优雅、人民热情友爱的西方形象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是一种梦想,张承志大概也是怀着一种类似的梦想去西方寻找的,然而,他却发出了一种“不谐”音,这种“不谐”之音是对西方的普遍性知识和标准生活的质疑,重新触碰社会主义历史传统的遗产以及它的现代想象所提供的资源,并且由此蕴藏了生产出新的生活可能性的选择。在关于西方的现代想象中,他比其他作家更多一分警惕和紧张:“说我在巴伐利亚的时时刻刻都思念着伊犁,都痛苦于游子之情,都回忆着祖国山河,那是恶心的——但我在那些绿丘墨浪中确实怀着一份保留、一份对比。我如同警惕般保持着一根弦的紧张。”
张承志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详细描述所见所闻的“西方”形象和细节,而是迅速转入了自己的文学世界:理想和尊严、星空和草原、艺术和体制、大段的议论与抒情。本节拟以《绿风土》为主,兼及张承志的其他西方游记,对张承志作品中的西方叙述做一个详细的考察。
一、美国梦
“梦”是《绿风土》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我们习惯称呼那种无力实现的美好情境为梦想,许多未曾踏上过西方土地的人都经常会有一个梦想,使用率最高的就是“美国梦”,那是财富与自由民主的代称。张承志也对这个词情有独钟,怀着挖掘这个梦的实质目的来到美国,但在美国下决心修改在《金牧场》中对这个梦的善良猜测。张承志后来出于对《金牧场》的不满,将其改写为《金草地》,并要求作家出版社停止发行《金牧场》。关于两个文本的文字和思想区别,可参看许子东的《读张承志的(金牧场)和(金草地)》和《张承志:守卫昨日之梦》。但这两篇文章的着眼点过于强调张承志的“昨日之梦”,强调张承志的红卫兵背景,而不是其与现实的关系。张承志在其他地方也表示了对《金牧场》的不满,如在《真正的人是x》一文中,他说,“一九八七年,我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不仅过大地夸赞了美国黑人公民权运动中的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而且错误地夸赞了美国的清教主义。这部书中涉及的‘美国梦、德沃夏克的交响乐、关于哥伦布的议论,都肤浅至极、轻浮至不能原谅的地方”。这些被张承志认为“肤浅至极、轻浮至不能原谅”的,应该都是“美国梦”的可见标准,不仅如此,张承志还进一步把当时还带着绚丽色彩的“自由”“民主制度”捎带着批判了,他说:“自由,自由,这个国家用自由泡酥了一切价值。宗教的目的性在这片国土上迷失了。每一个拉比、牧师和伊玛目都像政治家。高中女生翘起晒黑的大腿在客厅里放声高笑。每个人开着一辆撞瘪了一块的汽车。原野上种的不是为人吃的玉米田懒洋洋而放荡地绿成一片。”张承志还认为突然背负上的民主制度使他们(黑人公民权运动和印第安聚居区等广义地属于第三世界范畴的人群)茫然地丧失了任何继续自己的可能。然后他提到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当时这种表达怕是要拂逆公众尤其是当时知识分子情感的,“一九八七年,我旅行老美,发觉每座大城都有一条胡同(绝不是主要大街,故称胡同)被命名为‘马丁·路德·金路。当时,我觉得毛主席有一种未曾被解释过的哲理的深刻——非暴力主义完全可以当成体制的招牌或粉饰;它有那么一股奴才气,把正义通过下贱表达,让年轻人觉得不舒服”。张承志是在恢复毛泽东曾经阐述过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第三世界的打破现行体制的世界构想。
张承志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梦想”的不信任,对平庸奴才气的不屑,对体制招牌或粉饰的不舒服,对终极价值缺席的不满。一方面,因为张承志是在一个革命语言高度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化环境里成长并开始识字写作的,所以游记中的“我”从生理感官上处处有意无意地表达着革命意识。所以他在走进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后的心理感受“就是一种使我好奇,使我冷静,逐渐使我起了一层反感的莫名气氛。它沉浸而下,傲慢而专横地擦疼我的皮肤。……它以现代化后的优越和德国人的优越感继续用那严厉而彻骨的气氛摩擦我的肌肤”。他在广漠壮观的美国平原上能感受到“美国之绿蒸腾着一股骄横之气,掀动着遍地飘扬的星条旗”。诸如“经常听到据我看来是毫无教养的不礼貌的问题:你愿意住在美国吗?你在中国感到自由吗?你来到这儿你感到幸福吗?你有汽车吗?”这样的问题使他忍无可忍。这些事务所对应的语言系统属于政治科学层面上的,它们可以量化,可以满足物质的需求,但是与张承志的语言系统是错位的,并且严重偏离。另一方面,对“尊严”的追求,这个尊严的根源在许多人的意识里是一些不愉快的记忆的孪生兄弟,或者说是文革梦魇的继续。赵园对这个“尊严”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这是张承志宣称的将为自己“寻找一种方式”,一种“今后存在的形式”。他不顾流行思路甚至不惜拂逆公众感情地从毛泽东那里寻找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资源,但他并未试图代行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只打算说“一个人的历史”。赵园曾经略显悲壮地说,“你不能断言哪一个人的历史是不可能或不真实的”。这个评论十分中肯。
张承志的心态对于那个年代的人应该可以感同身受,但是他旋即把这种保留、警惕和紧张转化成了不宽容的批判,并且不惜拂逆公众的感情顽固地坚持下来,在中国举国上下开始蓄势“走向世界”的情势下,他的思考几乎注定了是一次孤独的失败的旅程。他在《不写伊犁》中记述了自己的这一心灵感受:“这是一次失败之旅,我闯入了一个无法突破的绿网,我不能像在蒙古草原上一样同它
的灵性直接交谈,也不能像在伊斯兰山区一样与它心感神交……我走过了几个城市,但我已经忘了它们,我心中焦急我暗中责骂自己但我束手无策。”所以张承志痛苦地呓语,自己的梦失败了,追踪他们(西方世界)的梦狠狠地撞了墙,这个梦想的破碎,才有另一个梦想的出现,回到他的草原和故乡,回到母亲的怀抱。
在一个体制化的、世俗化的世界里碰壁的张承志回归到对本真、神奇自然的迷醉,将迷狂状态下与客体世界物我一体般的沟通视为人的精神自我的提升,认为其作为人生境界与永恒价值的等值。
二、MESA VERDE
张承志总结自己的美国之行,从美国回来之后说不出什么算是一桩收获。世界多少是见识了一些,但并没有哪个使我真正有过震动。除了在MESA VERDE看到印地安人撤走后的高原。那些作家们所感叹道物质丰富、技术发达,对于张承志来说只是一些“见识”,而没有真正的感动。在《木石守密》中张承志解释道:“在伟大的美国民主制出现以后,MESA VERDE只剩下当旅游区这一条路。任何新的愤怒,任何造反异端,在星条旗下都变成了正统的体制……对于我,MESA VERDE(印地安土著区)只是给中国的一个注释。”张承志在《绿风土》中多次提到的MESA VERDE,这个印第安人的聚居地,成为他萦绕不去的地点,它超越语言、情感、经验,“在苦于语言隔阂又从未获得语言之外的交流——这种已经连续了十数年的我的经历中,MESA VERDE终于变成了最新的一环”。张承志的文学以另一种方式注解了施米特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任何实质性的民主制度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原则,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才有平等,地位不平等的人之间绝对没有平等。因此民主制度首先要求的是内部的同构性;其次,只要形势需要,它就会要求排斥和清除异质性成分。”一方面,那段不愿意被提及的文革历史不是从此湮灭不闻,而是借由“MESA VERDE这一环”重新续接起曾经潜行匿踪的一段历史,并且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另一方面,MESA VERDE作为民主自由的美国内部一个不能简单化解读的暗疾,使得张承志对普遍化的平等思想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并且引诸中国自身。
张承志说:“永远不会改变人民的十年苦难给我的真知,以及江山的万里辽阔给我启示”,这是一个激情的宣告,在张承志的西方游记《绿风土》中,他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高速公路上、辽阔的绿色平原上,清晰地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思绪不断闪回中国的国土,闪回到“酷热如火的鲜红山脉”,“只有在MESA VERDE我才梦醒般突然忆起了宁夏和新疆,在MESA VERDE用不着英语和任何一种外语,我突然如释重负地感到了平等”。最后急切地对自己发出砰喊,“回到亚洲去吧,回到北亚,回到东亚,回到中国,回到内蒙古草原,新疆枢纽和陇东山地。在那里,那绿风土中的秘密已经离你很近了”。我们熟悉的“地理中国”的图像就出现了,从北中国的大草原出发,扩张了《北方的河》中的“北方”与“大陆”等地理边界和感情边界,成为不断增殖的地理概念。与这个“地理中国”相匹配的是人文内涵,他试图建立起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框架,从而充实起一个与他所批判的“西方”相抗衡的“中国”形象。
中国的宁夏、新疆,内蒙古草原,伊斯兰山区,它们与张承志作品中“草原一母亲”、“人民”的理念息息相关。《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在伤痕与倾诉中“母亲”或者说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人民”的指称是十分突兀的,一直到后来的创作中张承志一直坚持“人民”的美学观念,额吉,主人公的交流对象,影响者和教育者,一名伟大的草原女性,久经磨难但不失游牧民族本质,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的关键时期,完成了改造红卫兵为人民之子,中国底层人民温暖和力量的象征,作家也完成了对于苦难世界中的人的强烈认同,最苦难、最贫困的地方有着最真诚、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追求,如后来的小说《黄泥小屋》中的穆斯林庄稼汉,执着地拥有念想,其念想就是一座黄泥小屋,《三叉隔壁》中的农业工作者与乡民,“念想”则是一片嵌在戈壁滩上的“碧绿的苜蓿地”。这些均属卑微的“念想”,人物正是因着这念想,才“仗着心劲”,追寻着活。
《绿风土》中多次提到一位伟大的画家——梵高,甚至还逐副介绍梵高的画作,不忌讳谈梵高的画与自己作品的关系,比如《望星空》之与《北方的河》,《向日葵》之与《金牧场》。越过文本中的具体指涉,我们还知道张承志与梵高在宗教上的认同。梵高“我想用这个永恒来画男人和女人,这永恒的符号在从前是灵光圈,而我现在在光的放射下寻找,在我的色彩绚烂里寻找。但这却不阻挡我可怕的需求,我能说出那个字来吗?宗教”。张承志后来转向宗教书写,如《心灵史》,薛毅在《张承志论》里曾经对张承志的文学思想有这样的论述,“张承志更进一步找到了生命之根,回到了回族之中,一个由中亚进入中国,失去了故乡,失去了母亲,生活在荒芜、贫瘠土地上,只剩下信仰并坚守信仰的民族,一个能在精神上活着,保持灵魂的圣洁和崇高的民族,在贫困和苦难中追求爱、人道、人性、保卫着穷人的宗教”。
宗教意识和人民美学随后成为张承志作品的重要标志,而他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1989年冬到1992年秋,张承志在日本和加拿大又有两年的异国游历,这一次他已经不限于痛苦挣扎了,而是有了快意恩仇的味道,在《清洁的精神》中直接沿用“西方列强”、“殖民者”、“美国佬”、“盎格鲁·撒克逊”等称呼,更在《岁末总结》中表达了自己的暴怒,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抗“世界化”图景,抗击新帝国主义全球化侵略的历史进程的意识。
有论者指出,“中国认同”不但不是对“西方认同”的反抗,相反,“中国认同”是展开“西方认同”的一个必要环节。以《北方的河》为例,主人公翻译并经常激动地引用李希芬霍尔的地理学著作《中国》,文化的“中国性”或者对于中国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五条大河都是被一种科学与人文的奇怪组合——“人文地理学”给虚构出来的。现代地理学是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通过地理概念的确立,我们建立和巩固领土的概念,只有具备了领土,民族国家才有了实体的依据。中国人对“中国”的体认是通过一种“外来”的学科,即“现代的知识”所引导,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前提也是来自外界的指认,我们用来反抗西方的“中国”恰恰是西方创造出来的现代性装置。这一论述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并不能用来简单地解释张承志作品中的“中国认同”,“地理中国”已经开始转变为“西北中国”或者是“边陲中国”,这是一个底层或者说穷人的中国,也是有宗教意义的新的认同,而非大文化意义上的泛中国。
张承志开始迥异于当时文学界“怎么写”与“写什么”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他对于写什么表现出自己的无所谓,写得好坏不是首要的选择,这也是直接回应许多人对他的“红卫兵”精神和文体的指责,“对我来说,我要用它鼓舞自己上路的心情,鼓舞自己走进底层的方向,鼓舞自己达到真知而不是通说的目标”。这个“真知”就是重新叙述一个包括了底层和第三世界的旅行,在这种旅程中,有饥饿、干渴、褴褛、盘缠罄尽,并且是和自己的生存谋生相似的世界,是生命的必须之旅,有自己的伦理和信仰:“我只追求正义。只以底层生存的人为信条。”综上所述,张承志无论是在批判西方还是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始终在聚焦事物的“独一无二”性,并且不断地肯定自己,最终表明“灵魂没有交换价值,它不属于普遍性的国度”。回到韦伯所区分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张承志无疑是远离政治科学的,他“看见”的西方与投射着自己愿望的“中国”都不是具体的,是“价值”意义上的,但是其他作家所看见的政治科学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也是不能缺少这个纬度的,不然那就是一场迷失。
关于张承志,王安忆与张新颖有一段对话,恰当地做了一个总结:“(张承志)太没有匠气了,太不像匠人了,而我是个匠人……他一定要直抒胸臆,他一定要抒发情感……中国历史那么漫长,版图那么辽阔,时间和空间的含量都特别大,就特别能满足他的悲情,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比较宝贵的就是,对人民的苦难的一种反应。”这些使得张承志成为他自身的东西反哺给了时代,他们彼此就是这样犬牙交错,当他给我们那样一个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会惊奇。说到底,他是独一无二的。从现在的背景看张承志,他的意义就是他的兀自存在是乐观主义者所不能忽视的,他标志着历史的车轮不能绕行的一段路程,是广阔平原上崎岖嶙峋的一座山头,或者迟早要浮出历史地表的问题,诸如在遭遇西方时的尊严问题,对美好生活的标准问题,中国认同问题,回归宗教信仰问题等。《绿风土》是他的文学作品中最早、最集中地表达出他对西方看法的散文集,在商品大潮尚未席卷中国土地的历史时期,张承志的文学探索颇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