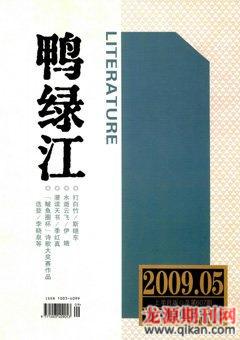我在沙漠的内心生活
杨献平,1973年生,河北沙河人。原生态散文写作理念的提出者、概括者和实践者之一。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首届“QQ作家杯”散文特别奖、首届“自然生活与思想”征文奖等。著有散文长卷《刀锋苍狼:匈奴及其帝国》(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我们周围的秘密》及合著《原生态:散文十三家》(百花文艺出版社)等。现居额济纳。
有一年,我一个人,在外地,傍晚启程,步行回家。落日隐没,夜幕深入肌理时,我还在路上。路是山路。为了早点回家,我只能抄近路。两边是峡谷和森林,双腿擦着岩石和茅草。夜鸟在草丛或者树枝上叽叽而鸣,野狼在幽深林中长嚎。星空之下,寒冷铺天盖地,在风中,将南太行所有的泉水和溪流关进了冰层。脚步在空谷踏出一片回声。似乎一些人的喊叫,一些隐秘之物的叹息。我头皮发麻,走一阵儿,跑一会儿。气喘吁吁,浑身热汗。再后来,有冰凉的东西打在脸上,像是一粒粒针尖,叫我莫名疼痛。
我必须行走,一刻都不能停留。爬上一道山梁,迎面一阵大风,差点将我扑到在地。心里腾起的恐惧让我全身发软。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好多事情:幼年的快乐和不快乐,成年之后的欢愉和疼痛,面对的艰难和不可预知的前方路途,一幅幅图景,闪电一样连绵。再次站起身来,双腿发软。四顾的夜幕像是一张巨大的秘语,以黑暗的方式鼓荡不止,嘈窃不停。
我想,今后,一生当中,我再也不会这样行走了,尤其在黑夜。那种步步紧逼的孤独、恐惧和疼痛,比刀子更深入骨髓,比绝望更逼人沉沦。路过的村庄已经开始沉睡,路过的凶险之地(尤其是知悉的他人生命罹难处),像一口巨大陷阱,连风中打摆的树叶,也包含了某种玄机,甚至致命的暗示。
临近自己家成片村庄的时候,心情放松了许多,暗自庆幸自己能够穿越漫长而凶险的夜幕(似乎杀机四伏的命运隧道),再一次安全回到温暖的人世。这时候,我才发现,在黑夜行走,夜再黑,行走的人也还是具体的和明亮的。人在其中,就像是一粒移动的火星,照亮所有的孤独和本能。
进门的时候,恐惧消散,夜幕从眼眉和发际远去。太阳升起,光芒再度泛滥,满山遍野的生命都发出了明亮的声音,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好,感觉到一个人被白昼包围是那样地实、安全和慰贴。
开门的母亲看到我,一阵惊诧,叫我进屋,拿出昨晚的馒头,点火热了昨晚的剩饭。张口的时候,眼泪应声而落,扑嗒嗒地落在洁白的馒头上。母亲埋怨说,怎么不搭车呢?不住在亲戚家里呢?怎么不等到早上再回来呢?我一句话没说,走出屋门,站在院子里,仰头看了看高空的太阳。风在山岭上翻动茅草和树叶,洁白的羊群漫过对面的坡地,幽深的森林在远处苍翠,安静得不发一声。
两年后,一九九二年冬天,清晨,太阳还没升起,我就起床了。父亲和母亲比我起得更早。灶火熊熊,驱散了四周的冷。阳光彻底降临的时候,我背起行囊,走出自家院子,沿着左边向下的山路,向公路走。沿途的老坟、桃树林和房舍,一如既往地陈旧和沉默。
走前身侧的父母亲满脸悲伤,母亲的眼泪总是擦不干净。我知道,她舍不得我走得太远,但又不得不让我离开。上车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上来,在鞭炮和锣鼓声中,父亲的脸颊像是一块紧绷的石头,母亲两眼红肿。
我没有哭,反而觉出一种自由,内心充满了对远方乃至新生活方式的想象和渴望。到乡政府,看着依旧泪流不止的母亲,我想我应当说些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一遍遍叫母亲放心,到部队,一定会干出个样子。母亲嗯嗯着,反劝我说,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做事,不要给家人丢脸。
车辆启动,父母站在窗外,看着我。这时候,身材高大的弟弟气喘吁吁跑来,一路喊着哥、哥、哥,我向他挥挥手,使劲看了一下父母亲的脸,随着渐渐加速的车辆,平生第一次远远离开了南太行,离开了那里的村庄和亲人。
从邢台开始,我的众多的同路人一起,从故乡出发,身体在钢铁之上,被快速运载。朝着明确的方向,在曲折的道路从北向西,走州过县——那么多的关山、河流和人烟密集的城市和村庄,一个人容在更多的人之间,陌生的汗味和方言让我感觉到另一种孤独。我长时间看着窗外,从河南的梧桐、陕西的城墙到李广的陇西,扑面而来的戈壁阔大无际,连绵的黑色卵石似乎整齐排列的铜弹壳,在衰败的阳光下泛着零碎的光。
车过乌鞘岭,又是深夜,车厢里到处都是松动的睡眠。坐在硬座车厢,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孩子提着红色的灯笼,在黑夜的山谷走。周边的事物都是黑色的,连自己的脚尖、鼻尖都漆黑一团,白色的石头上有水,水中长着几根青色的草,草根四周有几颗晶亮的鹅卵石,几条鱼儿缓慢游动——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正在踌躇之间,越来越深的河谷里面,突然都是人,几个络腮胡子的男人伏地磨刀,一群骑马的人好像逡巡的士兵,还有一些衣饰鲜艳的妇女,站在青砖灰瓦的阁楼上,像是唱歌,又像是仰望——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他们是谁;为什么来到,又到何处去。
醒来,天光乍露,右边的戈壁仍旧是黑色的,左边的祁连在雪中发白,似乎庞大的梦境,站在河西走廊制高点,仰视寰宇,俯瞰人间。右侧依旧是匍匐连绵的戈壁。路下的村庄有人开门,有人骑车,有人站在羊圈门口,有人站在沙堆上,不住抽烟。带兵的连长说,这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欧亚大陆的必由之路,盛产丝绸、香料、驮队、强盗、战争和诗歌——到边城酒泉,下车,站在寒风煤屑的站台上,只觉得大地仍在晃动,沿着犹如盲肠的河西走廊,继续向西的路程。
边地城市——酒泉,与汉武帝、霍去病、匈奴、月氏、吐蕃、回鹘、西夏等民族和历史紧密相关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根远处飘来的草芥,在驼铃和流苏,刀锋与胡笳之间乍然落下,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和新鲜。
我平生第一次走得如此之远,沿着岑参、王昌龄、李白和杜甫走过的那些道路,从京畿之地到塞外边关,从北方乡村到西北大野,我始终觉得,雄浑博大的西北疆域——河西走廊——边关和疆场,诗歌与美酒,都是一些可以让灵魂浪漫的美妙基因。坐在大轿车上,徐徐进入酒泉市,尽管与内地城市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感觉仍像是在进入一个梦境的城市,一个充满传说和各种异趣的乌有之城——那时候的酒泉,到处充满尘土,矗立在市中心的鼓楼,虽然颜色犹新,但姿态却不再巍峨。稀少的行人和车辆,在淡黄的阳光下,步子不紧不慢,脸颊毫无表情,不一会儿,就相继没入短促的小巷或者不高的楼宇。
我们也是,被车辆承载,穿过市区,在越来越荒芜的公路上奔驰,烟尘在车后犹如风暴,遮没了来路。偶尔的孩子冰面光滑,白得叫人伤心;偶尔的坟墓土碑林立,在阔大戈壁上,昭示着终极的无尽和时光的苍凉。
零星的村庄被干枯杨树包围,身穿羊皮大氅的人,驱着羊群,在荒芜的田地和戈壁上牧放。还有几辆笨重的四轮车,载着尘土灌满的货物,向南或者向北。还有几位衣饰鲜艳的女孩子,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在寒风中犁开一道缝隙,通红的双颊让我想起成熟的苹果。
发源于祁连山南麓的弱水河(当地称黑河)在大戈壁和村镇之间蜿蜒,几乎没有流水,偶尔的水洼结成冰块。河道四周,隐约着一丛丛紫红色的红柳灌木。紧接着,是一小片的绿洲,以前的名字叫毛目(据说是因居弱水河边,以河喻目,绿洲比眉,因而得名)。奔走了五个多小时的车辆骤然停下,趁别人下车的时候,我刮掉车窗上的白霜,看到的外面低矮的民房,简陋的街灯,还有堆放在房顶的玉米秸秆,在风中哗哗乱响。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生当中,会在这一个陌生的地方安营扎寨,并持续十数年。在我内心,对这一地方的外表,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渴望城市的心蓦然冷了下来。走下车厢的时候,我忍不住叹息了一声,迎面的一股冷风,把我的咽喉打疼。
放下行囊,才感觉浑身是土,粘稠的土,连五官内都是。那一天,我特别翻了一下日历:1992年1月12日。
从这一天开始,我开始了在巴丹吉林的独立的尘土生活。后来,我在当地《县志》看到,《山海经》中将巴丹吉林沙漠称之为“流沙地带”,周穆公、老子和彭祖等人先后于此谒见西王母,或“没入流沙”、“凿窟以居”。弱水河一名也出自《山海经·海内西经》(“水弱不能载舟,鸿毛不浮,是为弱水”。又有佛曰:“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或许,这一些,都与我即将展开的生活没有任何实质性关联,它们只是一种流传的说法,远去的存在及其事迹。对于我这样活在当代、初来乍到的一个人、过客和独行者而言,充其量只是一种想象的诱因和“基石”而已。
初春,风沙猖獗,像是一群暴躁的野兽,在戈壁之上,毫无遮拦;夜晚的吼声惊醒万灵,细碎的尘土落在喉咙里,土腥的味道让我有一种身陷浮土的沉重感。打开灯光,整个房间充斥着黄色土雾,新买的书架、脸盆和桌凳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如此,一直到四月末,风沙才相对减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营区之内,绿树蓬勃,水声四起,戈壁上的骆驼刺也开始萌发绿色。为数不多的果园内,花朵盛开,枝桠横生,叶子们相互拍打着,把花香送得更远。身在其中,我觉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芬芳和快乐。
这是巴丹吉林沙漠一年中最为美丽和令人迷醉的季节。没有什么比周边的环境,树木、水和花草更能够令一个身处异地的人感觉欣慰了。那些天,我时常走到果园中间,采一些苜蓿回来,清水洗、煮之后,凉拌或炒了吃——满嘴的绿汁,连牙齿和舌头都是。
青草的味道,是我喜欢的。除此之外,我还热爱土豆、萝卜、大葱和鲜红的辣椒。在巴丹吉林,在吃食上,我的一个重要的改变是,由半素食主义者转变为半肉食主义者,但仍旧不愿意吃鸡、鸭、鱼,乃至其他一些动物烹制的菜肴。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体重竟然由最初的六十公斤降到了五十一公斤。自己照照镜子,一个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的人赫然出现在面前。自己也觉得吃惊,忍不住顾影自怜,暗自心疼。
1995年,我离开工作近四年的单位,到另一个单位。似乎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觉得了环境乃至俗世地位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也第一次深切体验到“阶级”一词的深刻内涵。我渐渐明白,一个人在一个庞大集体中,与一粒沙子容身于一片庞大的沙漠,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背景的大,个人的小,群体或统一的力量和意志充斥甚至垄断到了各个方面,就连个人的私密心情乃至生理欲望,都要向其缴械投降。
而我,却是一个抵抗和反叛性质严重的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来自更大方面事物的压力表示抗议,时常有不遵从甚至反抗的情况发生。但在更多时候,我只能按部就班,和他人一样,顺从一个意志和一个方向。其实,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裹挟力量,一个人根本无法抵抗,也不可抵抗。
好在还有余下的空闲,那才是个人的时间,沮丧的时候,我时常将这些宝贵时间挥霍在睡眠和酒液当中。
季节交替。巴丹吉林沙漠夏天很美,尽管炎热,尽管戈壁之上经常汹涌着庞大的火焰,令人奇怪的是,那些置身火海的骆驼刺依旧青绿,没有一丝损伤。风沙也少,偶尔还有暴雨,山楂一样的雨滴普天而降,快速敲打地面。正午相对安静,人和鸟儿一样,躲在阴凉处,修饰羽毛,或者睡眠。没有风的时候,高大的新疆杨一动不动,叶子上泛着钻石一样的光亮。孩子们不停追逐嬉闹,欢笑之声,一波一波,此起彼伏。
傍晚,基本上都是人的各种声音,大声的,小声的,愤怒的,温情的,暧昧的,清晰的……混杂在一起。我经常一个人,从夕阳下出发,过马路,穿围墙,到安静的沙枣树林——百年的沙枣树叶子发灰,密集的果实尚还青青,风吹之后,它们相互撞击的声音,像是杂乱的掌声。地面青草肥厚而高,不少野鸡和野兔隐藏其中。不小心惊扰了,它们仓皇跑开,姿势笨拙。偶尔会碰到几个和我一样的人,坐在树林下面,自斟自饮,唱歌,叹息,东张西望。
五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冬天,临近春节,我决定回家。离开南太行这些年以来,我只是在信中了解到家乡和父母的情况。随着迅猛的时间,伊初清晰熟稔的村庄,竟然在内心变得模糊起来,很多时候,努力回想,也还只是一个简单的轮廓。
我想,这么多年了,它一定有所改变,我想我必须要回去看看。
刚签了请假报告表,我就提起行礼,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向南,回南太行故乡的行程,所有的事物都是过往,所有的行走都为了一个方向。不断的风景在窗外,也在窗内。闪过的,人的和自然的,都在冬天沉浸,尘土飞扬。那一次,我对回家这个行为做了一连串的分析和想象。
沿途,我靠在窗前,一直在想,忽然觉得: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所在的地域背景再大,而他自己,最终的落处可能也只是一座房屋一扇门。
北方的冬天,城市街衢上煤屑纷飞,到处都是冷。乘车或者步行的众多人们,穿着厚重衣服,走来走去,相互看到,又相互消失。迫不及待赶上最后一班班车,附在窗玻璃上,一个一个城镇看。旧年的丘陵依旧,旧年的房屋,多了一层白霜,旧年的山峦,风吹枯草。
日暮时分,回到家里,首先看到灯光,掀开门帘,父亲、母亲和弟弟坐在火炉边,端着碗筷,闷声不响地吃。一阵惊喜之后,就是说不完的话儿。灯光之下,父母脸上隆起的皱纹之间,漾着喜悦的光泽。说到后半夜,心情仍旧是激动和愉悦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到父母房间,继续说话。太阳的光辉到达窗棂的时候,我起身,爬上背后的山顶,俯瞰的村庄散落山间,盘旋的公路像是一根绳子,绕来绕去,最终在山顶上的缺口消失。奶奶的旧居仍在那里,老大的梧桐树枯枝如爪,在空中乱飞。邻居的房屋仍在,鸡鸣狗叫,烟火缭绕。窄小的公路上,不时有人和车辆,来了去了,远看,就像是一出哑剧。
一个月的假期,我几乎走遍了阔别五年的南太行村庄。收集的消息大致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当年的同学谁谁谁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到什么单位,以及其爱人、子女、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第二,夭折的同龄人。其中,会明是第一个,晓民是第二个,海文是第三个,张三是第四个,王五是第五个,天灾或者人祸(瓦斯爆炸、冒顶和水淹居多),都叫我震惊莫名。感生命之脆弱,哀生存之艰难;第三,同龄人的婚育和生活状况(生了女儿的一定要儿子,生了儿子的还要女儿);第四,村里各家的恩怨(张三骂了李四,王五打了赵六。张家偷了李家,李家毁了张家财产),以及富裕者的事迹(其中,包工头、煤矿和铁矿暴富居多)等;第五,母亲的唠叨。最大的主题是我的婚事(托人给我提了好几门亲事,都是女方长辈反对而未果)。她已经等不及了,那么多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我还是孤身一人。直到临走的那天,还在我耳边重复。
临行时,蓦然发现,父亲和母亲真的老了,皱褶满面。回身时,心突然狠狠疼了一下,眼泪流出来,怎么也止不住。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流泪。母亲的手和父亲的一样粗糙,身材高大的弟弟也眼眶通红,看着我,哽咽出声。
向西的路程,与当年相比,只是心情沉郁,思绪怅惘。但路程还是当年的陇海线和兰新线。河南的风景在三门峡显得突兀,路边的梧桐下面,一眼眼的窑洞,孩子们趴在冬天的黄土坡上,咬着嘴唇看长长的列车。穿越秦岭时,旁边有人说,这里一共有109个隧道。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灰暗。天水之后,黄土和戈壁,土山寸草不生,兰州的风景只是黄河。扑面的河西走廊,寺庙香火的味道,羊粪和尘土的气息,积雪的反光刺疼眼睛,让我不敢仰望。
在酒泉下车,心情仍旧沉郁,周身和内心仍旧散发着故乡的味道。离开一个月的巴丹吉林,还在尘土之中,微微晃动,这似乎是它的宿命,就像我,一个人,只身异地的生活,充满了各种艰险和未知。正月过后,空气发暖,傍晚的湖畔,散步的人多了起来,孩子们似乎也嗅到了春天的体香,一个个骑着小车子,或奔跑着,在夕阳中制造欢乐。
课余时间,我通常把自己关在房间,看书、电视或者静躺,胡思乱想。有几次,参加集体活动,我也不愿意抛头露面,看着台上活跃表现的同事们,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但绝对没有嫉妒和轻视,而是觉得,一个人自我表现(才能)的形式不仅仅在这里,也不仅仅这些。有一次参加聚会,那么多人,大声说话,推杯换盏,自由自在。而我,却坐在那里,心神不定,有人来碰杯,尤其是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我不敢正视,她们还没有走到近前,就面红耳赤。
我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自卑的人,骨子当中的落寞和悲观与生俱来。
这令我高兴也忧虑,发现自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看清自己,总归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自卑导致了我的自恋,悲观常常让我看到事物表象的另一面,而绝望,则使我从一定程度上,在最为孤独的时候,保持了一种清晰的意识和自我克制能力。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是一个拥有足够的世俗智慧的人。事实正好相反,我最惧怕日常的繁琐,乃至与他人之间可能的敌对与不快。
我愿意独自去一个地方,行走和冥想。
1997年夏天,我先后去了几个地方。一、金塔县天仓乡,在乡政府旁边的一所商店内,看到一位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姑娘,弯眉大眼,面孔周正,神情之中有一股令人迷醉的贤淑和安静。二、额济纳旗,在达莱库布镇的中心,看到纪念吐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三百周年的标志(高柱之上,匹马奋飞),一个人站在下面,仰着脑袋,一字不落看完背面的文字。三、兰州,爬兰山,并骑马奔腾了好一段路程,马蹄迅即,差点摔下来。四、营盘水库,几个同事和朋友,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捞了不少小鱼虾。一边的胡杨树叶子金黄,像是一堆金子。夕阳成血,大片胡杨树一动不动,偶尔飞过的野鸭和燕子,将它们衬托得更加明净和安详。
秋天,我和好友裴商定,两个人结伴到北边的沙漠走走。并先期做好在沙漠生存和过夜的准备。
数日后,向北的沙漠,出发的豪情。戈壁边缘,人迹和车迹不时出现,有的久远一些,有的崭新。走出约十五公里,沙丘展现,在大地之上,金色的躯体起伏连绵,光滑纯净。在戈壁与沙漠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一处约十米方圆的绿色植被,有红柳、蓬棵和芨芨草。叶子稀疏,但仍旧青绿动人。其中一丛红柳灌木根部,是一个沙鸡窝,抛开浮沙和碎草,有三只白色的蛋。
站在沙丘上,向北眺望,偌大沙漠一波一波,在大地上汹涌堆积,似乎凝固的海洋,浩瀚无际。抬头天空似乎近在眉睫,有一种覆压感。傍晚,我们走到一片干硬的戈壁上,沙子温热,自在的蜥蜴和蚂蚁们正在归巢。
前半夜,月明星稀,没有风。我们仰躺着,天空湛蓝无际,硕大的月亮似乎一个含笑的脸庞。我们谈到了上帝、人类登月和宇宙之上的人造卫星和各种航天器。说到古埃及和中东的沙漠。还有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我想起幼年看过的电影《马兰花》,那是沙漠的花朵,中国西部的花朵。故事淡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这一花朵的名字。第二天,太阳升起,沙漠一片辉煌,就连小片阴影,也有着足够的亮度。再一次行程,浑身疼痛,骨头断了一样。
继续向北,依旧是一座座沙丘。两个人在巨大天幕下行进,感觉到决绝和悲壮。中午,站在其中一座沙丘上,看到远处移动的骆驼,像是一块块移动的红色石头(形状奇怪,但却优雅安静),四周不见牧人。傍晚,走到了石头城(蒙语为海森楚鲁),冰川纪的遗址,那么多的石头,以猛兽、海龟、利剑和飞鸟的形状,在空旷中站立,风噬的身体,刀切的造型,令人赞叹时间的非凡作为,让人体验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坚韧与勇气。
在一块被刀整齐劈开的巨石下,又一汪泉水,清澈的水,沁凉的水,不断从石下向上翻滚,形成了一眼泉水,不断漫溢,沿着长年累月的细小沟渠,无声无息,流向广阔的沙漠。这一夜,我在泉边宿营,喝了好多泉水。处在空旷中,因为水腥,竟然有了一种草原的味道。我站在最高的石头上,学唱腾格尔的《草原之夜》、《蒙古人》,梦想有神仙或者临近的牧人,能够为我们带来悲怆苍凉的马头琴声。裴朗读了昌耀的诗歌:“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斯人》)
第五天,回到单位,乍然融入人群,觉得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这样的一种心理,让我始料不及,裴也曾对我说了相同的感觉。黑夜,我们坐在临近的土山上,喝啤酒,聊天,四周无人,说起那次远行,还有一个相同的认识:在沙漠生存的人,不到沙漠深处,就不会是一个有深度的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人,放置在沙漠这个大背景中,巨大与渺小,永恒与速朽,两相对比,是彻底的惆怅和沮丧。事实上,在沙漠边缘,视力再好也看不了多远——平坦有时也是一种隔断,你看到的,只是无尽的苍茫,天地相交之处,颜色苍灰,雾墙一般,阻挡了远望的目光和神游的遐思。到处都是沙砾,被风运来搬去,动作直接、重复,而又简单。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生活,迄今已经十七年了,我只是一个融汇其中的沙子,所有的行为和思维,包括个人私密生活,都是其派生的产物。我甚至以为,我这样一个人,已经成为了这片沙漠的一部分,其牢固程度堪与生养我十七年的南太行乡村相比。在这两者之间,一次次地去往,一次次返回,不间断的肉体换位和心灵挪移,它们对于我的影响同样深重。
但目前的状况是,我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时间正在超越南太行故乡,草木繁盛的北方山地,遍地荒芜的西北大幕——我已经觉得了它们在我内心流动的痕迹,在一个人肉体和灵魂之中,此消彼长,交相辉映。
在乡村,幼年的孤独和苦难构成了我现实生活的强烈自卑与不安,也造就了我内心深处的孤傲与刚强。很多时候,我时常觉得只是一个人,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尽管有终生不弃的亲人和朋友,但仍旧有如此这般的强烈感觉和心灵指认。
或许,我的这一种“个人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者说篡改了我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生历程。很多年来,我不止一次,咬着嘴唇,低着脑袋,或者仰首向上,对自己说:这么庞大的世界,纷纭的事物,呼吸和沉默的,张开和关闭的,繁华或者落寞,而“你”只能是其中一个。
现在乃至未来几年,作为“这一个”的我,在南太行和巴丹吉林沙漠一如既往,一次次将它们强大的地域习气乃至灵魂素质嵌入,每一个人、过客和土著流淌的血液乃至隐秘的骨髓当中,成为它们在人世的另一些鲜活标本和个体影像。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