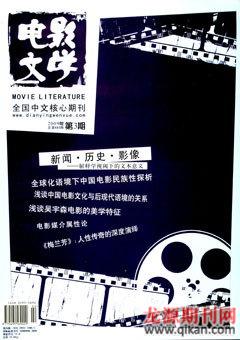流动、转换的叙述视点与平行交错的环状叙事结构
符 抒
[摘要]一部影片真正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如何以它的叙事修辞手段,包括流动、转换的视点,交错重叠的时空与相应的叙事结构,把一个故事讲述得出神入化,引人注目,并且成功地征服与控制观众的反应。这就是《情书》带给我们创作上的又一宝贵启示。
[关键词]修辞手段;视点转换;环状结构
美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讲的就是叙事。
的确,要把一个故事讲述得精彩,使之引人入胜,这里面大有文章。
其实,叙事与叙述,严格地讲,这二者有所区别,叙述是指话语层面上的叙述技巧,叙事则包含了故事结构和语言画面技巧这两个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意味着用视听话语虚构社会生活进程,以人物的命运,或者以事件的转变为前提,从一个事件转变为另一个事件。其间有因果性、时空联系、具体的叙事环境,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叙述者存在。因为“各种事实”要成为故事,只能通过叙述者的叙述,而叙述者的叙述,又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进行。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用智慧与修辞策略,引导着观众,同时也影响着甚至征服着观众的思想感情,因此,不是“叙述者”,而是“叙事者”的人生态度与艺术趣味,往往左右着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叙事者”,就有什么样的叙述作品。
一、《情书》中主要使用了三种视点:客观视点、人物视点和隐含作者的视点
1先说“客观视点”
“客观视点”的倡导者是巴赞,他强调摄影机的功效,可以从形式到内容实现最大的真实。但是“客观视点”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存在,摄影机表面看来好像是“客观”的,与电影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的视点、情感都没有关系,似乎没有任何思想,然而摄影机机位的摆放,角度的选择,拍摄长短的取舍,运动的节奏把握,统统是由人掌控的,应该说是编导的主观视点的直接选择,包括后期的剪辑在内,当然不会是自动生成,无不是编导视点选择的结果。所以,以机位与镜头来体现的“客观视点”,绝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它只能是带有编导主观掌控下的客观,说白了,不过是说服观众予以信任的一种修辞手段而已。
“客观视点”在这部影片《情书》中有大量的运用。一开始的片头呈现的就是一种“客观视点”,观众并没有听到谁的“画外音”,无论是女主人公的,还是作者的,似乎看不见“叙述者”的存在,但是确有一种“眼光”让观众看见了“视点”前发生的事件与渡边博子这个人物。这个“眼光”就是躲在摄影机背后的作为“叙述者”的作者的“眼光”,被人称为“隐含作者”。只不过他的“眼光”是通过摄影机的“客观视点”表现出来罢了。观众因此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一袭黑衣的博子为什么要这样躺在茫茫雪原上,仿佛要听任漫天飞雪埋葬自己?开始观众可能还不清楚其中的究里,但旋即很快便明白了:原来是痴情的博子内心的渴望,一度幻想自己就这样静静地追随已逝的未婚夫而去。这种来自摄影机的“客观视点”,在拍摄这组镜头画面的时候,采用了先仰后俯的拍法,“仰”拍则强调了博子陷入丧夫(未婚夫)之痛而难以自拔,随后的“俯”拍,给了她一个长镜头,采用大全景俯拍被冻醒后的博子,独自孤苦无助地朝着远处积雪覆盖的墓地,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走去。由摄影机实施的这个片头的“客观视点”,切入影片的角度选择了博子这个人物,这个角度的切入,可以非常及时地将观众带入故事之中,展开情节,引起悬念,激发我们浓厚的观影兴趣。
在“客观视点”的使用与运用上,唯有一个要求必须严格遵循,这就是要尽可能使我们的画面叙事,符合视觉的观赏心理规律,便于让观众认同。当然,影片中的“客观视点”,远不止这一个例子。比如,博子与秋场的戏,女藤井树因感冒而引起的家人之间的戏剧纠葛,甚至包括旧址要不要搬迁,爷爷反对而妈妈坚持等等。我们看到,《情书》中凡是离开博子和女藤井树这两位女主人公的“个人视点”的叙事,几乎多为“客观视点”叙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论述。
2再说“个人视点”
紧接片头之后的墓地祭扫。原有的“客观视点”,悄然转入“人物视点“叙述。这个“视点”的转换,甚至让人难以察觉,开始仍然是一种“客观视点”的描述:镜头在藤井树父亲的致辞感谢声中,从墓地的尖顶缓缓摇下,观众看到死者的墓前围聚了一群亲朋好友。这个简短l的两周年祭,在大伙儿欢快地端起红酒品尝之际,匆匆结束。死者藤井树的父亲,则大声地吆喝着要跟亲朋一醉方休,死者生前的好友捎来口信,要在深夜前来墓地祭扫,热闹一番。仿佛大家都把这个祭祀亡灵的仪式,当成了不得不履行的某种形式,这也许是大和民族对待死亡的一种达观态度。就连死者的母亲也坦然笑着对博子承认,她是借口托病故意离开。现在,参与现场真诚祭奠的唯有博子一人,她似乎反而成了另类,仍然以一腔真情,沉浸在难以忘怀的悲悼之中。
祭祀结束,博子准备驾车离去,我们发现,这场戏的“客观视点”向“人物视点”转移了,而且转移得非常自然巧妙:藤井的父亲敲窗拜托博子将藤井的母亲送回,但他显得很不高兴。他明知妻子玩的是一种逃离的把戏,所以当他送她上车的时候,用一种粗暴的态度将她推到车上,以致后者被弄疼了,发出一声低低的抱怨。然后是一位醉汉前来企图胡搅蛮缠,被他的同伴们及时拽走。博子打量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坐在车内不知所措,她不知该说什么,似乎只是在冷眼旁观。沉静与喧嚣,悼念与忘却,对比是如此鲜明而强烈。我们可以看到,博子在这里的“冷眼旁观”,正是通过摄影机的“拍摄视点”进行的,摄影机的“注视”,其实就是“人物视点”的注视,摄影机的“观察”,就代表了人物的“观察”。影片随后展开的,回到未婚夫藤井树的家,走进他那间尚未打扫完毕的尘封的居室,同样也是从博子这个“人物视点”展开的。这间屋子对博子来说,亲切而又熟悉,陌生而又久违。博子正是在这个“家”,偶然从“毕业纪念”册上,发现了藤井树读中学时代小樽市的家庭旧址,便情不自禁好奇地偷偷将其随手记录在自己的手臂内侧。于是,接下来一封寄往“天国”的情书,就由此而产生了。
博子因失去了自己挚爱的未婚夫,愈发渴求了解他过去的一切。一方面可以使自己思念的心结获得抚慰,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永远跟他“生活”在一起。而女藤井树,对中学时代的男藤井树的了解,无疑是最熟悉的人选了。她和他同学三载,并且在同一个班上,“过了三年灰色的生活”,这自然让博子抓住了“救命稻草”。这位跟未婚夫同名同姓的女藤井树,或许是出于好奇,出于单纯善良。出于对博子的同情,她欣然答应了她的要求。因为博子告诉她,男藤井树“以前是我的恋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只不过有时会想起他,我想他可能在某个地方
努力奋斗着。”秋场认为博子故意隐瞒男藤井树亡故的消息,是一种对女藤井树的欺骗,其实这是他不理解她的心思,如果博子按照秋场的想法告诉了女藤井树,这两位女孩的书信交往恐怕就很难进行了。女藤井树或许就会想:既然人已死,你打听他过去的一切还有必要吗?现在,女藤井树对博子的回应是一种“自述”,这种对往事回忆的“自述”,完全是女藤井树的“个人视点”,整个中学时代她对他那些印象深刻的、令人难忘的一桩桩往事的回忆,其实都是跟她直接或间接地、清晰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包括开学第一天老师的点名,两个藤井树的同时应答;做清洁值日,两个藤井树被并列安排在值日表上;选举图书管理员被同学故意作弄,以致女藤井树哭了,怒不可遏的男藤井树却与同学扭打在一起,两人在图书馆任职服务期间,男藤井树并不热衷于工作,却只管一次次几本几本的借阅那些不曾被人借过的书;错领试卷却佯装认真核对答案的样子,故意拖延时间不予归还,却让女藤井树在暮色四合的自行车棚,吃力地不断摇动把柄为自行车充电照明。当自作多情的大井一厢情愿地追求男藤井树,女藤井树反而傻乎乎地替她充当丘比特被惹恼了的男藤井树等候在她归来的路上,将一个纸袋罩在她头上,却令她一头雾水……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人物视点”中的人物,比如女藤井树,因受故事框架的限制,其视点不可能超越人物与人物活动的范围,所以作为。叙述者”的“人物视点”,也不可能无所不在,更不可能深入到除了作为“叙述者”的人物之外的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博子发现自己对来婚夫过去的一切知之甚少,而女藤井树由于情窦未开,更是只认为男藤井树行动怪异,不招女孩子喜欢,却不明白对方其实是属意于自己,因不擅长用言辞表达,所以别出心裁,总想用出格的举止,企图引起她对他的注意。这实际上是青春期中的少男少女,一种可爱而滕胧的表达方式。可惜少不更事的女藤井树,辜负了男藤井树这一番无言的“表白”。应该说,这种“人物视点”的选择与使用,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们俩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与青春萌动,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局限。实则是一种特殊的故事表达角度,能够产生浓郁的生活气息,说服人的真实感,使观众饶有兴味,与故事中的人物,尤其是与“叙述者”一起经历,一起感受,一起备受情感折磨,一起同喜共忧。
毋庸讳言,“人物视点”即是这个被选定的人物的主观视点,诚如苏珊·朗格所言:它“通过一个人物的眼光来过滤所有这些事件,可以保证它们与人的情感和遭遇相符合,并为整个作品——动作、背景、对话和其他所有方面——赋予一种自然统一的看法。”显然,这位叙事学专家对把视点限制在某个人物的经验范围以内的原则,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所以他强调,“用一个人物的印象和评价来限制那些(故事中的)事件,就是说‘统一的观点,(其实)就是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观察角度或经验。这样的人物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经历这些事件。”经历即呈现,从影片《情书》看,观众感受到的情况大致正是如此。观众与影片中的博子和女藤井树在一起,共同经历着故事中的这些事件,而不是无关痛痒地在听别人讲述故事或是冷限旁观看别人的故事。
3最后谈谈“隐含作者”视点
这个说法是叙事学家研究小说的一种方法。众所周知,诗和散文,与小说不同。诗和散文,直抒作者胸臆,而小说作者的视点,往往是隐藏起来的:经常以人物的视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看似书中人物的所思所想,似乎与作者无关,其实大有关系,而读者的多数,一般也不会立即与作者的视点相联系,以为那全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自述。因此,作者的观点隐藏在“叙述者”的背后,人们却看得津津有味,电影在这方面跟小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隐含作者”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比小说有着更强烈的隐蔽性,电影还原物质世界,观众在银幕上看见的,是真真切切的“生活”,以为那只是人物的故事,人物的思维,极少有人会想,那其实就是作者的思维,作者的视点。作者并不出面,作者借助故事人物的“视点”,或者让故事本身“自动讲述”,观众恰恰很容易被迷惑被俘获。一般来说,观众普遍反感作者的说教,但对故事中人物的倾诉,只要态度真诚,都毫无防范而乐意接受,这一点早已被无数经典影片所证实。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隐含作者”即电影中的编导,是观众(读者)根据作品以及自己的观影(阅读)经验所构建的作者形象。美国的叙事学家布斯认为,这个“隐含作者”与实际的作者本人有区别,所以“叙述者”还并不等于作者。这个观念我是赞同的,艺术作品毕竟是艺术作品,其中的“隐含作者”与真正的作者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我同时认为,如果完全切断这二者之间的有联系的一面,恐怕也极为不妥。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有联系的一面则是主要的。杨绛女士早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认为“作者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可能在作品里完全隐蔽自己。他的心思会像弦外之音,随处在作品里透露出来。”影片《情书》中透露出的博子的伤痛,女藤井树家人对其的呵护有加,秋场对博子开始新生活的不懈鼓励等等,实际上都是编导借助于影片中的“隐含作者”所表达的自己的一种人生思考与人生态度,一种旨在说服观众的修辞行为,通过成功的修辞控制观众的反应,并对观众在道德与情感方面施加影响。
二、平行交错与重叠,组成了影片的环状叙事结构
《情书》在叙事结构上,由两条平行叙事线索,组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艺术世界。一个是博子与追求她的秋场的世界,一个是女藤井树在国中读书与男藤井树相处的点点滴滴,以及现在与家人关系的世界。对这两个世界的两条平行叙事,它们都具有各自的“起、承、转、合”的传统叙事特点,但又有交错,还有它们相对的完整性。
对博子来讲,是从“发现”转入“求证”。博子意外“发现”自己成了别人的“替身”,因而叙事的“动力”彻底发生了改变,从渴求找人“倾诉”变成了“求证”自己到底在未婚夫心目中曾经占有什么位置,“求证”他所说的“一见钟情”其“含金量”有多少。
对女藤井树来讲,是从“回忆”转入“发现”。女藤井树对男藤井树的“回忆”,最初仍然认为正是这个同名同姓的家伙,给自己在国中的三年学习生活带来的是“灰色的岁月”,不堪回首。即使在回首之中,仍然认定那个家伙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行为怪异”。但是随着“回忆”逐一展开,她“发现”了许多过去被自己所疏忽了的细节,当她把这些疏忽了的细节与往事一一串联起来,排列在她的回顾之中,她终于后悔莫及地“发现”:那个家伙其实并不讨厌,相反很可爱,很有男子气概。他实际上早就钟情于自己,那些显得怪异与笨拙的行为举止,企图引起的是她对他的注意,表达的却是一个青春少年的纯真之爱。
对秋场来讲,要赢得博子的爱,就必须关心她,帮助她从爱的“伤悼”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正视过去的已经过去。
对女藤井树的妈妈来讲,要治疗女儿的感冒宿疾,从
老宅迂徙并非是明智之策,关键是要改善对爷爷的信任,找回那份失落的亲情与温馨。
两条平行叙事线索,在剧中重叠与交错地推进,使整个故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环状叙事。从叙事的情节节奏、情节结构、情节推进与情节安排的密度上来看,是“隐含作者”在进行驾驭与操纵。而“隐含作者”的介入,我们虽然听不到他的“声音”,也看不见某些电影那种惯常采用的打出的“字幕”,但我们依然可以明确地感知他的存在。这突出地表现在处理环状叙事的两个时空的交替安排上。
从内容的表述上来看,《情书》这部影片中的两个女主角,她们的确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独立的生活空间,如果这两个独立的艺术世界、独立的生活空间,不发生环状的交替与重叠,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变成互不相干的两个板块结构叙事。然而,要是这样处理与安排情节叙事,无疑就背离了岩井创作的初衷,因为岩井要表达的主旨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那个感悟。这个时空的交替与重叠,使影片摆脱了板块叙事结构,而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完整的艺术叙事。
关于两个女主角博子与女藤井树的书信交流,我们注意到,影片中选择了女藤井树的家,家门前的红色邮筒,特别是多次将她安排坐在她的电脑前打字。这形成了一个“组织时空”。这个“组织时空”的作用,最初并不引人注目,但随着书信的频繁往来,它显示出了。组织者”的优势,把不同时空,按照时间顺序的基本逻辑,加以巧妙地组织编排。而那些被组织和被安排到这个“组织时空”里来的情节场面时空,包括女藤井树自己的大量。回忆”时空场面,显然都成了整个故事情节叙事中非常重要的“插入时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正是影片中这些对往事回忆的大量“插入时空”,由它们组成了这部电影的感人的血肉部分。对观众来讲,“插入时空”的焦点,聚焦于“被看”与“被注视”的对象,即影片中的藤井树是否真的爱藤井树,这恰是观众的关注点与兴奋点。
应当看到,这种“交错式时空”,是彼此补充与相互推动的,“插入时空”中的情节场面,围绕两个藤井树展开的纠葛,推动了“组织时空”中的动作线向前发展。即博子的“发现”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后——已到了该向未婚夫告别的时刻了,但人的感情有别于动物,人的感情要复杂多了,所以当影片情节达到高潮时,博子面对温暖的晨曦照射的庄严巍峨的雪峰,那一声声充满凄苦充满深情的呼喊:“藤井君,你好吗?……”一刹那之间,万山呼应,荡气回肠。这真是催人泪下而又浪漫的大手笔!
博子在秋场的陪伴下,奔赴未婚夫生前攀登献身的地方,为自己的青春岁月划下了一个句号,但同时又是她的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女藤井树在高烧昏迷之中,被爷爷奋不顾身,顶风冒雪送往医院接受了及时的抢救。影片结尾部分对这两个女孩的表述,又一次回到两条线索的交错平行叙事。其中的视点讲述方式,变得流动而并非一成不变,甚至经常相互转换。“隐含作者”的全知性的外在视点,随时以“人物视点”予以配合补充,而人物的内视点,则以“作者视点”从外部进行统摄与整合。
总之,在《情书》这部影片中,流动转换的视点与相互配合的内外视点,由剧作的环状叙事结构所决定,其间的视点转换与两个时空的重叠与交替,因为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与情感逻辑,服从于讲述作品的故事的修辞技巧需要,都得到了观众的欣然认同,给我国的电影创作,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启示。